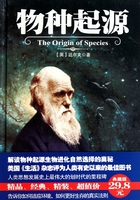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六点三十八分,一个新生命诞生了,全身紫色,冷得发抖,迎接她的是助产士和护士例行公事的动作和眼神。她的妈妈仰面躺在几步开外的无影灯下面,等着缝合下腹部十三厘米宽的切口,没有抱她,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她的爸爸,可能等在产房外面,也可能不在。
之前的那些关于分娩要领的课事后证明根本没有用处,我用力的方式和时机完全不得要领,几十分钟漫长无用的尝试之后,因为胎儿宫内窘迫,医生为我做了剖腹产手术。虽然手抖得拿不住笔,我还是在产床上看了知情同意书,签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就此变得简单了。仅仅三十分钟之后,一个七磅重的婴儿从我的身体里取了出来,在医生的手接触到她身体的那一刻,她想哭,却呛了一口水,咳嗽起来,发出细微的,却是用尽全力的声音。那种颤抖的带着胸腔共鸣的声音,陌生而又古怪,几乎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我躺在那里,麻醉药的副作用让我觉得胃痛和恶心,惴惴不安的等着医生开口,害怕他说孩子有哪里长得不好。直到一个护士把她抱到我面前,对我说:“是个女孩子,很健康。”
孩子被包在粉红色襁褓里先送出去了。我又在手术台上躺了二十分钟左右,一个带眼镜的男医生给我缝合伤口。我知道他的名字,Bryan,也知道胖胖的说话带缅因州口音的麻醉师叫Clark。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这样,在手术台上,对着一个开了膛的裸体,若无其事地聊天。
“你很瘦,伤口会长得很好。”Bryan缝完最后一针对我说。
我说谢谢,第一次想到还会有个伤口。接下来,又是过床,被推出手术室,像在电影里看到那样,仰面朝天,只看到走廊上一个接一个的日光灯,听见自动移门打开又合上的声音。然后是Lyle的面孔,他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她漂亮极了,有对大耳朵。”
我什么反应也没有。我累惨了,被安顿在病床上之后,很快睡过去了,再醒过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伤口的疼痛在麻醉效力退去后越来越深切,右手手背上插着输液的管子。我不能翻身,脑袋下面也没有垫枕头。我勉强转过头,看见Lyle半躺在床边的长沙发上面,支起两条腿,那个刚出生的孩子闭着眼睛躺在他的腿上。他很高,显得孩子格外纤小,头靠着他的膝盖,脚软软地贴着他的肚子。他两只手捧着那张红红的小脸,就那么一动不动地静静地看着。那幅画面几乎让我落下泪来。
他看到我醒了,抱着小孩坐起来。我不想听他说什么惺惺作态的话,如果他不讲,那就我来,让事情简单一点。
“你不再爱我了是不是?”我问他,开头几个词说得很平静,然后颤抖,最后用不争气的眼泪结尾。
“不是这样的。”他回答,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小孩放到婴儿床里面。沉默了一会儿方才继续,“我知道你往30D打过电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他,眼泪顺着眼角滑下去落在床单上。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可能是因为有输液的管子插在那里,他的动作既不温柔也不坚定,“没有其他女人,从来就没有。那间房间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你。我不会……我只是需要一个地方,一点空间。”
“没人说过有其他女人。” 我打断他,“为什么什么都不和我说?”
“因为你从来就不相信我。”他回答。
“所以你就这样走了。为什么?我做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事情?”我不哭了,努力冷静下来的把话说完。
“我不是故意的,我需要一点时间。这只是一个阶段。我不知道……”他继续含含糊糊,然后又是沉默。我看他,他垂下眼睛躲过我的目光。
我闭上眼睛,用手示意他够了,不用说下去了。我想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曾经是陷在爱情、欲望和纯美的家庭梦想里的傻瓜,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所设想的那样美好,所以他后悔了。我想告诉他,不用说了,我都懂了,结果却一个字都没说。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把话说出来。我在脑子里架构起一整句句子,如何发音用哪种语调,全都想好了,就是不说出来,或者是说不出来,渐渐地我开始分不清楚有些话到底有没有讲出来过。
躺在旁边小床里的婴儿发出嘤嘤的声音,跟其他健康的新生儿不同,她没能为这个家庭带来任何轻松和兴奋的感觉,尤其是我。所有人都对我宣称:“这是你的小孩。”而我却被一个怪念头缠住了,始终不能相信她就是曾经在我肚子里的那个Caresse。那个时候我离她如此之近,通过那些踢腿儿转身挥手的动作,觉得她就好像已经是一个有感情的聪慧的孩子了,她跟我进行着某种交流,分享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秘密。但是,当她脱离母体,这个一碰就会受伤的幼小生命似乎又退回到一个更加原始的状态。她五官稚嫩,手又小又纤薄,握着拳头没完没了地睡,最初的两天里,连吃奶也兴趣缺缺。不过,那样正好,因为我也几乎没办法给她喂奶。
分娩之后的几个小时,按照医生的说法是“随着荷尔蒙的骤然下降”,我不断下沉直到陷进没有一点亮光、没有尽头的深蓝色里。我记得看到小孩的出生纸,上面填着我的医学年龄,二十五岁,我几乎忘记的年龄,只知道在过去的任何时间里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绝望的感觉。这只是一个阶段,我现在明白了。我打算活一百岁,如果真的可以活那么久的话,那段时间真的就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瞬间。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爱我、保护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或者只是用温柔坚定的声音告诉我,一切坏的都会过去的。
我没完没了地睡下去,好几天不吃不喝。有的时候我并没真的睡着,只是闭着眼睛。我还是不方便翻身,也不太敢触碰自己的身体。特别是肚子,那个本来饱满的,孕育着一个活泼生命的肚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松弛的死气沉沉的地方,而且也不是原来紧绷平坦的样子了。
Lyle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出现在病房里,一般都不会超过半小时,如果碰上孩子醒了,他会留得久一些。有的时候,他站在床边看着我,而我不愿意睁开眼睛。
我在医院里住了五天,其间几乎没怎么碰过孩子,全是Damala和保姆在照顾。也没有喂过奶,衣服的前襟总有两块湿的奶渍,换了干净的很快又洇湿了,我不去管它,幸好也没有什么忍不过去的胀痛的感觉。
出院的那天上午,有一会儿,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我侧过脸,那个小孩子就在离我不到五十公分的地方,看起来既不像Lyle也不像我。她似乎醒了,一只眼睛仍然闭着,另一只懒洋洋的很慢很慢睁开来。我努力靠近她,想看清楚她虹膜的颜色,曾经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希望那会是深蓝色。
外面天色阴沉,九点多的时候,开始下起霏霏淅淅的小雨,Nicole、Cheryl-Ann,还有Lyle都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能自己坐起来,也可以四处走动了。我坐在床边,跟他们一样逗逗孩子,互相说话。有其他人在场,一切看起来就都很正常,和任何一个新添了个宝贝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了。
Lyle站在婴儿床边上给Gerard打电话:“是榛子色,对,美极了。”
我知道他是在说眼睛颜色。榛子色,原来是榛子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