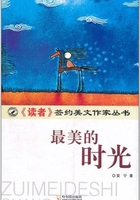金鹰卫也发现了身后的异状,他们可以选择回援,那样就能重新与铁林军衔接,还能给苑军造成重大打击。但是同样他们也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金鹰卫用来近身战斗当然也能以一当百,但是比起冲刺的威力就小多了。带兵的金鹰卫队长思考一下,一挥手,命令手下对着正前方,正在不断发出指令的苑军主将霍庆阳而去。金鹰卫是最好的武器,最好的武器要用来杀死最重要的敌人。
霍庆阳一身铁甲,端坐在马背上,金鹰卫挟着冲天的气势扑过来,人还离得远远的,就有一阵疾风扑面而来,吹得他衣襟猎猎作响。霍庆阳一动也不动地看着,眼神越来越锐利。他的马是从做定远军副帅的时候就骑着的战马,和胭脂、砚台那样的绝世良驹比起来,也许算不上好马,但却是一匹真正饱经沙场的战马。面对无数散发着巨大杀气的敌人,在没有得到主人指示之前,马如同他的主人,铁铸一般一动不动。
霍庆阳身边的亲兵受到主帅感染,也莫名镇定起来。士兵们和霍庆阳并没有多熟悉,他在西南做行军总管日子已经不短,平日里大家都觉得他更像一个主管杂务的官员,什么小事他都会过问,却一场仗也没有打过,甚至可以看得出,他根本就不想打仗。一个领兵的元帅怎么会是这种气质?可是这一刻,见到霍庆阳山一般屹立在那里,并无丝毫怯意,再没有一个人怀疑他是在百万军中厮杀了十几年的老将。
霍庆阳紧紧地盯着扑过来的飓风,并不下令。那阵狂风来势不减,风卷寒光,越来越近,霍庆阳目中精光一闪,挥手喝道:“射马!”
他“射”字出口,身后五十个士兵挽弓松手,空中利箭如云,宛若一把尖刀插向对面,正中金鹰卫队伍之中。五十支羽箭而已,聚在一起也不过海碗般粗细,却宛若大锤砸向水面,带起的风声尖锐至极,简直能在短时间内扯裂天空一般,呼啸着冲向金鹰卫胯下的战马。
饶是金鹰卫个个身手了得,反应远比正常人迅捷,第一时间就挥刀下劈,用他们手中百炼精钢的马刀将箭支劈落在地。却还是有一些人来不及,十几匹战马悲嘶着咕咚咕咚倒在地上,十几名金鹰卫止不住惯性,一头栽在地上,几个跟头之后,就被来不及勒住战马的同伴生生踩死。速度太快的坏处就是,遇到突如其来的状况,即便脑袋反应过来,手也来不及行动。
利箭像刚刚金鹰卫撕裂他们的防御一样,将金鹰卫的队伍撕开条裂缝。但金鹰卫队形只乱了一瞬就恢复正常,他们个个都有精湛的骑术,可以控马越过同伴的尸体,却不会让队形打乱。
领头的金鹰卫队长双眸也有了诧异和震惊,他看到有一百多个弓弩手一直站在苑军主将的身后,就知道这些人会有些战斗能力,可不应该有这么可怕的素质。刚刚利箭从他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竟然让他浑身战栗,这队弓弩手的眼神、队形、力量、准确度,甚至面对他们冲过来时保持的镇定,都是他在以往任何一次战役中都没见过的。他不知道,这便是让他们西瞻军闻名丧胆的原来定远军中,最著名的神弩先机营成员。
神弩先机营不做单兵作战用途,所以他们没有冲锋。如果用现代战争形容,金鹰卫就是特种兵,神弩先机营就是特别行动队。金鹰卫不太善于射箭,昔日他们在战争中能席卷草原、远征北褐万里不败,仰仗于他们的速度造成的出其不意的冲击。他们极少动用千人以上,甚至只有一百个人,就敢向一个中型的部落冲锋。
这次来大苑也是一样,金鹰卫的战士觉得软弱的中原人,只会比北褐战士更加不堪一击。他们需要战胜的就只有恶劣的天气,和大苑那的确难缠的战阵而已。事实上也是如此,只出动了一千五百人,在并不占据地利、平等作战的条件下,他们就几乎将青州四万军队全部吃掉。
或许还要注意一下苑人的头脑,小小的一个河水改道,就差一点让他们困在山上下不来。但是苑人的战斗力,骄傲的金鹰卫是无法重视的,你怎么可能对一个眼神明显畏惧你的对手重视起来?这是第一次,几百个金鹰卫面对区区五十个敌人,他们在敌人的眼神里看不到一丝畏惧,也看不到一丝冲动。这样的士兵,可以冷静地执行任何任务,可以把战斗力发挥到最佳的状态。
只一瞬间,金鹰卫的领队就明白这队苑军不好对付,他毕竟作战经验丰富,一声呼啸,做了个手势。配合纯熟的手下立即勒马向两侧分开,想要从侧翼迂回攻击敌人的主将。他们已经看清,对方五十个人手中只有弓箭没有手弩,而弓箭只在远距离起作用。金鹰卫虽然被阻挡了一下,却也和苑军拉近了一段距离,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只要让他们再上前一段,他们绝对有信心将这些弓箭手斩于马下。他们纵横草原多年,每个人刀下都不知夺去了多少个人的性命,短兵相接,他们不相信有什么人能挡住他们的马刀。
可金鹰卫没有料到,他们竟然无法拉近和这一小队苑军之间的距离,霍庆阳在一轮羽箭射完之后,毫不犹豫地喝道:“散!”五十个弓箭手霍然散开,勒马向两翼退去,居然抢先在金鹰卫之前。
众人愕然,才要追击,前面五十个人潮水般退却,将后面同样五十个手拿弓箭的士兵露了出来,五十把以上强弓特有的弓弦拉满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羽箭又出,箭头的寒光成网状交织在一起,天地先是一静,再是密集的破空之声哧哧响起。刚刚接受了一遍强弓洗礼的金鹰卫们,绝对想不到这一轮箭雨竟然如此错落有致,可以将箭射成一张网,却不让自己的箭支在空中彼此撞落。单打独斗,神弩先机营的弓手肯定不是金鹰卫的对手,骑马穿插纵横他们也不在行,可凭着无与伦比的箭术优势、变幻莫测的箭法,却让金鹰卫吃了一个大亏。
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金鹰卫由于一直戒备,还能用刀拨开利箭,后面的却因为猝不及防,好多人都中了箭。尤其是最后一排,绝对没有想到箭支会飞过整个队伍,也没有想到箭支飞过整个队伍用的时间,居然和射最前面的人一样,同时射出,同时达到。十几个人无一例外,全部被一箭穿过了咽喉,直直倒在地上。再有几队这样的弓手,很可能所向无敌的金鹰卫就栽在这里了,可惜没有下一队了,这仅有的一百个人,是青瞳特别指派给霍庆阳的亲兵队。
定远军解散之后,尽管全力寻找,神弩先机营的战士仍只汇集了不足五千人。大概练兵是要有魂魄在的吧?离开了定远军大营那样特定的环境,以后再怎么选拔射箭高手,再怎么严格练习,也无法达到这个水准。
神弩先机营一百人有一百人的配合方法,一千人有一千人的配合方法,越多人,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青瞳没有将他们打散,全部派往关中,作为抵挡西瞻进犯的屏障了。谁也没有想到西瞻人会从青州进犯,这一百个人,还是很努力才给霍庆阳挤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为了射穿金鹰卫特制的战甲,他们射出的箭是特别打造的重箭,这样的箭每个人只有三支,并且重箭不能像一般羽箭那样迅速搭弓,射出一箭,就必须退后重新瞄准。只这么一耽搁,金鹰卫就已经冲进了他们的射程,弓箭难以取准了。两队神弩先机营士兵射完一轮后不再拉弓,而是毫不犹豫地散向两翼,他们没有一个人怕死,却也不肯做无谓的牺牲。
没有神弩先机营并不代表金鹰卫就安全了。
“长矛手!”霍庆阳再次用他低沉的声音发出命令。紧接着声音之后就是铺天盖地的长矛刺过来,虽然没有利箭那样惊人的威力,但是架不住人数实在众多。神弩先机营的弓箭已经成功阻慢了金鹰卫的速度,失去了速度优势的金鹰卫不再所向无敌,而是陷入无边无际的长矛阵势中。金鹰卫的领队眉头深皱,明白今日想夺取苑军主帅的性命已经不可能,他一声呼啸,命令手下向左翼突围。
王庶看得热血沸腾,高声大叫:“追啊!”
霍庆阳远远地听见了,心道:追不上的。但他却没有把这种打击自己军队士气的话说出口,而是简单地发出又一道指令,“冲!”
金鹰卫杀了他这个主帅是有意义的,而他就算把几百个金鹰卫全部杀死也是没有意义的,就算能追得上,他也不会追。与铁林军正面交锋的苑军已经损失惨重,他有更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做。
战场上激战的苑军个个杀红了眼睛,连日来残肢的刺激、尸体洪流的刺激、身边袍泽尸体的刺激,都激出了在中原人队伍中难得一见的彪悍。简直是死得越多,冲上来的就越多,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一个退缩的人。
但是自身战斗力的严重差异,单单靠血性可以支撑片刻,却不能支撑很长时间,体力严重衰退,许多苑军的动作和力气都不得不变小了。这时,有一队援军纵马急冲而来,这队人人数不多,只有几百的样子,然而他们发出一声齐齐的叫喊,几百支长矛就被掷了出来。长矛出手,空中光影纵横。近距离用长矛显然比用羽箭威力大得多,除了重甲兵,好些铁林军都挡不住这凶狠的一击。掷出长矛的苑军士兵手中刚空,立刻拔出腰间长刀,向敌人猛扑过去。
随后赶来的几千人也一起叫喊着扑上去,他们疯狂地挥舞着手中兵刃,连绵不断的兵甲撞击声中,人马喝嘶声不绝于耳。夜色浓浓,也没有火把,在青白色的雪地映衬下,无论黑衣西瞻人还是青衣苑军,人人脸上都是青白一片,如同没有生命的剪影。
霍庆阳紧盯着战局,发出了第四道命令,“挤!”
他的命令简洁有力,在他身后已经列队完毕的五千多新生力量整齐地冲了上去,将敌人牢牢固定在有限的战场中,然后一步步向回去的路逼近,尽可能减少敌人落脚的地方。西瞻军队开始了战争以来第一次后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知不觉间密集起来。
霍庆阳站在战场外围,就像石雕一样坚定,他虽然没有领兵拼杀,光是站在那里,却如同定海神针,让每一个士兵心中安定。
王庶已经带人杀了几个来回,全身都是热汗,他纵马快步来到霍庆阳身前,叫道:“霍元帅,不要和他们纠缠,更多的敌人从山上下来了。”
霍庆阳点点头,“王庶,你去传令,弓箭队集合,在离山脚两百丈处拦截敌人。”
王庶道:“那么远的距离弓箭恐怕难及,元帅,不如我带人再接近他们一些。”他心道:霍元帅会不会忘记了这个弓箭队只是普通军中的弓箭队,不是他的神弩先机营。
霍庆阳看了他一眼,耐心道:“仰射射程小,取准不易,最好等敌人下得山来再射击。但是西瞻马匹的冲击速度极快,弓箭队如果离得太近,只要一轮过去就会被敌人贴近,那就没有机会再射出第二轮了。离得远一点,虽然给了敌人下山的机会,但是下到平地之后,敌人的马速就不会有从山上冲下来那么快,平地上的敌军就会比较密集,弓箭队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王庶听着有些惭愧,大声答应而去,看来他需要学习的地方实在还很多。
嗖嗖之声不绝于耳,苑军弓箭队对不断下山的敌人展开了攻击。长久积蓄的力量,第一轮发射必然是惊人的。潮水般涌来的西瞻人亮出盾牌,抵挡密如细雨的箭支。但由于箭支过于密集,无论怎么抵挡,总有人从盾牌的间隙里中箭,扑通跌下战马,反而将后面战马的脚步阻碍了片刻。鹤翼阵两旁的苑军就趁着这个机会,将长矛狠狠地刺入敌人胸膛。从金鹰卫第一批士兵下山以来,就一直是单方面的杀戮,苑军被身手高超的金鹰卫和紧接着而来的铁林军重甲,打击得几乎无还手之力。战斗进行到现在,才第一次将双方的伤亡扳成接近的程度。
霍庆阳不断调整阵形,命令鹤翼阵压迫,将刚刚金鹰卫撕开的口子逐渐缩小,尽可能将更多敌人逼回山上。
铁林军也看出苑军的目的,然而他们现在的队列被拉得很长,此刻队伍两侧都是敌人,苑军已经形成牢固的鹤翼阵迎面拦住,正像一个铁翅膀的仙鹤般,向中间挤压,要将他们压成肉饼。前面不得不退缩,后面又不断有人从山上冲下来的结果,就是铁林军彼此挤在一起,连挥动兵刃的空隙也没有。
四万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下子都从山上下来,如今战场上从人数上看,还是苑军占据绝大的优势。队伍后面的铁林军很想上前帮助袍泽,但是两侧被鹤翼阵压住,实在凑不上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前方黑衣黑甲的铁林军,不断在苑军的羽箭下倒地不起,将鲜血洒在异国的土地上。
突然,一阵长长的带着吼叫的歌声从铁林军队伍后面传出——
“我们是苍狼的子孙,长生天赐予我们强壮的筋骨。”停顿了一下,那个铁林军的战士又开口唱道,“弯刀是我们的牙齿,战马是我们的翅膀,阳光下所有土地都是我们的牧场。”
有几个人跟着接口,唱道:“苍狼的子孙,快伸出你们的手,用敌人的血来见证我的荣耀。”
队伍前方的铁林军听到了歌声,像是变成了真正的饿狼,竟然无人再采用防御的姿势,全都挥动兵刃快速地砍杀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一起唱,“我们身体里流淌着苍狼的血脉,无人能阻挡我的脚步。我催动战马,踏过高山和原野,在白骨和尸体上竖起我们的战旗。烈火焚烧过的地方很快就会长满青草,那是长生天赐给英雄的牧场。”
苑军的战斗力本就比铁林军弱一个档次,如今被敌人气势如虹地一逼,竟然出现后退之势。要知道,他们现在后退一步,就等于给敌人让出一步的地方,就等于多放进一个敌人。敌人的人数本就比苑军多,战斗力又远远超过苑军,他们现在这一点点平手的局面,是靠战场狭小取得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崩溃。一旦崩溃,必然是无可抑制的四散奔逃。这种局面王庶已经在青州看过两次了,一次是四万大军被区区一千五百人追得几乎无路可走,不过当时他也在溃逃的队伍中,只顾跑得晕头涨脑,还谈不上看清全局。而另一次是在山上,他可是俯览整个战局,眼看着自己布下的崅月阵崩溃之后,苑军如同毫无反抗能力的羔羊,任由敌人追上一个个杀死。
王庶对战场上细微的变化已经十分敏感,他深深明白溃退可能只是一个环节。眼见现在苑军止不住脚步的趋势,就知道不好,于是命鹤翼阵放开包围,让出地方让弓箭手急射几轮,想用远距离优势将敌人逼回原地。开始几轮箭雨符合王庶的期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铁林军一时被密集的箭雨压得抬不起头来,刚刚拉开一点的战场又一次向反方向收缩。
王庶见到有效,不断叫道:“放箭!放箭!”
“我们是苍狼的子孙——”忽然西瞻的队伍中又传出狼嚎一般的歌声,那声音已经不成曲调,但偏偏高亢得穿云裂空,“弯刀是我们的牙齿,战马是我们的翅膀——苍狼的子孙啊——”无数已经受伤的敌人一边唱着歌,一边向羽箭扑来,“伸出你的手,把战旗插在白骨堆成的战场。等明年春风吹过,白骨上就会长满青草,那是长生天赐给我们的牧场。苍狼的子孙啊,不用畏惧死亡,生命只是艰难的轮回,你永远的家在天上。”
战场上,羽箭的使用最受局势限制,有一方气势大增,逼近了哪怕一点点,就可能让羽箭失去射程的优势。随着铁林军不断逼近,越来越多的弓手来不及搭箭瞄准就将箭支胡乱射出去,挡在弓手身前的长矛队被一层层剥离,不过半炷香的时间,箭雨便从密如飞蝗变成稀稀拉拉。
终于到了临界点,一切条理秩序都荡然无存,苑军和西瞻军缠斗在一起,已经没有了鹤翼阵、没有了弓手和长矛的配合、没有了将敌人挤压限制的目的,唯一剩下的只是缠斗,无论是苑军还是西瞻铁林军,现在都各自凭着本能作战。
王庶知道自己即将又一次眼看着军队崩溃,人说未见胜先识败的将军,将来必定是好将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老天对他的偏爱。虽然说两国交战经常是几十万人对峙,但真正在其中一场战役上,出动上万人也已经不多见了,双方各出动几万人,算得上顶尖的规模了。从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流州不过半年时间,这种顶尖规模的战役他就经历了三次,三次都是他这一方失败了。王庶失神地望着激烈的战场,这老天未免对他太偏爱了。
主将霍庆阳却没有他那么容易受到打击,他的全部精神已经被刚刚转过弯道的敌人吸引。乍看上去,这几千人和其他铁林军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用和前面队伍相同的队形、相同的人数、相同的节奏跑下来,仿佛只是若干分队中的一队。但是在霍庆阳老辣的眼神中,这些人就像羊群中的牧羊犬一般,有种无法掩饰的气质。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百战百胜,那么他就会拥有这种气质。眼下这几千人的气质形成强大的气场,仅仅看策马的姿势以及士兵之间的距离,霍庆阳就知道,这些敌人和刚刚开路的金鹰卫是一样的。
具有这种素质的士兵,一个军队绝不可能有许多,用来开路的都只有几百个,可是现在他们却有几千人在一起。几千人都是神情紧张,他们在马上飞驰,身子却都微微向内倾斜,隐隐形成一个圆形,护卫着中间的那一个人。圆心处一人骑着红马,穿着和周围人一样的衣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只一刹那,霍庆阳就知道这个敌人是谁了。他和这个敌人打过一次交道,不过那一次,他奉命追击孙阔海率领的主力部队,和此人正面交锋的是原来的参军、现在的皇帝。如今自己终于有机会与这个对手交锋,很好。
霍庆阳在心中计算着金鹰卫的速度,不断下达着命令,他的目光已经自动过滤了周围所有的金鹰卫,只牢牢盯着中间红马上的人。眼看着这人的身影越来越近,沉稳的老将也有一丝激动,就是现在!霍庆阳的手重重向下一挥,神弩先机营士兵手中的羽箭几乎与他的手势同时出动,配合无间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挟着三支重箭,一支箭射出,手指变戏法地一翻,另两支箭立即一起搭在弓弦上,几乎不分先后飞向目标。
敌人虽然有几千,但三百支重箭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队伍正中骑红马的人。尽管这个敌人穿着打扮和其他士兵没有区别,但神弩先机营的弓手们没有一句疑问,这是刚刚主帅的命令,也是他们埋伏这么久的目的。今日势必不能拦阻敌人,那么就要最大限度地削弱敌人的兵力,不能把战役结束在山脚下,虽然对大苑来说是巨大的灾难,但霍庆阳是个未战先想退路的人,这个最坏的结果他已经在战前就想过了,如今这种最坏的情况真正出现,他也要让这场仗取得最大的成果。杀死敌人主将,当然就是最大的成果。
箭雨刚刚飞出,萧图南立即做了一件事情——拿着盾牌翻身下马,他这种经验是从千百次生死搏杀中获得的。对手用的是重箭,重箭很难像一般羽箭那么灵活,破空之后,为求杀伤,取的都是稍高的位置。这么说,万矢齐发还有个空处,那就是近地的位置。
萧图南在下判断的那一刻同时行动,刚离开马背便立即蜷起身子,尽量将整个身躯躲在盾牌之后,盾牌护在了正前方稍稍向上的位置。无数的金鹰卫来不及做出别的动作,竟然齐齐俯身,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他落马的地方。
萧图南只觉得头顶整个天空都被这些亲兵挡得一暗,然后他就听到沉闷至极的扑扑声不绝于耳。那种声音仿佛利刃穿过豆腐、铁锤击碎竹子。热辣辣的鲜血争先恐后地激射在他身上,如同四面八方都有人用桶向他倒出热血一般,瞬间就将他淋了个湿透。然后他手腕猛然一紧,整个人就像被大锤敲中一般,一股无法抵挡的大力从盾牌上涌过来,不等落地,身子竟然被大力击得平平向后退去。
他反应得极快,几乎所有的箭都没有追上他落马的速度,只射中了他的亲兵。这一刻,就算换成武功高强的任平生,也绝对不可能有他这样快的反应速度和准确的判断力,也不会有无数人舍生忘死地保护,也就未必躲得过三百支神弩先机营射出的箭。
即便这样,还是有四支重箭超过人反应速度的极限,先于一切到达他身边,三支击中了他的盾牌,一支划过他的肩头。然而那箭支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击中他盾牌的三支箭就将他整个人带飞了起来。划过他肩头的那支箭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切开了他的盔甲,并没有碰到皮肉。但是箭风把空气挤压得如同也变成利箭,把他肩头的肌肉炸开很大一团血肉模糊的伤口。即便让一个普通的弓手正好射中,也不见得能造成如此大的伤痕。
现在是杀死敌人主将的好时机。萧图南被三支箭带得飞起来,在别人看来,他身子平展,前后左右还有不少护卫,暴露在空中的时间也只有眨眼睛那一瞬,几乎不可能取准。但对于神弩先机营的弓手蒋成来说,一眨眼的时间足够他杀死三个人,目标既然被他看到,就等同于被他消灭。
蒋成是这一小队的头领,每次执行任务,他手中最后一支箭都要等别的队友射完了才出手。如果队友没有杀死目标,那么他来补救。如果队友已经完成任务,他会补上一箭,确定目标死得不能再死。
神弩先机营最后一支重箭在他手中变戏法一样搭在弓上,箭支上弓那一瞬间就已经对准萧图南的咽喉,准确无比,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将两者连接一般。蒋成中指行云流水般扣弓,只要手指一松,下一刻,这支箭就会出现在敌人的咽喉上。
他成为神弩先机营队长以来,像这样的箭射出去恐怕有上万次,还从来没有一次失手过。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这支箭的速度要更快些才行,所以他比以往多用了三分力。突然,他隐约听到自己手中的弓弦发出了奇怪的嘣蹦声,中指敏锐地感觉到弓弦发生了变化,好像手中的弓在告诉主人自己力不从心。蒋成手一滑,箭支飞出的那一瞬间轻轻颤抖了一下,那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的颤抖,只有手指和弓弦才能感觉到。蒋成脸色骤沉,没有机会了,箭支还没有到达,他就知道这一箭不会命中了。
这支箭准确无比地来到萧图南咽喉前,又在所有人的惊叫声中,贴着他的皮肉落在地上。羽箭的方向还是那么正确,没有丝毫错误,但是在最后那一刻,弓弦没有给箭支应有的帮助,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力量。
突然一声清脆的响声过后,蒋成手中弓弦已经断成两段。神弩先机营的队员一起看向他,表情茫然。对他们来说,弓就是他们的手臂,就是他们的灵魂,此刻他们的灵魂没有给他们最需要的帮助,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错过了杀死萧图南的最好时机。有奸细——人们心中第一时间升起这个念头,有奸细破坏了他们的弓弦。
事实并不是这样,西瞻人还没有本事在大苑军中,安插能接近神弩先机营兵器的奸细。神弩先机营弓弦断裂,完全是因为气候所致。大苑矿藏丰富,他们的弓弦是用金属制成,遇到过低的气温就会断裂。而西瞻最多牛马,他们的弓弦是用牛皮牛筋做成,遇到下雨就会失去弹性。这方面老天并不算偏心,双方各有长短。
霍庆阳和西瞻人打交道的经验应该足够了,但是云中远远没有高原这么酷寒,所以他也只知道西瞻人的弓箭会在雨天失去力道,却不知道自己的弓弦在严寒下也会失去作用。整个大苑军队里,也只有青州的守军用的是牛皮牛筋制成的弓弦,这一点作为军事机密,连一关之隔的麟州都不知道。而神弩先机营每一个弓手手中的弓都是陪伴了他们多年的兵器,他们想都没有想过要换弓,加之接连射出三支重箭,所以弓弦承受不住,自己断裂了。
战场上,大战役的胜负需要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人的生命却很可能在老天爷一念之间。萧图南就是这样,因为天气的帮助,躲过了他上阵以来离死亡最接近的一次。
萧图南站直身体,喝道:“好个神弩先机营!”他面色冰冷而坚毅,“怕什么?我不会死的……”萧图南心道: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我会带着我的士兵,把你的山河踏得粉碎。在那之前,长生天不会让我死。
“王爷!王爷!”拙吉吓出一身冷汗,迅速挡在他身前。
萧图南面容冰冷,翻身上了战马,从怀中摸出面具戴在脸上。
“王爷……”拙吉小声劝道,“面具给属下戴吧。”
“不必了!现在躲藏已经无用。吹号角,苍狼的子孙,跟我冲出去!”他用力一挥手,肩膀伤口狰狞,甩出一串血珠儿。
几千个金鹰卫一起大喝了起来,山下无数铁林军随之惊天动地地欢呼起来,“振业王!振业王!”
紧接着冲锋令之后,方才还四面散开、仿佛没有丝毫秩序的西瞻骑兵迅速汇集,变成无数个小队,每一处都是前两队左右两翼掩杀,第三队正面冲锋,向苑军杀去。如果说刚刚金鹰卫开路是利刃,将苑军划开一道细缝,那么现在的西瞻士兵就是钢针,密密麻麻不知从多少个方向向外射出。
战鼓声、号角声、兵刃相交声响成一片,分不出哪是苑军的,哪是西瞻的。至此,战场陷入彻底的混乱,敌我双方主将的命令都无法下达到小队,如同一个失去大脑控制的人,四肢胡乱挥动,只能打到哪里算哪里,徒劳地想拦截从无数个方向冲出来的敌人。
西瞻士兵很快就突破了苑军设下的重重拦截,向麟州方向冲去。无数黑色、青色的身影缠斗在一起,在麟州山坡、河谷铺开了一张大网。每一个身体完好的西瞻士兵都将冲出去当成首要目的,但是他们一旦受伤,就会立即跳下战马,把自己没有受伤或者体力较好的战马,让给身后冲过来的同伴。他们自己则停下来,尽可能将敌人阻挡在身前。而一个个冲出来的西瞻士兵,会毫不犹豫地跳上更好的战马绝尘而去,对替他们挡下死亡的同伴看都不看一眼。
护卫着萧图南的一队已经走远了,他们拥有整个队伍最好的马、最好的战斗力。他们飞快地穿越整个战场,没有人能拦住他们。他们并没有管身后还陷入混战的战友,对于金鹰卫来说,攻击是第一要义,攻击是第一手段,不停地攻击、以攻代守是他们奉行的宗旨,这种骑兵从来不做断后的用途。
战场如同被猫抓过的线团,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西瞻军各自成列,从不同方向突围。霍庆阳指挥着身边勉强还能控制的七八千人,在战场上紧紧追着一队千余人的敌军不放。战场形势改变,他的目标再次改变。西瞻铁林军深入大苑国内作战,那是死一个少一个,趁着现在敌人密集的时候,尽可能消灭多一些敌人,那么日后深入内地的战争中,就会减少一些对手。单单从战斗力而论,七八千人对千余人才有把握,所以霍庆阳没有好高骛远地选择更大的队伍追击,而是选择了他有把握吃下的最多人的队伍。
这一队西瞻军似乎感觉到了身后敌人的威胁,他们不停地改变路线,试图甩掉身后的苑军。但是混乱的战场让他们不能发挥速度优势,而他们身后的苑军又和其他人不同,目标极其明确,就是认准了他们不放,就是要杀了他们才罢。
跑了一阵,西瞻军突然分出一队八九十人的队伍,向左前方狂奔,同时,剩下的大队人一声呼啸,向右前方奔去。等苑军追到他们分兵的位置,西瞻人一个大队一个小队、一左一右都已经跑出去老远。霍庆阳愣了一下,吩咐不用理会这几十个人,继续追击右边大队敌人。
又跑了一会儿,再次从前方西瞻军中分出一队几十人的小队,大小部队再次分别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跑去。苑军一个偏将喜道:“西瞻人有逃兵了。”
霍庆阳眉头微皱,这队人虽然少,但是彼此贴得很紧,进了树林还保持队形,不像是没有组织的逃兵。他微微停了一下,命令继续追着大部队,不理这些人。
追了一个时辰,西瞻像这样分兵分了七次,每次多则八九十人,少则五六十人,像从大麻绳上拆下来的小股细绳,苑军始终不理会这些,只盯着大部队不放。直到他们面前的目标越来越少,最后从千余人剩到三四百人,霍庆阳才猛然惊觉西瞻人的目的。
如果你看过被狼群追逐的野马,就能明白这个分兵的道理。西瞻人的目的就是冲出重围,但是聚集在一起冲显然不成。苑军八倍于他们的兵力,紧追不放,还聚集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全部送命,只有分兵才能尽可能保存实力。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面对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分兵岂不是送死?但事实上,真正追击过程中,面对大部队分出来的少得可怜的几十个人,追兵基本都不会理会小股,而是直接追击大部队,那么这一小股人便安全了。
这种分兵的诀窍就是每次绝对不能分多,分多了敌人就会分兵追赶,不会容这些人跑了。只有让敌人看不上眼的一小部分分出,才会被急于追击的敌人忽略不计,这样几次分下来,至少能逃掉一大半人。霍庆阳发现自己的错误后,他追了一个晚上的敌人已经剩下不足四百。
就算西瞻的战马都是好马,从山上冲下来,一个晚上不停地奔跑厮杀,此刻也个个疲惫不堪,在小金川和大金川交接的水域,八千苑军终于追上了不足四百的敌人。西瞻士兵停止了奔跑,他们知道分兵到此结束,他们背对着漂着冰凌的河水散成一个圆弧。长声呼喝中,苑军的矛头和西瞻的腰刀一起闪烁,双方都憋着刻骨的仇恨和怨气。
战局至此已经不需要霍庆阳指挥,用二十倍的兵力将一小撮敌人困在小金川边缘,谁都知道该做什么。能在混乱的战场上追了一夜没有队形涣散,无论从体力还是纪律性上,都说明这八千个苑军是最精锐的,眼下这支精兵就带着刻骨的仇恨对敌人发起最后的攻击。
西瞻铁林军在大苑的土地上,展现了他们称雄四国的战斗力。四百个士兵对八千个精兵,战斗竟然还能持续一个多时辰。很长一段时间内,小金川变成红色的河水里,苑军流出的血还是远远多于敌人。直到天色大亮,阳光照耀在红色的河水中,最后十几个全身是血的铁林军仍然在歌声中奋力拼杀。
“我们身体里流淌着苍狼的血脉——
我的荣耀要用血来见证!
长生天的宠儿,别畏惧死亡,祈求与哭泣属于弱者!
灵魂会在烈火中升腾,鲜血浇灌过的地方很快就会长满青草,那是长生天赐给英雄的牧场!
苍狼的子孙——
别畏惧死亡!
无人能阻挡我的脚步,长生天让我看到的一切,都是长生天准备赐予我的!”
河边还剩下十几个西瞻士兵,最初那个想出用人体糖葫芦串下山的小队长也在其中。他杀得兴起,一把扯下破破烂烂的衣服,在冰天雪地里上身赤裸,露出肚子上骇人的刀疤。至少有七八杆长枪同时伸向他的肚子,他一声大吼,抡刀砍向枪杆,七八根枪杆竟被他一刀全部砍断。然而更多杆长枪伸了过来,一起插在他的肚子上。他仰面跌进水中,肚子上密密麻麻的枪杆向上挺立,如同插着糖葫芦的草标。
最后一个西瞻士兵是个百夫长,身手很敏捷。他在这必死的境况下仍沉着应战,苑军越急他越稳,至少有十几个苑军在他神出鬼没的招数下一招毙命。这个百夫长用眼角余光看到一个将领打扮的苑军纵马逼近,趁他荡开几个士兵的空当,一杆长枪毒蛇般探向他的胸口。他不知道这个人是王庶、是大苑的亲王,但他知道这人和其他敌人不同,是个用枪的高手,如果依照自己挥刀的速度,枪尖会在他砍断枪杆之前送进他的喉咙。
于是这个百夫长挥刀格挡用了斜向上的力道,却并不去砍枪杆,而是刀头一斜,顺着枪杆滑向对手,如同燕子抄水,这是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招数。他变化,王庶的枪杆也突然起了变化,手腕一翻,枪背隆起、再抽下,如同一个浪头要把燕子打进水里。百夫长立即抽刀,然而枪杆追击甚急,闪电般压住刀头,这个浪头还是打在他的脖子上,连着他自己的腰刀一起,血线发出哧哧的声音。江边最后一个西瞻士兵,就被自己的刀抹了脖子。
王庶骑在马上,任由敌人激射而出的热血喷在自己脸上。他紧紧握住枪杆一动也不动,不知为什么,他的耳朵里似乎还能听见敌人的歌声——我们是苍狼的子孙,苍狼的子孙……好像这歌声已经被大青山、小金川牢牢记住了,风每吹过一次,就会低低吟唱一次。
斯役,苑军亡万余人、重伤万余人、轻伤四千余。阵亡和重伤的人数多于轻伤,可见战斗之惨烈。而西瞻军事后统计,阵亡六千余,无重伤员。
在付出了六千条生命以后,西瞻最精锐的铁林军终于冲出了大青山屏障,来到大苑广阔平原的第一个落脚点——麟州。他们带着骁羁关冲下来的锐气,带着没有拖累的战斗力,带着没有补给、没有援军、没有退路的处境,向前方毫不停留地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