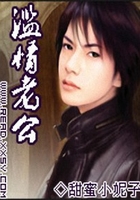我确信Fanny姐姐已经把杂志递到我家了,因为我已经在网络上看到那期杂志的电子版了,Fanny姐姐很厚道,我说要封面醒目位置,她就真的给我一个相当醒目的位置。
可是,就算是这样,骆兢铭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不主动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写信,更不曾在对话中对涡流露过半分情绪。这家伙,真是坚挺得紧!
于是,我打电话跟阿宝抱怨,我说:“骆兢铭这次看来真是气坏了,我这么讨好他,他都不理我!”
“你活该!”阿宝似乎是在吃着什么东西,边吃边回答我,口气极其不客气。
“宝……”我穷极无聊地跟阿宝耍赖。
“滚一边儿去,我又不是你男人!”阿宝咋巴着嘴,吃得很是畅快的样子。
“死女人!”我愤怒地砸着枕头,恨不得那枕头就是阿宝,那才好出气。
“我说,你就只是含蓄地写了篇破小说?”过了一会儿,阿宝似乎吃停了下来,慢悠悠地问道。
“啊,那个,其实也不是很含蓄啦!”我有点不太好意思,阿宝的态度很明确,我做的那些事,在她看来,还远远不够。
“你是请不了假呢,还是出不起机票钱?”电话那头传来敲台面的声音,我发现阿宝真是越来越有气势了,完全地压倒我。
“那倒也不是……”我开始抠枕头,为什么我就是不敢亲口当面跟骆兢铭讨饶呢,这个我自己也不太明白。
“那你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磨蹭什么呢?少几天课又死不了人!”阿宝义正词严地说道。
我不说话,在那儿思考着回来的必要性。
“我可听Elyn姐说了啊,她原来跟骆兢铭的那点儿破事儿……”阿宝拖长了声音,在那儿故弄玄虚,“原来人在国外,对你没威胁,现在人回来了,你闪了,你倒是很有谦让精神啊!”
“说什么呢!”我一口淬回去。
“为了我们咖啡馆的事情,Elyn姐可找了骆兢铭不知多少回了,谁知道会不会旧情复燃啊!”阿宝的口气凉凉的,在那边儿一个劲儿地煽风点火。
“他敢!”我一拳头砸在枕头上,果然定力不够,又被挑上了。
“什么敢不敢的?是谁说的,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这大半年的,也真是辛苦人家骆兢铭了。你就不能回来劳军一次?再说了,三叶草这星期天也要开张了,你这做老板的总得回来吧!”阿宝说得起劲,说得我真有冲动赶紧订机票回来了再说。
“好啦,我考虑考虑。”我软了下来,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做一回私事优先的小女人。
“考虑你个鬼!还不给我滚回来!气死我了,不跟你这没建设性的人废话了,手机话费贵,挂了!”说着,阿宝啪地挂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愣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笑了起来。
我是个别扭的女人,总是希望别人能解读出我的心思,逼我做出我愿意做的决定。无疑,阿宝是个很懂我心思的人,她知道我终究还是觉得一篇文字不够分量,仍是不免担心忧虑,于是,她说,你给我滚回来吧,回来把你男人看好守牢下个封印,然后再安心回去把书念完。我的心思,她一字不差地全部替我说了出来,所谓好姐妹,也就是这样的吧!
挂了阿宝的电话,我想了一会儿,立刻又拨了骆兢铭的手机,铃声响了三次被接了起来。
“是我,骆兢铭。”没等他说话,我就先开口道。
“我知道,有来电显示。”他的声音很是欢快,听起来心情颇好。
“你在干吗呢?”我疑惑地问道,周围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是在家里。
“正跟几个朋友吃饭,”说着,他似乎是走到了边上,周围突然就安静了下来,“怎么了?”
“那个,最近有没有我的快递?”我嗫嚅了半天,终于开口问道。
“什么快递?”骆兢铭装傻充愣的本事真是一点破绽都没有。
“那个……一本杂志。”我咬了咬牙,回答道。
“杂志?哦,收到了。”他的声音仍是镇定。
“那……你看了?”我小心地问道。
“嗯,看了。”骆兢铭回答问题的口气仿佛这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听得我不由得有点火大起来。
“看了?”我的音量提高了一点,“看了,你还给我这副鬼样子?”
听到我终于吼了起来,骆兢铭反倒笑了,“轶乔,你就那么有把握我能看懂?”
“那你看懂了吗?”我一下子没了气焰。
“嗯,故事写得不错,看来你在纽约挺空。”骆兢铭答得狡猾。
“嗯……那个,我听阿宝说,三叶草,这个星期天就能开张了?”我还是决定换个话题再说。
“是,我听Elyn说过,怎么,要我替你去?”骆兢铭倒也不执着,我问什么,他就跟着说什么。
“也不是。”我犹豫着是该直接杀回来呢,还是先告诉他一声。
“哦,我周五开始,要去成都出差个四五天,开张那天正好也不在上海。”
“啊?”我有点意外。
“怎么了?怕回来看不到我?”骆兢铭突然就那么问道,听得我一愣。
“啊?什么呀?!谁回来了?!”我学着濒死的鸭子,最后犟着嘴。
“轶乔,你猜,我是在跟谁一起吃饭呢?”骆兢铭突然声音温柔了起来,那种感觉简直跟狐狸没两样。
我开始有一种不怎么好的预感,“你让阿宝听电话。”
果然,电话那头换成了阿宝笑嘻嘻的声音,“轶乔,那个,我刚才吃东西不方便,按了免提来着。”
我倒吸一口冷气,“你想死啊!”
“我哪知道是你打的电话呀,我又不是你男人,你的号码能倒背如流的!”阿宝叫着委屈。
我气得有点说不出话来,能想出这样的损招,除了骆兢铭,我也想不起来别的人了,“还有谁在?”
“Elyn姐,Vivian,还有晓紫。”阿宝小心翼翼地报着名字。
从她嘴里每蹦出一个名字来,我就愈加有想咬人的冲动,“把电话还给骆兢铭!”
“跟阿宝说完了?”骆兢铭笑笑地问道。
“嗯,你没有开免提吧?”我一肚子火压着不好发作。
“没,我方便接电话。”骆兢铭笑得更欢了。
“你故意的!”骆兢铭整我有点狠,我开始觉得委屈了。
“你可以回来咬我。”他回答得嬉皮笑脸的,我却突然地被这话给说得脸红了。
“我……”我想,这个电话跑题了,并且远得我已经拉不回来了。
“有什么话回来说,我会替你跟Andrew打声招呼的。”骆兢铭果断地阻止了我。
我固执,他又何尝不是,也有他一定要我做的事情,比如,回去给他一个交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表示,骆兢铭不生气了,他知道我要回去,他也要我回去,虽然,他不提那故事,不提我欠他的那些话。
天气渐渐炎热起来的五月,我在纽约已经待了三个多月了,来不及等到培训完结,我便要回家了,那里,所有的人都在对我说,你赶紧给我滚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