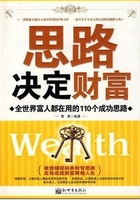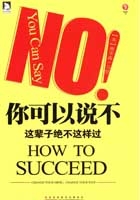黑风寨。
“喂!不是同你说过不许再喝酒的么!”
寝屋的门“砰”一声叫人自外面踹了进来,屋内之人循声瞧去,却见司徒沫双手插腰一脸凶相地站在寝屋之外,本一双清澈灵透的眸子,如今正是充火似的瞧着床榻上的鬼臼和站在他身边的三名小喽啰。
“就只喝——”鬼臼见让司徒沫抓了个正着,忙将喽啰手中的酒水护在怀中,似是努力地想了很久之后,伸出两指同司徒沫比了比“一点点”的手势道,“就那么——”
不等鬼臼将话说完,司徒沫早已是横眉竖目地闯进了寝屋,之后一把夺过鬼臼手中的酒坛子,冲着门外便毫不心疼地扔了出去,在鬼臼一片心疼地哀嚎声中,她霍然将清眸一瞪,“一滴都不许!”
如今他还是有伤在身,子湛已是千叮万嘱短时期内要忌酒,话说自己刚刚才走开一会儿,去子湛房间讨教一些有利于他伤势的法子,却不料尚未踏足寝屋,便是自外头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酒香味。
他要喝酒已是犯了大忌,如今一喝竟还要喝那么烈性的酒!简直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即便不给我喝,也别将那酒扔了呀。”鬼臼可怜巴巴地望着门外已是粉身碎骨的酒坛子,砸了砸嘴巴,兀自叹了口气。
那么好的一坛陈年女儿红,自己才是刚刚闻着了味,连尝都没有尝,便是这么叫她扔了,着实可惜!太可惜了!
“不扔了它,等着你醉死酒中?”司徒沫秀眉一挑,见着边上的喽啰碍眼,立时冲着他们没好气地道,“明知大当家的受了伤却还拿酒给他,你们究竟是为了他好,还是眼睁睁地盼着他早死?”
“小的不敢。”
那三名喽啰见鬼臼这几日叫司徒沫看的紧,猜忖着这肚中的酒虫子定要爬出来了,这才本着拍马屁的原则,带了上好的女儿红来孝敬鬼臼,哪料到这司徒沫竟长了只如猎犬般灵敏的鼻子!
这不,他们才刚刚挖掉了酒坛上封存用的泥土,刚刚才将酒递于鬼臼鼻前让他闻了闻,下一刻便见他们的夫人用力踹开了寝屋的门,一脸凶相地怒斥走来。
“滚下去!”
司徒沫又是没有好气地冲着三人喝道,那三人一听,忙是同鬼臼躬了躬身子,之后通通缩着脖子离开寝屋。
“听说咱们夫人是这圣烨皇朝首富司徒仪的二女儿?”
司徒沫见三名喽啰走出寝屋却忘了将门带上,本是想要转身去关门的,岂料却听得那三名喽啰走出不远之后的这番对话,因了好奇他们究竟想要说什么,索性沉声静气地站在原地等着听他们的下文。
“是,我也听说了。”
如今说话的这名喽啰显然是极力想要将声音压低的,只是平日里粗犷惯了的他们,即便有这心思想要压下音色,然而一出口又是叫司徒沫听了个清清楚楚。
“这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不都应该是斯斯文文,莺声燕语的?”
“呸!你这说的是勾栏里的窑姐!”有人反驳,“不过,即便不是莺声燕语的,怎么说也该是任人欺负的好性子,怎么会像我们夫人——”
那说话的喽啰突然顿了顿,却也将司徒沫的心勾了起来。
像她怎么了!她不是照样沉鱼落雁,秀外慧中?
司徒沫如是想着,却不料听得那喽啰接下去道——
“怎么会像我们夫人这般泼辣,生来就注定嫁于我们大当家为妻。”
什么!说她泼辣不算,还说她司徒沫生来就该嫁给马贼?!敢情那说话的喽啰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成!
“你再与我说一次!”
司徒沫忍无可忍,无须再忍,那愠怒的声音,只在喽啰话落后便是应声而起,直吓得那三个自以为很小声的喽啰们撒腿就跑。
“还不给我速速站住!”司徒沫大喝一声,正要追出门去,却在身子向前倾的一瞬,叫人自背后环住了腰身。
如今寝屋之中除却自己同鬼臼之外没有别人,她知道身后之人就是他!
“放开!”
司徒沫冷然清喝,下一瞬却发觉自己的身子叫鬼臼更用力地拥住了,她方想开口呵斥他,却听他低沉的声音先是盖过了自己的,“如此刁蛮任性,泼辣胡为,果真生来便该嫁于我鬼臼为妻。”
姓鬼的!
司徒沫于心中暗咒,身子刚刚一动,却又听他调侃道,“方才你可看清了那说话之人?我要好好打赏他。”
可恶!
司徒沫在鬼臼怀中用力一挣,见他依然没有轻易放手的打算,手肘对准他的右肋间,用力地撞去。
身后传来一记闷声,司徒沫趁鬼臼吃痛收了些力道时伺机逃脱。
“姓鬼的,你要记住,如今本小姐还会在这里照顾你,全然是看在你收留我们一众钦犯的份上,本小姐只是想还了你这份恩情,你断然不要想错,更不要想太多!倘若以后再同本小姐有肌肤接触,我定当剁了你的婬手做花肥!”司徒沫兀自说了一长串,正想问鬼臼可是听明白了时,却见他捂着刚刚叫自己手肘撞过的右肋间,身子一点点地蹲了下去,司徒沫秀眉微微一蹙,旋即开口问道,“你怎么了?”
“我——”鬼臼话至一半,突然一声哼唧后将话咽了回去。
古古怪怪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喂,我将你扶到床/上去罢。”
见鬼臼埋着头,慢慢地点了两下,司徒沫这才蹲下身子,将他自地上搀起,而后一步步地向着床榻走去,只是亦不知那鬼臼如今是不是真当很难过,自门边向着床榻走去的这段距离,竟是将他身子的大部分重量都倾向了她,直叫她卯足了劲才能勉强扶着他走出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