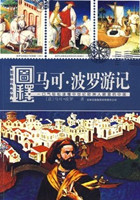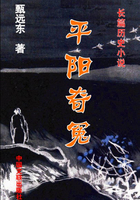凌晨一点,万籁寂静,这里是您的老朋友夜枯兰官,欢迎收听《夜半一点钟》。
今天碰到个事儿。
被打劫了。
中午和一个报社的记者朋友吃饭,约好在川菜馆。馆子地方比较偏僻,我不是很认得路,七转八转,还是没能进到里面,只好把车就近停下,穿过巷子,步行过去。
巷子里,很杂乱,电线交错,门窗歪塌,一地污水,有些地方,要弯下腰才能通过。
夜枯兰官常自诩,十年侦探生涯,练就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本事,不过今天看来,要么是吹牛,要么,就是真的老了。
等察觉有异样时,身后已经被一个尖锐的物件抵住。
“别动,老子拿刀顶着,身上的钱包、手机还有车钥匙,全给老子掏出来,别耍花样,不然捅死你狗日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谈不上怕,就觉得窝囊,可还是把东西都掏出来,托在手上,任由身后的那位仁兄拿走。
顶在腰上的物件离开了,然后是急匆匆的脚步声。
转身,摸出金属打火机,照着劫匪的脖子砸过去,这个力度我很有把握,不会打出事,又能让对方大脑有瞬间的短暂昏厥。
等我把他按在地上,掰过头来时,愣住了。
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我想,称其为孩子,或许更合适。
头发几乎长到肩膀上,染成黄色,戴耳环,刚被按倒时眼神凶狠残忍,如困兽。
很难想象,这种眼神来自一个孩子,让人不寒而栗。
他在地上拼命拱着,想挣脱压制,嘴里发出低吼声,像受伤的狼。
十分钟后,他发现一切都是徒劳。
恐惧,脸色苍白,嘴唇发抖,那是一个孩子做错事后的表情。
“叔叔,我错了,求你放了我。”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知道是他错了,还是我错了,这让人不好受。
手松开。
“你走吧,回学校读书去。”
这算纵容吗?我也不知道,只记得,《圣经》里,耶稣认为,孩子犯错是要给机会改正的。
我被从地上跃起的孩子一刀捅在手臂上,鲜血喷涌,破肉入骨。
突如其来。
他为什么就不给自己机会呢?
从医院到公安局,再从公安局回电台,一路上我都被一个问题揪住心。
是什么让少年变成一头残暴的野兽?
如同上一集《抢劫》中的刀子一样,竟以抢劫来填补无聊空虚的青春,以抢劫来获取成人世界的关注,最后以悲剧收场。
谁做错了?
这是个沉重的话题,成人,无疑要承担责任。
可能是他的父母,可能是他的亲人,可能是他所处的环境,不管怎么样,这个成人的世界,必须要有反思。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晚的不可思议事件。
这是听众代表招待会的第三个故事,讲故事者,是一个普通公司职员,他说,要给我们讲一个关于大厦的故事。
准备好你的听觉了吗?
夜半一点钟,黑暗最深处。
从经理办公室出来,坐在椅子上发呆。
脸上有点湿,他刚才训斥我时,喷在我脸上的。
那口水,像硫酸,能感觉到正在皮肤上“吱吱”地沸腾腐蚀,烧烂了早就麻木的自尊心。
我叫范进,和中举的那个人同名。
大学毕业,年过三十,离开学校多久,就在这家公司做了多久。
到底多久?有些模糊。
他们总在背后挫我,孤僻,怪异,他们老这样说。
困乏,无力,低落,整夜做噩梦,早上醒不来,这个星期,已是第四天迟到,迟到十分钟。
被骂了半小时,是的,我该死。
我在想,可能是患上某种隐蔽的绝症,病态的细胞正在拼命吞噬躯体,某个阴霾的清晨,我会沉睡不醒。
如果我死了,肯定就不能来上班,这属于旷工,经理得知后,会不会继续痛骂我?
如果我死了,我想,这栋大厦里,不会有人惋惜,这张小格子办公台,一平方米大的地方,从毕业后,我就在这里,一直没动,格子外的世界,很模糊。
机械般地做完事情,千篇一律的文案,下午六点钟,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下班了?
下班时间是五点半,但我从未九点前下过班,经理会扔过来很多事情让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他让我一个人把会议室的椅子和桌子全部搬到天台去,我不知道搬上去干什么,那天晚上我搬到十一点。
我才一米六八,一百斤,五十张桌子,两百张椅子,有点累。
第二天,他让我把桌子和椅子,从天台,搬回会议室。
一米六八,一百斤,五十张桌子,两百张椅子。
七点钟。
天黑了。
我的脸贴在玻璃上,有点冷。
窗外霓虹灯闪烁,像千万双眼睛,在窥视。
深吸一口气,二十三楼,俯瞰下去,蝼蚁,甲壳虫。
反胃,眩晕。
我有恐高症。
九点钟。
同事陆续离开,匆匆忙忙,面无表情,无人看我一眼。
经理走过来,居高临下,瞥一眼呆坐在格子里的我,走了。
他们本来就没当我存在。
走到街上,不敢回头,逃命般挣脱,大厦,阴沉的大厦,正在背后,狰狞。
奔到地铁口,脚步慢下来。
每一个城市的地铁口,都像匍匐在地表的怪兽,张开血盆大口,等着或干净或肮脏的躯体,鱼贯而入。
地铁通道。
一个流浪汉,长头发,长胡子,全身污糟,盘腿而坐,拿一副扑克牌,排过来列过去,嘴里还念念有词。
他在和自己玩牌。
半年前,我路过这里,他突然抬起头,冲我微笑问好,未及反应,又低下头,继续玩牌。
如果我在这座水泥城市里,还有个朋友,那么,就是他。
从那天起,无论多晚,我都要来陪我的朋友一会儿,看他打牌,有时说几句话,更多时候是沉默。
我蹲在他旁边看着,他低头玩牌,路人,有些惊讶,旋即又变成冷漠,还有些外国人,举着相机拍照,嬉笑,然后走开。
他们怎能理解?
我的朋友正在派牌的手停下来,扭过脸,看着我,表情怪异。
“你心情不好?”
我努力让自己挤出个笑脸,回道:“没有啊。”
他愉快地笑着,说:“别骗我了,我看得出来,哈哈。”
“怎么会看出来呢?”
他凑近我的脸,神秘地说:
“我当然知道。每一座大厦,窗户后面,都有一个秘密。”
“哈哈,那你知道我什么秘密?”
“我知道你今天被人骂了,还知道”
“还知道什么?”
“还知道,你很想那个人死,哈哈。”
半年,今天才发现,我的朋友,幽默风趣。
晚上,回到出租屋,和衣躺在床上,莫名的焦虑如蒸汽升腾,弥漫在胸腔里,弥漫在脑海中。
我在焦虑什么?
天蒙蒙亮,沉睡过去。
第五次迟到。
走到大厦楼下,鼓起勇气,仰头望去。
一个一个小窗户,隐约反射流光。
很高,真的很高。它在俯视我,能听到“哈哈”的笑声。
巨大的,无法承受的压抑。
脑袋“嗡嗡”响,缺氧,四周摇晃,眼球跳动。
书上这样说,颈部长期不良姿势使韧带增厚,骨质增生,曲度变直,椎间盘蜕变,造成脊髓,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的压迫而出现颈部疼痛,头晕恶心等症状,严重者可致瘫痪,多见于伏案工作者。
不管是否颈椎坏掉,我都憎恨这栋大厦,从第一天,就开始不可抑制地憎恨,让我每天喘不过气,艰难活在压抑中。
没有反抗,若干年过去,一次反抗都没有,是的,我生性懦弱,恨,却不敢离开。
今日,憎恨,到临界点。
坐在格子里,最好的结果是,在他的痛骂中倒地,抽搐死去,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一具尸体嘘寒问暖。
那也不好。
我说的是,如果有人对我嘘寒问暖,那也不好。
不会应付。
我不懂应付别人的关心,哪怕只是对我打个招呼,我也要花五秒钟时间来思考怎么回应对方,这样很不好。好在这种情况不常发生,没人愿意和我接触。
“砰”。
巨响,从经理办公室传来。
门打开,他低着头,走到格子前。
今天,他不会放过我。
“把昨天日报表给我。”
沙哑,阴沉,像破风箱。
他想怎么样?
“把昨天的日报表给我,听到没有?”
文件堆里翻找,五分钟,没找到,明明记得昨天晚上做了的。
他突然以极快速度,抓起我左手边一张纸,转身离开。
纸被提起瞬间,看到大标题,原来,日报表一直在眼皮底下。
他的脸,极苍白,望之生惧。
想起通往阴间的纸人。
哦,纸人,不会有这般沉重的脚步。
他不骂我了?可能要等等吧,等老总来了,在他面前骂我,嗯,他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