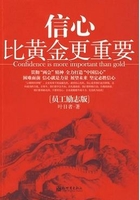张幺爷被白晓杨拉上来,一屁股坐在河坎上,望着白晓杨,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白晓杨神情温和地看着张幺爷,说:“幺爷,别坐地上,又潮又冷的。”
张幺爷不说话,眼眶继续泛红,说不出是激动还是兴奋。
白晓杨不理会张幺爷了,转身又去拉另外的人去了。
这时张幺爷才在白晓杨的背后哽咽着大声说:“你不该叫我幺爷,该叫我干爹的!老子担心死你了……”
张幺爷鼻子一酸,眼泪终于抑制不住如决堤的潮水般倾泻而下。
白晓杨扭过头,瞟了一眼张幺爷,漂亮的眼睛里全是调皮的微笑。
被对面枪声惊得魂魄出窍的愣小子们越慌越上不了河坎。白晓杨伸手去拉一个愣小子,愣小子用力过猛,差点儿把白晓杨拽下河坎。
一旁的兆丰边拉人边朝惊弓之鸟般的愣小子们说:“都别慌,一个一个地上来,他们没照着我们打。”
河对面的黄部长和袁子清都看见了从林子里出现的兆丰和白晓杨。
袁子清大声说:“兆丰!是兆丰!”
黄部长顿时朝一个民兵大声喊:“给老子瞄准点,打那个造反派,反革命!”
可那个民兵做出瞄准的姿势,半天不扣扳机。
心急火燎的黄部长一把从民兵手里抢过枪,歪着头瞄准,然后朝兆丰抠动了扳机。
子弹“嗖”的一声擦着兆丰的耳朵边飞了过去。兆丰一愣,瞟见黄部长正朝着自己再度瞄准,并拉动了枪栓,兆丰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此时的袁子清却突然间如梦方醒般地一把将黄部长端着的枪口朝天上一举。又是砰的一声枪响,黄部长朝空中放了一枪。
那些端枪的民兵们看见黄部长亲自端着枪在打,都住了手,看着黄部长。
袁子清朝黄部长大声喊道:“黄部长,打不得啊!你要犯大错误的啊!”
黄部长此时就像失去了理智一般,一脚将袁子清踹开,骂道:“锤子才打不得!老子打的是反革命、造反派、牛鬼蛇神!”说完又端起枪瞄准。
被踹在地上的袁子清跳了起来,上去一把薅住黄部长手里的枪,声嘶力竭地朝黄部长吼道:“黄部长,你听我一句,真的打不得!真的打不得啊!”
黄部长没有想到关键的时候袁子清会突然间出手阻拦他,和袁子清你来我往地抢起了枪。
袁子清边和黄部长抢枪边继续朝黄部长喊:“黄部长,你就听我这一回吧!他们真的是卧牛村的人,是老百姓,不是敌人、坏人!你不能用枪打他们。要是打错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黄部长的力气还真是较不过袁子清,几个来回就呼呼直喘,但依旧死死攥住枪托子不放地朝袁子清吼道:“袁子清,你狗日的究竟和谁是一伙的?”
袁子清也呼呼直喘地说:“老子和谁都不是一伙的,老子只和共产党是一伙的。”
黄部长终于撒了手,叉着腰杆盯着袁子清,像是盯一个怪物。
对面的张幺爷他们都上了河坎,各个脸色发白,气喘吁吁。他们心有余悸地看着河对面的黄部长和袁子清他们。
黄部长盯了一阵袁子清,狠狠地骂了一句:“回去老子再斗争你狗日的!走,回去!”说着转身走了。
袁子清没有动,失魂落魄地一屁股坐在河床上的一块鹅卵石上,望着宽阔干涸的河床发起了呆。
有两个民兵上去拉袁子清,被袁子清的手挡开了。
两个民兵没有再拉他,也跟着黄部长上了河坎走进了林子。
此时,冬日里的暖阳已经完全爬升起来,朝霞的绚丽和辉煌毫无保留地普照在河床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在霞光的映射下泛着神秘的光晕。那条在河床中央蜿蜒流动的清泉更是显得流光溢彩般的灵动秀丽,曲曲折折地流淌向远处一层浅浅的薄雾中。薄雾的深处,是郁郁葱葱的原始丛林……
这时,张子坤从一块卧牛般的大石头后面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来,肮脏的脸上还是憨痴痴的傻笑。
他的手里攥着一根朽木棍,突然跳上大石头,将朽木棍扛在肩膀上,滑稽地在大石头上面原地迈起了正步,声音宏亮地唱起了歌: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
就是保家乡……
张幺爷和张子恒看了一眼张子坤,一脸的无可奈何。
张子坤这时又跳下大石头,依旧扛着朽木棍,迈着正步唱着歌,沿着河床朝上游走去。
张幺爷有点担心地说:“子坤这是要上哪儿?”
张子恒说:“谁知道?疯疯癫癫的……”
一旁的白晓杨这时让背着庹观的愣小子把庹观放下来。
被平放在地上的庹观脸色蜡黄,就像一具死尸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