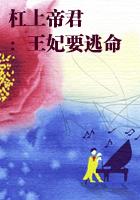德国的汉堡警察局,警官史特勒手持一份案件的卷宗走进了警长格奥格的办公室,将其恭恭敬敬地放在上司的桌上。
“警长,四月十四日夜十二时,位于塔丽雅剧院附近的一家超级商厦被窃去大量贵重物品,罪犯携赃驾车离去。现已捕获了A、B、C三名嫌疑犯在案,请指示!”
格奥格警长慈祥地看了得力助手一眼,翻开了案卷,只见史特勒在一张纸上写着:
事实1:除A、B、C三人外,已确证本案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牵连。
事实2:嫌疑犯C假如没有嫌疑犯A做帮凶,就不能到那家超级商厦作案盗窃。
事实3:B不会驾车。
请证实A是否犯了盗窃罪?
格奥格警长看后哈哈大笑,把史特勒笑得莫名其妙。然后,格奥格三言两语就把助手的疑问给解决了。
请问,警长是怎样断案的呢?
一柄扇子
古时候重庆府有个胡生利,在外做生意很久没有回来。四月的一天,他的妻子一个人在家,晚上被盗贼所杀。那天晚上下着小雨,人们在泥里拾到了一把扇子,上面的题词是王名赠给李前的。
王名不知道是谁,但李前,人们都认识,平时言行举止很不庄重,于是乡里的人都认定是他杀的人。李前被拘捕到公堂上,严刑拷打之下,他也承认了。
案子已经定了,一天,县令的夫人笑着对他说:“这个案子判错了。”于是,说出了一番话……
县令听后果然心服口服,以此去找罪犯,果然得到了事情的真相。
发黄的字据
北宋天圣年间,四川仁寿县的江知县上任不久,就受理了一桩田地诉讼案。
原告张某是个专管征收赋税的小吏,告他的邻居汪某无端赖占他家良田二十亩。
汪某申辩:“并无此事,这二十亩地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去年张某来我家收税,说如把田产划归他名下,可以不缴赋税,不服徭役。我正为缴不出赋税犯愁,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商定在字据上写着将我的田产过拨给他,但实际上田产还是属于我的。”
张某说:“十年前,汪家遇有急事,主动提出把二十亩地卖给我,有字据为证。”
知县接过字据,仔细审阅。这张叠起来的字据是用白宣纸写的,纸已发黄,纸的边缘也磨损了不少,像是年代很久了。知县将字据叠起又展开,展开又叠起。
突然,知县眼睛一亮,把惊堂木一拍,喝道:“大胆刁民,竟敢伪造字据,诓骗本县,还不从实招来!”
知县从字据上发现了什么破绽?
王之焕审黄狗
唐代著名诗人王之焕,在文安县做县官时,受理过这样一个案子。
三十多岁的民妇刘月娥哭诉:“公婆下世早,丈夫长年在外经商,家中只有我和小姑相伴生活。昨晚,我去邻家推碾,小姑在家缝补,我推碾回来刚进门,听着小姑喊救命,就急忙向屋里跑,在屋门口撞上个男人,厮打起来,抓了他几下,但我不是他的对手,让他跑掉了。进屋掌灯一看,小姑胸口扎着一把剪刀,已经断气了。”
王之焕问:“那人长什么样子?”
刘月娥说:“天很黑,没看清模样,只知他身高力大,上身光着。”
“当时你家院里还有别人吗?”王之焕又问。
“除了黄狗,家里没有喘气的了。”刘月娥答道。
“你家养的狗?”
“已经养三年了。”
“那天晚上回家,你没听见狗叫吗?”
“没有。”
这天下午,县衙差役在各乡贴出告示,县官明天要在城隍庙审黄狗。
第二天,好奇的人们蜂拥而来,将庙里挤了个水泄不通。王之焕见人进得差不多了,喝令关上庙门,然后命差役先后把小孩、妇女、老头轰出庙去。庙里只剩百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王之焕命令他们脱掉上衣,面对着墙站好。然后逐一查看,发现一个人的脊背上有两道红印子,经讯问,是刘月娥的街坊李二狗,正是他行凶杀人。
王之焕这次破案与审狗有什么关系呢?
咖啡杯之谜
从几天前,推理作家江川乱山先生就在M饭店埋头写小说。
一天晚上,他写不下去了,便在饭店附近散步,调剂精神,恰巧碰到私家侦探团五郎。
“啊,团君,难得见面。这副打扮,是在跟踪谁呀?”乱山先生盯着团侦探问道。
平日衣冠楚楚的团侦探,今晚穿着破旧的毛衣,戴着一顶毛线织的滑雪帽,拖着拖鞋,打扮得像个穷画家。
“这是为侦察而装扮的。你在这地方干什么?”
“和平日一样,闷在这饭店里当罐头呀。好久不见了,喝一杯怎么样?”
“对不起,我正在戒酒。”
“咖啡怎么样?这个饭店的咖啡很不错。”
“可是,我这种装扮进饭店,怪丢人的。”
“不要紧,可以在我的房间里招待。实际上,我正想请你帮忙。”乱山劝说道。他俩从登记处看不见的侧门进入饭店,上了电梯。
乱山先生的房间,是九楼的905号房,有一间不大的会客室和卧室。
“在这么高级的房间里写作呀!”团侦探像看稀奇似的打量着房间。
会客室的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稿纸和书本,两人进卧室后乱山先生向饭店里要了咖啡和三明治。
“我必须在下周交一篇短篇推理小说,但始终想不出饶有趣味的阴谋,难下笔呀,有什么素材吗?”乱川说。
“私家侦探处理的案子,都是些普通案子,对你写的推理小说没用。”
“随便谈谈。交稿期限马上到了,请帮帮忙。”
“既然说得这么急——”团侦探把最近处理的两三件案件告诉给乱山,但他不太感兴趣。
“没有更奇特的犯罪吗?”
“很难拼凑,如果有那种奇特的犯罪,我也不会做私家侦探,而去当作家了。”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啊,团君,杂志的记者来访,对不起,请坐坐吧。”
“如果打扰您,我先回去。”
“别这样,再和我聊聊,采访马上就结束,这段时间,请帮我想个新奇的犯罪。”
乱山先生自私地说完,把团侦探留在了卧室。他带上门后把记者迎入会客室。
记者拿出录音机,立即开始了采访,他发现卧室传出电视机的声音,迟疑了一下问道:“先生,有什么客人——”
“朋友来了。”乱山先生答道,但记者已贸然断定乱山带了女人,只采访了三十分钟便草草收场走了。
乱山先生回到卧室,团侦探正在看电视。
“让你久等了,很对不起。”乱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准备喝方才剩下的咖啡,一看桌上,忽然发现自己的咖啡杯不见了。
“哎,我的杯子呢?”
“不是刚才带到会客室去了吗?”
“不,不会,确实放在这儿。”尽管这样说,乱山还是到会客室找了一遍,没看见咖啡杯。
“一两个杯子算什么!”
“当然算不了什么,可事情太奇怪了。”
乱山到处寻找时,看到团侦探诡秘的微笑。
“啊,是你干的,把杯子藏起来了想骗我吧?”
“哪里的话,我一步也没离开卧室,如果怀疑,你就尽力找吧。”
乱山认真地开始寻找,因为是饭店的房间,也没什么地方可找,他在床下、桌子抽屉、电冰箱和衣柜中都找遍了,没发现咖啡杯。
“啊,我知道了,你从窗子扔出去了。”乱山打开窗户看着下面。
房间在九楼,距地面约三十米,夜晚,完全看不见地面。
团侦探微笑着说:“如果从窗口扔下去,杯子会摔得粉碎,我想搞点恶作剧,也不至于如此过分。”
这时,又有人敲门。
“谁?这种时候?”乱山先生一开门,只见饭店侍者站在门口,手中拿着白色的咖啡杯。
“我把杯子给您送来了。”
乱山目瞪口呆地问:“放在什么地方?”
“这房间下面的院子里。”
“院子里?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杯子?”
侍者让他看杯子外写的字,是特种笔迹:
把这个杯子送到905号房。谢谢!江川乱山。
“多谢,辛苦了。”团侦探斜视着呆立的乱山,把小费递给待者。年轻的侍者推辞了一下,还是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收下了。
“团君,一定是你干的,你收买了那个侍者,让他把杯子送来的吧?”
“没你这样的胡猜。今晚与你偶尔相遇,被你强拉到这家饭店,怎么可能事前与侍者商量呢?”
“我在接受采访时,你可以偷偷地给登记处挂电话呀。”
“那么,请你找登记处核查一下吧。”
乱山好奇心非常强烈,他立刻挂电话问登记处。
“怎么样?”团侦探微笑着问。
“你说得不错。”
“看吧,这个杯子一定是你喝咖啡的杯子,好好看看杯子边上,你是左撇子,用左手拿杯子喝咖啡,所以咖啡污痕在这边。正好与右撇子相反。”
“不错——但是,这个薄薄的瓷杯,怎么从九楼高高的窗户落到下面院子里的呢?说不定是你用绳子从窗户吊到院子里的吧?”
“那种长绳在哪里呢?我连根细绳都没有,如果把咖啡杯换上精巧的玻璃工艺品或翡翠工艺品,不就是一件有趣的窃案了吗?这手段可以写推理小说吧,而且,在这种场合,必须让读者知道,罪犯受过检查,没带绳子。我不打算写书,你慢慢思考吧,时间不早了,恕我失陪。”
说完,团侦探立刻回去了。
翌日早晨,团侦探被电话铃惊醒,电话是江川乱山先生打来的。
“团君,咖啡杯之谜被我解开了。”乱山兴奋地说。接着他说出了团侦探的手段。
“不错,一个晚上就解开了。不愧为推理作家呀。”
那么,读者们,私立侦探团五郎究竟用什么方法,从九楼把咖啡杯放到下面院子里的呢?
观星塔上的凶杀案
昨日清晨科学院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研究生严勤学死在观星塔最高的平台上,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经仔细检查,发现严勤学的右眼,被一根长约三厘米的细毒针刺过。在他的尸体旁边,有一枚沾满血迹的针。由现场情况看来,严勤学显然是自己把刺进眼中的毒针拔出来以后才死亡的。此事目前尚未对外公开,也没有查出任何线索,现在整个科学院已经为这件事起了很大的骚动。
观星塔是个独立单位,而且,下面的大门是锁着的,没有钥匙绝对无法打开,也没撬开的痕迹,严勤学可能是锁好大门才到平台上去的。所以我们推测凶手一定不是从钟楼的大门进去的。
这平台的位置是在四楼的南侧,离地面差不多有二十六公尺的高度,观星塔的旁边还有一条河流,自钟楼到对岸也有四十公尺的距离,昨夜又刮着很大的风,即使那凶手是从对岸用吹笛把细毒针发射过来,也不可能那么准地打到严勤学的右眼。
可是,严勤学却正是被此毒针打中右眼而死的。那么到底谁是凶手呢?又是用什么方法把人杀死的呢?这真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案件。
科学院的院长把严勤学的死亡,视为自杀事件处理,想在院内简单地替他办葬礼,可是,谁又能相信一向信仰坚强、好学不倦、对大自然充满热爱的研究生,竟会采用这种方式自杀呢?
这时科学院中的人员都议论纷纷,特别跟严勤学最接近的潘教授,更是不同意院方所下的定论,于是就展开了调查,决心揪出凶手,为严勤学伸冤报仇。
他在调查的过程中,知道严勤学为更好地研究太空中的一切,每晚都偷偷地在观星楼认真观察天上星星及月亮的活动,大风大雨也从不间断,这一切的表现,更坚定了潘教授的信心,更坚持了严勤学是被杀而不是自杀的看法。
潘教授调查了跟严勤学最接近的几个学生,又知道,严勤学是某富商之子,他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今年夏天,他父亲因病去世,严勤学打算将他所得到的那份遗产,全部捐给科学院。可是严勤学的弟弟却认为他这种做法相当愚蠢,他曾经威胁严勤学说:如果不马上停止这不智之举,他就要向法院提出控诉,禁止严勤学的继承权。
“在发生此案的前一天,严勤学的弟弟寄来了个小包裹,小包裹内装着什么东西,严勤学没有告诉任何人,昨天,我来清扫房间时,也没有看到那个小包裹,说不定,凶手是为了窃取小包裹,才对严勤学下毒手的。”院中的清洁工对潘授教说了以上的话。
年迈的潘教授此刻闭上双目,静静地思索着,又睁开眼睛,望着那水波款款的河水悠然地流淌。这时潘教授开始与警方商讨事件的真相。
“这是我照情形所作的推测,根据常识和观察力来判断案情,是不会相差太远的,在案情未公开之前,能不能叫人打捞此河,我虽有很妙的推理,但若没有证据,是没有人肯伏首认罪的,我这种推理,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警方于是对河进行了打捞,最后在河底找到了一个望远镜,这是一个长度仅四十厘米的望远镜。严勤学的弟弟送来的那个小包裹,一定就是这个望远镜!但这个望远镜怎会和杀人案扯上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