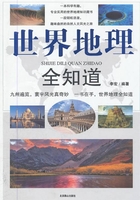(17)
[失控的雪糕]
我这几天明显的消沉下来了,就连豆头这个神经比电线杆还粗的人都发现了。
彼时还是在学校的图书馆的围墙后面,豆头的壁画已经画得七七八八了,我坐在草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他画着画着就停了下来,问我:“小麦,你最近怎么了?怎么如此颓废?难倒你也失恋了?”
不说这两个字还好,一说我就忍不住暴走,我从地上蹦了起来:“你才失恋,你们全家人都失恋!”骂着骂着我就红了眼眶,而被骂的豆头反之没有一点委屈,惊慌失措地看着我:“你怎么了,怎么就哭了?”
我昂起头,把眼泪憋了回去,扯着嗓子对豆头提议:“我们去喝酒吧?”他又一次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就像在看着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一样。
在豆头的监督下,我终究没有成功去酩酊大醉一场,他拉着我买了两盒三色雪糕坐在画室门口有一勺没一勺地挖着。
入冬已经好几天了,天气冷飕飕的,地板都有些凉。画室外贴着秦朗写的纸条:画室关门一天,明天再见。
我们是有钥匙的,但这也耐不住门是从里面反锁的。我们都猜,秦朗在里面。于是两个人就坐在了台阶上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往嘴里塞着雪糕。豆头很不能理解我这样诡异的行为,可是他没有问缘由,就这样陪着我,我第一次感觉其实有个像豆头一样傻愣愣的死党也不错。
吃完了雪糕后豆头去给我买灌汤包,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肉和油,他看着我目瞪口呆,可是我一点也不介意,一口就一个小汤包。就在我吃得满嘴都是油的时候,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从我们身边走过,豆头不停地扯着我的袖子,我凶他:“你干嘛!没见我在吃包子吗?”
话音刚落,画室的门就“吱”的一声被拉开了,那个女生站在画室门口,门内是我们满腮胡渣满身烟味的秦朗老师,他平静似水的眸子里没有焦点。
豆头小声地在我耳畔说:“喏,这就是老师的那个女朋友。”
我之前一直觉得豆头说话夸张成分比较多,直到亲眼看到那个女孩子我才知道他一点都没有夸张,她真的很漂亮,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沾了颜料的外套和牛仔裤,抹掉了嘴边的油腻腻,沮丧地拉着豆头准备开溜。可是秦朗的声音却像鬼魅一样冷冰冰地在我们身后响起:“小麦,豆头,你们给我站住。”
他看着我们,撂下那个漂亮的女孩子,任她尴尬地站在那里。
“秦朗,我有话和你说。”她的声音糯糯的软软的,我的公鸭嗓子和她简直没有可比性。
“可是我没话和你说。”我们的秦老师这样回答她。
[诡异的争吵]
“那个女孩子怎么来了?你不是说秦老师被甩了吗?”
“估计是她后悔了,回来找老师!”
“哼,他肯定不会吃回头草的,那种女人有什么好!”
“小麦,其实她好像还不错,说不定和老师有什么误会呢!”
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豆头:“你这个色鬼,见到漂亮女生就流口水!”
他涨红了脸看着我,支支吾吾了一句才挤出一句“你胡说”。
“我哪里胡说,你那天看到人家眼睛就直了!也不掂掂自己的分量,看上她就说嘛!我也不会取笑你的……”我就像针一样尖锐,从小到大他和我吵架从来就没有赢过我。我正沾沾自喜,豆头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愤恨地看着我,丢下一句“路小麦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就跑了。
我有些错愕地看着豆头的背影,心想他这是怎么了,但是我没有追上去,豆头同学是长跑冠军,而我的100米跑还没有过及格线,我能追上吗我。
我在豆头走了之后继续潜伏在离画室有五十来米远的电线杆之后,秦朗和那个漂亮的女生就站在画室的门口,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争吵,就这样两两相望,这一瞬间就让我想到了隔着银河的牛郎与织女,可是他们两个之间只隔着我和豆头吃完乱丢的雪糕盒子。
过了差不多一世纪那么久,我才听见秦朗缓缓地开口,隔得很远,他的声音也很小,可是我真的就听到了他的叹气声,他说:“昭昭,你走吧。”
那个昭昭的女孩子声音更是小,她喃喃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我只是看到她扯着我们老师脏兮兮的袖子却被他给甩开了。她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可是我想她应该是哭了吧。
秦朗并没有安慰她或是如何,而是绕过他朝我这个方向走来,就连画室的门都忘了锁。
我想要躲起来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看到了我,他拎着我的领子就把我提了起来,我才发现看起来瘦瘦弱弱的秦朗力气大得吓人,我慌张地看着他,指着身后红着眼睛看着我们的女孩子:“秦老师,她……”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而是拖着我往前走,手劲大得要将我的手腕碾碎。我很疼,我挣不开她,只好被他拖着横冲直闯地走了很远很远才停下来。
我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秦朗,小心翼翼地问:“老师,这里是哪里?”
他放开了我的手,盯着上面几道红红的印子,皱着眉头对我说:“抱歉。”可是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有些想吐血,他说的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好吧,如你们所见,我伟大敬爱的秦老师,拉着我这个无辜的学生华丽丽地迷路了。
[悲剧的画笔]
迷路了下场是秦朗带着我走了三个小时的路才绕回了我们的小画室。其实我们是可以问路的,但是秦朗因为心不在焉于是忘记了这件事,而我则是刻意故意不告诉他,就和他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迎着北风兜兜转转。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我怎么可能放弃。
在这三个小时里,秦朗终于告诉了我有关于他的故事,听完之后我恨不得将豆头拆骨入腹,他那是什么听力。秦朗所说的故事和豆头所说有天壤之别,虽然我更愿意去相信豆头说的那个版本。
秦朗来自农村,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家里没有钱无法让他上美院,于是他就出来打工了,边打工边赚钱给自己买画具,后来他又去了广场帮人画画,认识了张昭昭,就是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张昭昭的家里很有钱,父母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可是张昭昭还是义无反顾地和他在一起。
“那你们为什么分手?是因为她嫌弃你吗?还是她的父母使了手段让你们分开?”我想到了电视剧里都是这样演的。
可是他摇头了又再摇头,“都不是,只是我觉得有些累了,我没有房子车子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个破画室,还是租来的,我有什么资格和她在一起。”
我总算知道了豆头告诉我的那番话是出自哪里了。
“过段日子我我想关了画室,我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秦朗说完了这句后又开始沉默了,黑暗中我看着他波澜不惊的面孔,什么话也说不出。
什么都说不出。
就连我积攒了很多天的勇气,想要在这个混乱的夜里告诉他的话,也都没有说出来。
我和豆头的争吵并没有让我们的关系变坏,就在第二天他就乐呵呵地站在我家门口,等着我一起去上课了。壁画已经完成了,我们没有再逃课了,我坐在教室里不停地用画笔在纸上乱画着,豆头在后面踢着我的椅子。
我回过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有注意,手中的笔和本子就被数学老师抽了出来。那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在课室里大声地念着我纸上的字:秦朗秦朗秦朗。
我臊红了脸,他却一下子折断了我的画笔,用力地扔在了我的面前:“路小麦,你到底是来上课还是来画画,你们这些艺术生就这样,学了美术就当自己很了不起。你不想来就滚出去,这里少你一个人不少!”
他从来都不喜欢我,我知道。他曾经在班里发表过言论,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些不用努力就可以考上大学的艺术生了!我当时曾站起来告诉他,其实艺术生也要努力的,我们比普通学生还要付出多一倍的努力。
这是一个艺术班,我的发言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他从此恨透了我这个人。
我盯着地上的那支画笔,那是一只普通的2b铅笔,可是却是秦朗送我的,于是它就变得不普通了。
他叫我滚,于是我真的滚了。
我走到课室的门口他似乎又反悔了,气急败坏地喊我回去。
可是对不起,我滚远了。
[无奈的布偶]
我逃了,独自一人走了。
我没有回家,没有回画室,带着我的破书包和仅有的一百块钱就走了,途中我吃了豆头给我的,可是却被我嫌弃了扔在书包里的面包。
我走了很远的路去广场看人画画,一坐就在那里坐到了晚上。夜晚我不想回家,就住在了20块钱一晚的阴森森的旅馆,我住了四天,每天吃了5个五毛钱的包子。第四天晚上我躺在旅馆散发着古怪气味的木板床,想着我明天要不要去广场画画赚点钱吃饭,不然我就要在寒冬腊月里饿死和冻死。
我却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看到了秦朗,我以为是我的错觉,揉了揉眼睛他却还是站在这间只有五平方的小破屋里面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语气却柔和:“小麦,回家了,你的家人在到处找你,噢,还有豆头,都哭了好几次。”
我没有问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猜他应该也找我找得很辛苦。我慢慢地跟在他的身后一步步往家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气氛沉闷得可以压死一头牛,秦朗并没有开口责备我或问我为什么要出走,我却突然觉得委屈起来,我说老师我其实也不想做一个坏女生,可是我讨厌他们用那样的口气说我和我最喜欢的美术。
他突然停了下来,我没有注意,险些撞上他的后背。
“路小麦,只要是你觉得喜欢的,觉得对的就去做,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放弃,那样你就不是你了。”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只要你觉得对的,就去做。”
“可是你为什么要关了画室?”我忍不住嚷了起来:“难倒你敢说你不喜欢它吗?”
他叹气:“你不懂,走吧,你的家人和豆头都在等你。”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像只凶猛地野兽扑向他抱住了他的后背,由于用力太大,他险些被我撞到。我说老师我喜欢你,我好喜欢你。
“你别这样,我是你的老师。”
“你算什么老师,你都关掉画室了算什么老师!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你说只要我觉得对的就去做,可是你明明那么喜欢美术,为什么要关掉画室!”他掰开我的手,我却死命不松开,反而用更大的力气抱住了他,也不管这是在离我家不远的巷子外:“老师,我喜欢你啊。”
“别这样,小麦。”
我终于还是放手了,因为我看到了豆头,他抱着一只巨大的布偶站在离我们不远处,他笑得有些勉强:“小麦,送给你的,这是你喜欢的维尼熊,欢迎你回来。”
我看得出他难过了,我也难过了。
[悲伤的采购]
我回家了,但是没有人责骂我,包括我那个脾气暴躁也反对我学画的老爸。
后来我才知道是豆头找到了秦朗,秦朗来到了我家。那个时候我爸还在骂骂咧咧说找到我再也不能让我学画去,看我学出些什么东西来,是秦朗说服了我爸爸,还包下了寻找我的任务,整整几天都没有合上眼。
我回来了,我还是照常去学画,可是我拼命地躲避着秦朗,就像豆头拼命地逃避我。
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可是豆头还是没有来找我玩。于是我只好独自去找那个叫张昭昭的女孩子,其实也不用怎么找,因为她每天都会畏畏缩缩地画室附近徘徊着,只是从来都不靠近。
我去找她,气势汹汹地去,颓靡不堪地回。豆头不知道怎么发现了这件事,气急败坏地来找我:“路小麦,你怎么喜欢秦老师我不管,但是你怎么能去找那个女孩子的晦气呢!你怎么能这么坏!”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你电视看多了吧,你以为我去找她干嘛?”
“不是示威再找她麻烦吗?”
我没有理他,转身走了。
直到秦老师和那个女孩子和好之后,豆头才来找我道歉,甚至向我打探我同那个女孩子说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不过就说了秦朗对我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喜爱着,就算全世界都与你为敌又怎么样?
可是,老师对不起,我自己却做不到了。
我还是每天去画室学画带着那一群小萝卜头吵吵闹闹,还是每天回家后就做题复习等着高考,还是每个月去采购一次画室所需要的东西。
豆头要陪我去,我没有拒绝。
我和豆头一人抱着一箱颜料慢吞吞地回画室,他走在我身后小声嗫嚅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
夕阳下,豆头的脸蛋比晚霞还要红,他不知是害羞还是愤怒地大声喊了一句:路小麦,我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呀。
“我知道了。”
说完之后我就继续往前走,豆头颓靡地跟在我的身后。
我想,我每个月都去采购一次悲伤,再把它们统统关起来,总有一天那些不属于我的情感都会被我采购完。
等到那一天,我想我才能认真地对豆头说一句:喂,我们以后一起去大广场给人画画赚钱吧。
只是,你能不能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