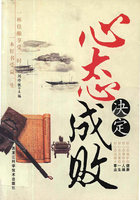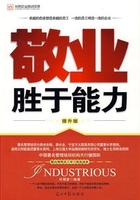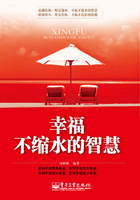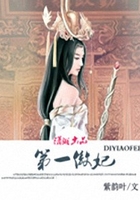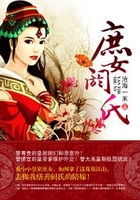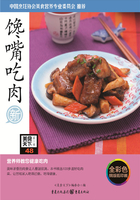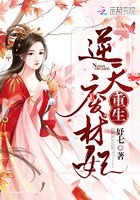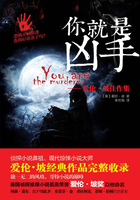而对于我们来说,不该停止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为了使自己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得出类拔萃;也不该连一本有关生命意义的书也不看,那样我们会渐渐失去做人的深度。
滋润心灵的精神食粮,永远不会嫌多。而读书,是滋润心灵、完善自我的唯一途径。读书也是讲究方法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
1.采众长
读书需要广涉群科、博采众长。宽打基础窄打墙,是读书方法之一。我们欲在任何一个领域中有大的建树,博通是必行之路。科学和艺术看来是相距甚远的领域,可也有许多相通之处。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索在回答“如何才能造就好的科学家”的提问时,他答道:“往往许多物理问题的解答并不在物理范围之内。涉猎多方面的学问可以提供广阔的思路,如多看看小说,有空去逛逛动物园也会有好处,可以帮助提高想象力,这和理解力、记忆力同样重要。假如你未看过大象,你能凭空想象得出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吗?对世界或人类活动中的事物形象掌握得越多,越有助于抽象思维。”
2.莫做书奴
书,本应是人的奴仆,为人所用。可有时却相反,因为有的人却成了书的奴隶,这不能不令人痛惜。不顾实际、死啃书本的人,甘作书奴,这样的人读书越多,却会变得越痴呆。因此,要善于驾驭书本,居高临下地读,而不要将自己埋进书本之中,被书淹没。你应占有书本,而不能为书本所左右、被它占有。有书就要去读,达到为我所用。有了书而不去阅读,就是莫大的悲哀。
3.择优而读
读书,需要选择。试想:一个经常在阅读沉思中与哲人、文豪倾心对语的人,与一个只喜爱读凶杀言情故事和明星花边轶闻的人,他们的精神空间是多么不同,他们显然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在茫茫书海中,我们要力求寻觅上乘之作、经典之作,要多读名著,多读“大书”。所谓经典名著、“大书”,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筛选。一些社会学家曾做过统计,其结论是:至少要横穿20年的阅读检验而未曾沉没,这样的著作方有资格称为经典、名著。择优读书,需要一种选择、琢磨工夫。我们应汲取前人的经验,将读书效率提高一个层次。
严文井说:“读书,人才更加像人。”在更多的时候,读书不只是与官财光荣相连,它是人的风骨的基石;它是文明的卫士,守卫在没有痰迹的风景线上;它是我们行为风范的精灵,不会使我们把商品和零钱扔给柜台外边的顾客,惹恼了他们后,还不知道为什么;它也是青春智力的储存器,使我们未来不至于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送给孩子一本书,上面画满强调线的却全是新人们认为最不深刻的地方;它也是人类经验的车船,就像培根描述的一样:“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富、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夸奖书籍的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和发明。”
能读书,是一种幸福;读好书,是一种幸福;从书中感悟我们的人生和理想,是更高境界的幸福。
信仰,是心灵安宁的指示牌
我们对一件事物的信仰,应当有助于发掘和解放我们的内在心灵。可以说实现自己的本性本身就在我们的信仰中。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信仰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是指人们对于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信奉和遵循,是统摄其他一切意志形式的最高意识形态。
信仰中的个体是自我不在自身的个体。由于信仰,个体的自我被寄宿在信仰对象那里。个体放弃他的自我——或者说个体的自我相信那个托管者比他把个体管得更好——他直接地请求托管。自我甘愿放弃自己,个体也服从自我甘愿听从信仰对象的安排。从这一点看,处在信仰状态的个体是超我的。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他就是信仰对象的代言者,而信仰对象则成为决定个体一切的基本力量。
迄今为止,任何信仰对象都是超乎群的普遍自我的对象。有些信仰对象希望普度众生,有些信仰对象希望救世济贫,还有些信仰对象希望传播普遍真理,它们都是超出个体的现实的理想世界,是为个体设定的理想的彼岸。其超我的特性是明显的。
印度著名的思想家,被誉为20世纪最卓越、最伟大的灵性导师克利希那穆提,在谈到对神的崇拜时说,“我们并不爱神,如果我们真的爱上帝,就根本不会有崇拜这件事,我们崇拜神是因为我们惧怕它,我们的心中只有惧怕而没有爱.庙宇、祭供、念珠,这些都不是神。是出于人类的虚荣及恐惧的产物。只有那些不快乐、充满恐惧的人才崇拜神。”这句话指出了我们大多数人对神的一些误解。很多人对神充满了依赖和恐惧,这样对神的崇拜和信仰反倒成了一种束缚。真正的信仰应当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本性。
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中说,宗教的职能不是去消灭我们的本性,而是去实现它。梵文Bodhidharma(音译“达摩”,意译“法”),在英文中通常译为“宗教”,而在印度的语言中却有更深刻的含义。“法”是万物最内在的本性,即本质,绝对的真理。“法”是我们行动的最终目标。这就好比说,种子的本性是包在壳里,只有通过某些特殊的奇迹,它才能长成树。种子的外观并不是种子的本性。它的本性是成为一棵树。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一粒种子,真正的信仰应当有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的本性,成长为一棵树,“冲破它的外壳,使其本身转化为朝气蓬勃的心灵上的嫩芽。在阳光和空气的哺育下,向四面八方伸出枝杈”,而不是将生命禁锢在种子的外壳之中。
在《人生的亲证》一书中,泰戈尔引用了《广林奥义书》的一首诗:“一个将最高神尊崇为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神的人并不了解自己,他就像从属于众神的一只动物。”泰戈尔认为,“人在精神上比他自己的外表更伟大,即他生活在无限的充裕中,这种充裕就是人的全部最崇高的东西,他的纯真,他的真理”。真正的信仰,当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伟大,成长和实现自我,而不是躲在神像之下需求庇护和慰藉。
周国平先生认为,“一切外在的信仰只是桥梁和诱饵,其价值就在于把人引向内心,过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神并非居住在宇宙间的某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是我们在内心中感悟到它。一个人的信仰之真假,分界也在于有没有这种内在的精神生活。伟大的信徒是那些有着伟大的内心世界的人,相反,一个全心全意相信天国或者来世的人,如果他没有内心生活,你就不能说他有真实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不在于标榜,也不在于膜拜神像,而是将自己引向内心,在一种虔诚的心境中,不断追求品德的完善,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