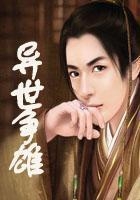“还有啊,家里老太太受不了刺激,好像疯了呢。”
“啧啧,这下子两个孩子都成这样了,这还怎么个活法啊。”
“你还别说,他们家不是一直都神神叨叨的嘛,我原来在帮忙做佣人的时候,晚上的还会听到那个老夫人跪在那几幅画像面前不知在哀求着什么东西呢,你说这不是见鬼了还是什么的呀,啧啧……”
“你不知道?这都是报应呀!听说原来这家呀,说是为了什么纯种的血统还真的害死过一个孩子呢……啧啧不会是什么先祖显灵要遭到报应了吧。”
“哎哎……”
“造孽哟……”
呵呵……
那漫长的月圆晴空仿佛席卷了天地般的嗤笑着,是在嘲讽着宅子,还是那在宅子里闭门不出的老主人呢?
没有人知道,他们只听说城西那个瞎了眼的老头每每在夕阳斜下的时候,都会点燃一根劣质的旱烟,幽幽然的抽着,伴着那青烟袅袅的声音缓缓传来:
这个世道,这个城里,这个宅子,可不是那么太平的啊。
而我们的故事,就像那山谷里的微风,带点阴冷般,或者是有些寒气逼人的,从这个有着些年份的宅子里幽幽吹来。
ACT 1 曲木
有蚊虫在耳旁嘶叫着的声响,像是认定了要和这夜的肃静顽抗到底,影暗中化为了墨绿色的一点,它们似乎也是饿了很久,满屋子寻找着自己的猎物。
没有感到一丝的疲惫,曲木却是老实地躺在床上,眼睛微微睁开,在漆黑的屋子里静静等待着午夜的来临,等待哥哥的回来。然后他听到钥匙转动锁孔的声响,便渐渐安下心来,他很想出去迎接,想对哥哥说声辛苦了,或者问好说声累不累,哪怕是鼓励的话也好,胡言乱语也好,只要能早些看见哥哥便好。
可现在除了平躺在这里不乱动,不要哥哥担心才是对的,其余的,他什么也做不到。
他很清楚自己在曲琛心中的分量,但似乎亲生哥哥却并不那么认为。
很快的,曲琛像往常一样推门而入,扭亮台灯,抱了抱他。“曲木,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好吗?我现在就帮你放洗澡水。”话还未说完紧接着便是他一声声的咳嗽,更像是要把整个肺部都要抽空般的痛苦难耐,咳得异常剧烈,昏暗的台灯下,他甚至能看见曲琛胸口上面积越来越大的阴影。
“曲木,你说如果人的赎罪能像清洗身躯这般简单该多好啊。”他自顾自的说着,边擦拭着对方的身体,尽管弟弟从来都不会回答。
曲木在黑暗中似乎动了动嘴唇,却依旧没有出声:
就算是哥哥也应该明白吧,不要去寻找那些没有问题的答案啊。
“在我失去所有的时候,你能拉我一把,让我好好面对,小木,你知道么,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曲木的脑海里似乎总会听见重复的话语,像是从山谷里飘出来的一般缥缈与捉摸不定,在不知多少年前似乎听到过与之相同的声音,他只是不记得了。
正因为哥哥在一直照顾着自己,哥哥一直在自己的身边,所以这是新的开始,回忆便应该留在历史的长河里让其销声匿迹。但若是反复不停毫无预知的这样呢喃在耳旁,久而久之他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哥哥帮自己做着按摩,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自己反而选择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蚊虫,那畜生怕是喝多了腥臭的血,肚子肿胀得似乎要破裂了。那些低等的生物,毫无头脑的只是贪婪眼前的利益,便是连性命都不要了。房间昏暗,只有哥哥帮他揉着脚踝的声音,对方的手指却情不自禁慢慢加大了力度。
哥,我疼。他声音微弱的连自己也听不清。
没有任何回应,哥哥的手很像绞肉机,似乎要将他的骨头一根根掰断。脚开始麻木,可是他没有办法。
在最初他还记得,那些厚厚的整整一叠的诊断书堆放在妈妈和哥哥的面前时,白衣天使面无表情的得出了最后的结果,“红斑狼疮,及时治疗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怪不得哥哥胸口前那些不正常颜色的斑块怎么也消失不去,怪不得哥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在充斥着消毒水的医生的办公室里,他看见了满面愧色几乎昏厥母亲,以及呆呆的站在原地表情怪异的哥哥。你甚至可以精准到预知他死亡的日期,却不能将他从死神的镰刀下拯救回来。
他拿着那份诊断书,看着仿佛已然被判了死刑的哥哥,猛然觉得眼前一片死寂沉沉的灰。
但那些是曾经的过往,现在的自己已不用为这些而烦恼了,只要自己的哥哥在身旁,心就会不可思议的安静下来。他曾经以为哥会信守诺言,但是却发现哥哥开始变得三心二意起来,对方的梦呓里清清楚楚,叫的不是他的名字。
“妈妈。”仿佛低低呻吟。
哥哥叨念着这个词的时候是痛苦的,他常常在黎明时分惊醒,洗手间便传来一声盖过一声的咳嗽。
哥哥又继续帮他揉着脚踝,絮絮叨叨,仿佛做功课一般,拼命要往他的脑子里塞东西。
笨蛋哥哥,你明知道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啊。
电话响了,终于结束了男子的喋喋不休。
“妈妈……”,他又听见了哥哥哽咽的声音,这个叫做“妈妈”的人,是不是哥哥很重要的人呢?是不是比自己更重要的人呢?他为这突如其来的想法而被吓了一跳,这个世界上,对于哥哥来说,又有谁是能比自己还要重要的人呢?他不禁害怕得打了个寒颤,哥哥,不要离开我。他对着自己的心说,哥哥,求求你,不要放弃我。
纵然是七海连天,也会干涸枯竭。
纵然是云荒万里,也会分崩离析。
这世间种种的生离死别,来了又去,有如潮汐。
只是那纷飞的爱恨别离,又怎能以这简简单单的“再见”二字作为永别的礼物呢?
那是他至亲的人,到头来,他也依旧不愿意在独自一人走下去。
ACT 2 曲琛
青年扣开了这个家的大门,曲琛这才想起,他已经有两年没有踏入这里了。
庭院里有大片大片的欧石楠,也正是到了快开花的好时节,淡粉色呈针状的花苞一朵连着一朵,若是仅供盆栽的话,那么景致便正好了,满院带着浓烈而略微刺鼻的花香包裹着他的嗅觉感官,昨晚那种无法呼吸般的压抑感又来了。
他没有想到,即使是重病了那么多年的母亲,却依旧能清醒的安排佣人来管理这些花草。那些都是他曾经非常喜欢的植物,欧石楠原本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常绿灌木,若是盆栽加工后便可入茶,清飘四溢,母亲更是喜欢不已,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将种子空运过来精心管理。
欧石楠,这些花依旧美丽,幼时他会和弟弟跑进庭院里玩耍,一定要等母亲托佣人来催促时才愿离开,时隔多年,却再无人来欣赏。
大厅里坐着苍老的妇人,由女佣照顾着,口水却一直不停的留出来,望着怀里的布娃娃,傻傻的笑着,“小琛,小琛,妈妈在这里呢。”
青年人心里很明显的被扎到了什么脆弱的地方,他有些吃力的蹲下身跪轮椅旁,握着老妇的手,“妈,那不是你的小琛,小琛在这里呢,小琛知错了,来看你了。”
那妇人的眼神突然就变了,推开他张牙舞爪的狂叫着,“胡说,你胡说,小琛哪里有错?错的是天地!错的是我,是我害了小琛,是我造的孽啊!”
她完全濒临崩溃的边缘,毫无顾忌的大喊大叫,而一旁被妇人推倒的曲琛又开始不停的咳出声来,只觉得内脏里一股腥味往上涌,再咳出来时,手里已多了一大摊的鲜血。
身旁的女佣也吃惊不小,只是唯唯诺诺的低声说着,“夫人这几天不太稳定,曲少爷你还是回来住吧,和二少爷一起……”。
她的话被撕心裂肺的咳声打断,罢罢,曲琛抹了抹嘴边的血,看来,已经是极限了啊。
女佣递过来一份文件,“这是夫人发病以前亲手拟的遗嘱,”她眼神奇怪的看了看曲琛,“少爷您过目一下。”
曲琛接过来,随手翻了翻,苦笑着起身,“妈妈,要不要去看看小木?”
仿佛是很飘忽的境地,时间竟是回到了那很多年前,他正在那后庭院落里玩耍,秋风萧瑟,风起落叶,他看见了一个少年,站在那庭院的中央,望着自己傻傻的笑着。
家里似乎平添就多出了这么一个弟弟,长相清秀,面容可爱,很是得其他亲戚的喜爱,只是他每每牵着弟弟去看母亲的时候,那富贵女子惊恐而慌张的脸庞,他一辈子都无法忘怀。
一场对外宣称引发了么子不幸去世的事件以后,从此那个家里没有任何人,再能知道这个弟弟的存在。
他却很喜欢这个自小就被母亲剥夺了自由的弟弟,虽然被母亲软禁在那间密室,却能懂事的叫着自己哥哥,还会开心的笑,总是能安静的坐在一旁,安静的听着自己所讲述的童话故事。
他不理解母亲为何要如此这样对待那个孩子,都是一个母亲生养的为何差距会这么大呢,给不了对方快乐的童年同时亦剥夺了对方的自由,为什么要将这些不幸降临在自己的弟弟身上呢。但那时他刚刚成年,在家中没有权势,也没有亲信,看着喜爱的弟弟,却无法帮忙。
而最为奇怪的是,母亲变得愈加的神神叨叨起来,经常会请一些法师或者道长来家里驱神做鬼,甚至不让自己询问那些缘由,反而总是口中喃喃有词的不知在说些什么东西,家中原本挂了好几幅先祖的画像也给取了下来,他只是偶尔听到佣人那里会讲诉着些许关于这些晚清时代的家中纷飞事物以及岁月过往,那个时候自己的年龄也小,似懂非懂的,也不得不受着母亲和家庭里的控制小心翼翼的不去触犯母亲的威严,晃晃不可终日一般闭紧嘴巴,老老实实不去过问某些绝对不能碰触的禁忌。
真实的谎言,如果你已经接受了那样的过去,那么就请好好将他带往坟墓。这是大户人家历经六朝不倒,长久不衰的,愚蠢也是最为直接的办法。
但是无法抑制的是岁月流逝,无法逃避的亦是时间年限,弟弟还在望不到边际的黑暗之中一天天的长大,而母亲却愈加的衰老下去,当他已经有能力将弟弟从那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迎接出来的时候,曲琛发现自己却已经力不从心了,而自己那亲爱的弟弟,已经变得自己仿佛已经认不出来一般的壮硕而高大。
最后一次了,五年来他的精力和身体已经全部达到极限,这最后的一件事,也了了自己的心愿吧。
“小木,小木,”曲木仿佛听到了悠远而苍老的呼唤,却不是属于哥哥的声音。那样平缓而慈祥的语调,似乎和梦境里的重叠在一起。
一直躁动不安的母亲看到躺在床上的曲木竟奇迹般的安静下来了,曲琛有些惊讶,却舒了口气。
母亲一直在用苍老的手抚摸着弟弟那因为未见阳光而显得苍白的脸颊,絮絮叨叨的说着某些过往,枯槁的面容也难得带着些温润的色彩。就这么一直说着,直到累了卷了,慢慢趴在曲木的身上睡着了。
曲琛颤抖着双手,拿起了电话,“是我,接夫人回去。”
他在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里漫无目的的走着,只觉着身子越来越沉重,冷风吹来,他感到了彻骨的寒意,停下脚步又剧烈的咳了起来,不想脖子上的吊坠断了,滑到了大街上。他惊恐的赶忙冲过来捡,确认无恙后满足般有些神经质的嘿嘿嘿笑了起来,吊坠上镶嵌的照片已发黑泛黄,那是母亲与弟弟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上的两人笑得却很尴尬,没有往常应该拥有的亲情所在。
只有这一件东西,自己应该可以带入坟墓吧,他神情恍惚的慢慢想着,却没看见路口飞速驶过来的车。
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飞了起来,抬眼便可看见浩瀚的苍穹,天空是深黑色的,太高太远,仰望似乎也抓不住什么,而自己心中的那一片虚无是怎么也挥之不去了。
他在血雾迷茫中好像看见了街边的曲木,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手,想去靠近对面的人。
“呐,曲木,妈妈说过,人死后体重会减少21克,那是灵魂的重量呢。”
他想喊,却什么也说不出。
“我呢,在我沉睡的瞬间,会不会是这样的呢?”也许不会吧,他只觉得身边突然围了很多很多人,都快要将对面的人挡住了,“曲木,五年前是不是上帝就已经把我的灵魂带走了呢?”
“妈妈还说过,如果受到了诅咒,那么连花也会变了颜色的,你知道么,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庭院里的花都变成草色的了。看来,就连欧石楠也不能原谅我了啊。”
他终于慢慢垂下眼,挣扎了这么久,他实在太累了。
失去意识的瞬间,他模模糊糊的,居然看见了曲木嘴边带着温柔而恬淡的笑容,那是自从自己将曲木变成废人之后从未见过的神情,仿佛他企盼了多年的救赎一般,更像盛开得茂盛的欧石楠,那片草色的欧石楠。
呐,我的弟弟,我想被宽恕。
我曾经,是那么那么的爱你。
ACT 3 曲木
“小木,小木,”那声音越来越接想曾经在睡梦中所听见的一样“在我失去所有时,你能帮我一把,让我好好面对。小木,你是妈妈的希望啊。”那个被自己称为母亲的女子死死的抓住曲木的手,并没发觉那只手显然毫无生气,也没注意到自己身后曲琛的脸色越来越青。
他就那么一直站在人来人往的喧嚣街旁,看着曲琛身边开出大朵大朵腥臭妖艳的花,他本不会站在这里的,按照人们的说法,现在的他应是毫无意识的。
他慢慢往回走,扔下了身后那一片血红,耳边充斥着许许多多的杂音,连他自己都奇怪那些为何过往还能如此清晰的印在脑海里。
他一直都是很听话的,对于母亲所有的要求,他都一一做到最好,他不知自己到底哪里比哥哥不足,即使做得再好,母亲永远也只是冷眼冷语,从不将其放在心上。
他一直默默忍受,以为如果长大,母亲便可多加关爱自己一些。
那时母亲身体已不太好,家里总是迷漫着浓烈的中药味,不多时,他惊讶的发现连哥哥也开始出现和母亲相同的症状,而且似乎比母亲还要严重的多,常常咳到晕厥送往医院,打了几针后略微有些好转,便再送回家。如此往复,他不知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久。后来他知道哥哥不幸遗传了母亲的病,所以也许是因为愧疚,母亲偏向哥哥一些呢?
每每在母亲对自己冷语相向时,他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或者是在抑制自己的愤怒。曲琛虽然身体不适,但至少他认为,那时毕竟还有哥哥是真正关怀自己的。
若不是他无意中看到了母亲亲手写下的遗书,说不定这些遥遥欲坠的平衡还能持续到他们所幻想的永远。
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房产,那些文字的落款处,全部只写了一人:曲琛。
和健健康康的自己相比,就算是可能会入土的人,他最后也是无法见证家族兴衰的掌门人,他太听话了,以至于母亲从未感受到他的不满,或者从心里就认为自己是不敢有这样的想法的。
可突然母亲对他似乎好了起来,脸上也挂着笑,还经常赞扬他的好,那天母亲同他在房间里谈话,“在我失去所有的时候,你能帮我一把,让我好好面对。小木,你是妈妈的希望啊。”话未说完他便听到了飞速下楼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哥哥。而迟钝的母亲却没有发现,仍是紧紧握着他的手,“妈妈要是不在了,哥哥就靠你照顾了,知道么?”
他终于绝望了,他也是母亲的亲生骨肉啊,为何对方从来就不曾好好的望过自己一眼,他的愿望已经卑微到连母亲都忽略的地步吗,看母亲的意思,他的身份便是挂着二少爷名字的终身佣人。曲琛没有听到后面的话,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其实不恨他的,偶尔满足一下虚荣心又有何不可?
直到他被哥哥亲手推下了楼梯,昏倒前,他终于悟出了曲琛眼里的愤怒,那里还有他从来都不曾知道过的空虚和嫉妒。映着哥哥胸前泛着紫黑色光芒的斑点,使他终于卑微而绝望的意识到,连那些曾经甚少拥有的关爱,都因这些而全部远去了。
也许哥哥也是寂寞的吧,那为什么不能了解自己呢?他们都如此渴望那份残缺的关爱,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医院里醒来后,他的双眼瞪着天花板,如果现在还是屈服着呢?他会比以前更为听话的,他要把属于自己的都要夺回来。妈妈不是讨厌他么,那么自己消失就好了,哥哥不是恨他么,自己如果已经脑死亡了呢,这个就是他满意的答案吧。
母亲彻底疯了,她从未想到已经板上钉钉的计划会被打破,曲琛不再刻意治疗自己的病,带着弟弟离开了家,那些他一时冲动所犯的罪,注定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弥补了。
他在床上一躺,就是五年的光阴。梦境里却总是会想起母亲这辈子对自己说过的唯一一句温暖的话,他的记忆却把最后那一句给抛弃了,也许即便是虚假的呢,他都想得到母亲哪怕是只有一天的关怀,而现在,什么都回不来了。
现在他拿着那份遗产公正,那里落款处的名字,全部被划掉改为了曲木,他轻笑了起来,那是哥哥的笔迹,把庞大的财产留给一个植物人,曲琛你也疯了么?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他的了,而到底是夺回母爱的证明呢,还是记忆中兄长的关爱呢,在空虚中连自己也弄不清了。那些记忆,终于成了他一生的谶语。
其实他首先并没有想过要报复的,他只是缺乏那些关爱,上天既然再给自己机会,那么他应当能享受到那些无法感知的关爱吧。他那庞大而富饶的家庭曾经没能给他带来幸福,家族刚刚起步的一百多年前,因为某个不明所以的命案,一个刚刚满五岁的孩子魂归了故里,那个孩子就是曾经的自己。而那个家里没有一人喜欢自己,因为他是家族长子与不知外头哪个野丫头结合的悲哀产物,是那名望家族不可磨灭的污点。
但他重生了,魂魄似乎并没有离开,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都开始可怜着这个从来没有得到关爱类似的温暖的自己,所以特意安排他没有去追寻着那个极乐的世界,转而选择了降临在这个家里的一个刚刚降生的幼小孩童身上。
他没有想过自己还能重新睁开双眼看着这个曾经彻底抛弃过自己的世界,尽管经过百年,岁月光阴斑驳着古老的庭院,聚散离合,可迎接他的新生的脸庞同那初始的时候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带着惶恐,终日沉沦。
ACT 4 母亲
都说一个生命的出生应当是世界上最为美妙的事情,但这个孩子带给我不是喜悦,不是幸福,我怀胎十月,疼痛了整整一天,当初醒来的时候看见的那张脸,却差点让我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实在是太像了……太像了。
虽然还仅仅只是个襁褓里的孩子,但那眉目,那唇线,那双眸的弧度,都与墙上那幅先祖的画像是如此接近。
我每天烧香拜佛,以为自己如此的接近了神明,结果……居然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劫数。
我以为只要将这孩子带往身边抚养,心底还有一丝丝渴望,或者是幻想,这个孩子,这个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的孩子,他不会变成索命的鬼魂,不会变成……亲手带着他的哥哥离开的死神。
可惜随着那孩子的年龄一天天长大,他脸上的棱角渐渐分明的时刻,我才终于发现,自己曾经的幻想是多么的可笑。
最先在家里发现这个孩子异常的是自己,的确,我是亲手将他带到这个世界的人,即便自己早就已经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在了自己大儿子身上,但那亲手抚养长大,看着身边人一点点蜕变成长血浓于水的敏感度是怎样也不能切断的。
那个孩子的脸,和那张挂在画像中的人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因为那是自然,他的体内流着的是他父亲的血液,但毕竟是百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些已经成为先辈祖辈们的恩恩怨怨与过往兴衰,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要想继续追究下去,可我却感到了最为深刻的恐慌,不知是害怕遭到报应,或者是害怕他会夺去自己的亲生儿子。
只可惜,现在的这些东西,我已经都得不到了。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会带给这个家庭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在我的模糊意识里,那个孩子的背影似乎从来都不是笔直的挺拔着身形,微微弯曲着不知在担心和不安着什么东西一般,我想伸手去抚摸开他眉心间的褶皱时,却才发现自己已经连手的力气都抬不起来了。
这个孩子早已经在我说不知道的地方长大长高,我没有去参与他成长的过程,就连最后一点的关怀都无法分给他。
因为那是曲家上千百年的诅咒,他的出生或许仅仅意味着曲琛的死亡。
小木,对不起。
妈妈其实很爱你,只是妈妈……已经没有能力再来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