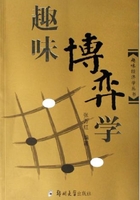表面上看来,在《新青年》一杆猎猎大纛旗下,集结的新文化战士都呈现出反封建、反世俗的一致性。但是在内里,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和而不同”一直相伴始终。鲁迅和毛泽东都说过类似的话:对欧美留学归来的学人,有一种莫名的不信任感。这种“莫名的不信任感”也许来自没有亲赴欧美留学的遗憾,也许来自留学欧美学子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那份长久的压抑在最后只能化成愤怒。在新文化运动领跑的四驾马车中,陈独秀由思想转向政治,想从亲身经历的实践中改变中国。胡适和周作人则由思想进入学理;而鲁迅,一直保持着精神的苦闷,在自言自语中自问自答,既无政治色彩,亦非学院气息。他们本应在文化构建上将一代新风开创到底,他们确实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为时不长便走向分裂,甚至决裂,这既有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也有各自留美与留日背景的天然对抗。
分裂的伏笔其实早已埋下:鲁迅早在《忆刘半农君》中就对胡适进行过辛辣的讽刺:“《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指名道姓的挖苦胡适,甚至将他形容为“烂泥的深渊”,怀有如此刻薄之心,这样的友谊已然裂痕初现,一旦遇到风波,反目成仇是必然的。风波总无法避免,说来就来了,这便是《新青年》的“双簧信”事件。
那还是一九一八年初,为推动文学革命,《新青年》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为读者王敬轩,搜集社会上复古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再由刘半农写回信逐一批驳,两封信同时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这出“双簧戏”,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胡适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很清楚,但他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次两人间的“短兵相接”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属于各说各的。在《新青年》的“双簧信”事件,以及“整理国故”上胡适与鲁迅都有过纷争。但相比以后的决裂来看,这些矛盾都属于皮毛。
一九二二年五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溥仪召见胡适,鲁迅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时,鲁迅才旧话重提:“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义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
从后来的文字里照见当初鲁迅的心情,已不仅仅是“莫名的不信任感”,而是有点“怀恨在心”。













![[茜茜公主]贵女启示录](http://c.dushuhao.com/images/book/2020/03/23/21142513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