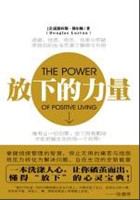我希望能有一部作品,完整的表现我们的看护同志,表现他们在战争中艰苦的献身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冬季,日寇在晋察冀扫荡了三个月.在晋察冀的部队和人民来说,这是一段极端艰难的时间。那一二年里,我们接连迂到了灾荒。反扫荡的转移,喿在九一八下午开始的,我们刚刚开完纪念会,就在会场上整理好队伍,并且发下了冬天的服装和鞋秣。我们背上这呰东西,在沙滩上行军,不断的撾水过河。情况一幵始就很紧张,来不及穿鞋,就手里提着。接连过了几条小河,队伍渐浙也就拉散了,我因为动作迟缓,拉在了后面。回头一看,只有一个女孩子,一只啣登在河边一块石头上,眼睛望着前边的队伍,匆忙的穿上鞋,就很快的跟上去了。
这女孩子有十六七岁,长的很瘦弱,背若和我一样多的东西,外加一个鼓鼓的药包,跑起路來;上枒不断的摇摆,活象山头邵棵风吹的小树。我猜她准足分配到我队上来的女看护。
快跑,小鬼!我追在后面笑着喊。
反正叫你拉不下!她回头笑了一下,这笑和她的年岁很不相称。她幼小的生活里一定受过什么压抑。我注意她的脚步,这孩子缠过脚,我明白了为什么过河以后,她总是要穿上鞋。
前面的队伍正趟过一条大河,爬到对面高山上去。头上是宽广的兰天。忽然听到飞机的叫声,立时就开始了扫射。我看见女孩子总忙脱了鞋,卷高裤腿,跑进水坦去,河水搭到她的腰那里,褂子全湿了,却用两只手高高举起了药包。她顺着水流歪歪斜斜的前进,走到河心,就叫水冲例,我赶紧跑上去,拉起她来,杜过河去。
我们刚登上岸,我觉得脚上一热,就钶了下来,血在沙滩上。
敌人的飞机一宜低飞着,扫射着河滩和岩石,扫伤了我的左脚。近处一个吋庄起火了,跑出很多人,妇女们来不及脱去鞋袜,抱着孩子跳进河里去。她们居住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从没见过飞机,更没听过这样刺耳的声音,敌人竟找到这里破环和威胁了她们的生活。她们嚷嚷着,招唤着家里的人,權我们快快上山。她们说,飞机在她们村庄下旦的时候那样低,在一棵老槐树下面钴了过去,一个人姑娘来不及闪躲,就叫飞机上的鬼子#从窗口打死了。女孩子告诉她们不要乱,让她们先走;又低着头,取出一个卫生包,替我果伤。在我们身边跑过的男人们也嚷嚷骂着,说等他们爬到山顶,飞机再低着身子飞,他们就抱大石头砸下它来!
扎住伤口,女孩子说:你把东西放下吧,我给你背!
哪甩的话,你这么小的人,会把你压死了哩!我勉强坫立起来,女孩子搀扶了我,挨上山去。
我们在山顶走笞,飞机走了,宽大清澈的河流在山下抟来转去。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上都是浈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我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踏,咽着唾沫走过去。
队上的医生老康,靠在前面一棵枣树上等我们。我们两个是好开玩笑的,每一见面,就都忍不住笑。我叫他雷佛那儿,这是因为那时医药条件困难,不管谁有什么外科破伤,他都是给开这一味药。他治病的特点是热情多于科学。他跑上来说:刚一出发你就负伤了!
可是并不光荣。我说广正在用腿用脚的时候,你看多倒霉。
每天宿营下来,我叫刘兰去给你換药!他说着替女孩子搀扶着我,刘兰才有工夫坐下去倒出她鞋里的沙土和石块。
这孩子很负责任,老康接着小声说,她是一个童养媳,婆家就在我们住过的那个村庄,从小挨打受气,忍饥挨冻。这次我们动员小看护,她的一个伙伴把她也叫了来,坚决参加。起初她婆婆不让,找了来。她说:这里有吃的有穿的,又能学习上进,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步?婆婆说:……你吃上饱饭,可不能变心,你长大成人,还妃俺家的媳妇她没有笞话:从这天起,每天晚上到付庄找好房子,刈兰就背爸药包笑填嘻的找了我米,叫我坐在炕上,她站在地下替我洗好伤口换好药,才回去洗脸休息。可是我的伤口并不见好,愦况越来越紧,行军越来越急迫4腿脚越来越不顶事。我成为队伍的累赘,心里很烦恼。第二天,黎明站队,组织上决定要杷我坚壁到远处一坐高山上去,叫刘兰跟随。我心见有些焦急,望望刘兰她却没有怨言。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面,人生地疏,叫一个女孩子带一个伤号,她该足更焦急的。
我们按着路线出犮,刘兰不知从哪里给我摸来一根木棍,天明我们进入了繁峙县的北部。这娃更加荒凉的地方坡高水急,道狭忖沿,在阴暗潮湿的山沟里转半天,看不见一个衬庄,迂不见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鸡叫。只有从沙滩上和过河的踏石上留下的毛驴蹄印或是粪块,才断定是人行的大进。
一到下午,肚里就饿了。天巳经快黑了,还看不见一个村庄。前面就是那坐高山了,在山底下,我要求坐下来休息一下,想到在爬这样莴山以前,最好能有一块玉米面饼子垫垫肚,然而我们并没有。希望就在山顶上。刘兰膣我开路。
振作精神,刘兰扶我上山去。我心里发慌,艰发黑,差不多忘记了脚痛。爬了半天,我饿的再也不能支持,迷胡过等到睁开眼,刘兰坐在我的身边,天巳经暗下来了。在我们头上,一棵茂密的酸枣树,累累的红艳的酸枣在晚风里摇摆。我一时闻到了枣儿的香味和钳味。刘兰也正眼巴巴望着酸枣,捫头蹙的很高。孴见我醒来,她很高兴,说:同忐,到了这个地步,摘一把酸枣儿吃,该不算犯纪律吧。
我笑着摇摇头!她伸过手去就虏下一把,送到我咀钽,她也按连吞下几把。我发觉她一同吞下了枣核和叶子,枣刺划玻了她的手掌。
吞吃了酸枣,有了精神和力還,在苍茫的夜色里遇到了山顶的村庄,有一片起伏的成熟的莜麦,象流劫的水银。还有一所场院,一个男人下身穿着棉裤,上兑光着膀子,高举着连枷!在他身旁有一个年轻的妇女用簸箕迎凤扬送着丈夫则刚打下的粮食,她的上身只穿着一件红色的兜肚。
我同刘兰就住在这小小的山庄上。进村以后,刘兰叫我坐在宁头休息,她去找上关系,打扫了房子,然后才把我安排到炕上。接着她又做饭烧炕,冼净吃饭的锅,煮刀剪,消苺药棉……弄到半夜,她才到对过妇救会主任老四屋里去睡觉。
这一晚,我听着五台山顶的风声,远处杉林里的狼叫,一时睡不着,却并没符感觉不安。我们是四海为家的,我们是以一切人民为兄弟姐妹的。从炕头的窗口望过去,刘兰和老四也没有睡,两个人的影子在窗纸上摇动。她们在拉着家常:你们从哪里来呀?
从很远的地方,
邵病人是谁呀?
我们队上一个干部。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宥护。
是大脉先生吗?给我看看病吧!
什么病呀,尔先和我学说学说,过几天,我们的医生就过来了广就是咱们妇道的病呀……下面的话,我就听不清。可是接着我就听见,老四也是一个童养媳,十四岁上成的亲,今年二十四岁了,还没有一个小孩。老四说:我们这山顶顶上的人家,就是难得有个娃,要不就是养不下,要不就是活不大刘兰说:这是因为我们结婚太早,生活苦,又不知迓卫生,以前我也是个童养媳……接卷两个人就诉起苦来,你疼我,我疼你的闹了多半夜才睡觉。
因为刘兰还不会做莜而,老四就派了两泣妇女来邦忙。她们都穿着白徂布棉裤、黑羊皮沃,她们好象从来没冼过脸,那两只手,也只有在给我们合面和搓窝窝的过程里才弄洁白,那些脏东西,全合到我们的饭食里去了。这一顿饭,我和刘兰吃起来,全很恶心,刘兰说:你身体好些的时候,多教我认几个字吧,我要给她们讲讲卫辻课。
不多几天,她这讲习班就成立起来,每天晚上,有十几个青年妇女集在老四屋里,对刘兰讲的问题发生很大的兴趣。刘兰告诉她们,她们生痫的根沅就在她们都是邛一块脏布包上灰土做月经带,用过了,就塞到淨房里,下次再用,一用二三年。刘兰告诉她们要把布洗净,放在干净地。
你看刘兰多干净!妇女们笑着说广我们向你学习!
从此,我看见这扭妇女们,每天都洗洗手脸,有的并学着我们的样子,在棉祅和皮衣里衬上一件单褂。我觉得刘兰把文化带给了这小小的山庄,它立刻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并给她们的后代造福。
有空,刘兰就邦她们到地里去收庄稼,她有时带回一些野韭菜、野运:、野蒜,包莜面饺子,改善我的伙食;有时带回一些玉黍秸,叫我当甜棒吃,好补充我身体里缺少的糖分。有一次,她不知道从哪里捉来几条小沙鱼。这样高的山上能有小鱼,已经新鲜叫老四看见了,活象宥见蛇一样,无论如何不叫我吃,她说那会把我毒死,更不叫在她家铹里来煮。
不久就下了火雪,我们都穿上了新棉衣,刘兰要在我的和她的祅领上缝上一个白衬领。她坐在炕上缝着,笑着说她还是头一次穿这样表三新的棉祅裤,母亲一辈子也没享过这个福。叫她呑来,八路军的生活好多了,这山庄上谁也没有我们这一套棉衣。
下了大雪,消息闭塞。我写了一封信,和大臥上联系,叫刘兰交给村长,派一个人送到区上去。刘兰回来说,这样大雪,村长派不动人,要等踏开道了才能送去。我的伤口正因为下雪发痛,一听就火了,我说:你再去把忖长叫来,我教育教育他!刘兰说:下了这样大学,连路上都不好走,山路上,雪能埋了人;这里人们穿着又少,人家是有困难!有困难就得克服!我大声说,我们就没困难过:我们跑到这山顶顶上来,技饿受冻为的谁呀!你说为的谁呀?刘兰冷笑着,挨饿受冻?我们每天两顿饱饭,一天要烧六十斤毛柴,是谁供给的呀!你怎么了!我欠起身来,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
咱们是工作关系,你是病人,我是看护,谁也不能压迫谁!刘兰硬沸梆的说。
小鬼!我抓起在火盆里烤着的一个山药,装作要向她脸上打去,她一闪,气的脸发白;说:你是干部,你打人骂人广说罢就转身出去了。
我很懊海:在炕上齟来复去。外面凤声很大,雪又打着窗纸,火盆里的火弱了,炕也凉了,伤口更痛的厉害。我在心里检讨着自己的过错。
老四推门进来,带着浑身的雪,她说,怎么了呀,同志?你们刘兰一个人跑到村口那里啼哭,这么大风大雪!
你快去把她叫来,我央告备老四广刚才我们吵了架。你对她说,完全是我的错误!
老四才慌忙的去叫她。这一晚上,她没到我屋里来。
第二天,风住天晴,到了换药的时候,刘兰来了,还是戈着。我向她陪了很多不是,她却一句话也没说,给我细心的換上药,就又拿起那封信,找村长去了。
接到大队来信,要我转移,当夜刘兰去动员担架。她拄着一根棍子,背着我们全部的东西,头上包着一決手巾,护住耳朵和脸,在冰雪擦滑的路上,穿着一双硬底山鞋,一步―个响声,迎着大风大雪跟在我的担架后面……这个大娘,住在小官亭西头路北一处破院的小北屋驭。这院里一共住若三家,都是贫农。
大娘生了三个女儿。她的小北屋一共是两间,在外间屋放若一架织布机,是从她母亲手里得来的。
机子从木匠手豇出生到现在,整整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间,我们祖闆的历史有过重大的变化,这机子却陪泮了三代的女人;陪伴她们痛苦,陪伴她们希望。它叫小锅台烟熏火燎,全身变成黑色的了。它眼望着大娘在生产以前,用一角破席堵住窗台的风口;在生产以后,拆毁了半个破鸡笸才煮熟一碗半饭汤。它春见大娘的两个女儿在出嫁的头一天晚上,才在机子上织成一条陪送的花裤。一百年来,它没有听见过歌声。
大娘小时是卖给这家的。卖给人家,并不是找到了什么富户。这一带有些外乡的单身汉,给地主家当长工,苦到四五十岁上,有些落项的就花钱癸个女人,名义上是制件衣裳,实际上就是女孩子的身价。丈夫四兀十,女人十三西,那些汉子都苦的象浇干了的水畦一样,不上几年就死了,留下儿女,就又走母亲的珞。
大姐是打十三岁上,卖给西张岗一个挑货郎担的河南人,丈夫成天住村野小店,她也就限着溜墙根串后沿。二姐十四上卖给东张岗拉虫好的大黑三,过门以后学的好吃懒做,打火抽烟,自从丈夫死了,男女关系也很乱。
两个女儿虽说嫁了人,大娘并没有得到依靠,还得时常牵挂着。好在小官亭离东西张岗全不远,大娘想念她们了,不管刮风下雨,就背上柴禾筐,走在漫天野地里,一边捡着亘根谷楂,一边去看望女儿。
到了大女儿那里,女婿不在家,就邦她打整打整孩子们!拾掇拾掇零捽活!到了二姑娘那里,看见她缺吃的没烧的,责骂她几句,临走还得杷拾的一筐谷楂,倒在她的火炕了。
大娘受苦,可是个结实人,快乐人,两只大脚板,走在路上,好象不着地,千斤的重祖,并没有能把她压倒。快六十了,牙口很齐全,硬饼子小葱,一晈就两断,在人面前还好吃个炒豆什么的。不管十冬腊月,只要有太阳,她就把纺车搬到院里纺线,和那些十几岁的女孩子们,很能说笑到一处。
她到底赶上了好年头,冀中区从打日本那天起,就举起了革命的红旗!
二姑娘一多儿的婚韦,也不能和闵个姐姐一祥了!
打日本那年,多儿刚十岁。十岁上,她巳经能够烧火做饭,拉磨推碾,下地拾柴禾,上树虏榆钱,织布纺线,邦娘生产。
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把人民的特别是妇女的旧道路铲平,把新道路在她们的眼前铺好。
她开始同孩子们一块到学校里去。认识宁儿好!大娘说,给多儿缝了个书包,买了块石板,在红饼子上抹了香油,叫她吃了上学去。
十二上她当儿童团,十五上她当自卫队,那年全区的妇女自卫队验操,她投的手榴弹最远。
经过抗战胜利,经过平分土地,她今年十八岁了。
多儿正在发育,几年间,不断有人来给她说婆家。
姐姐常常是姝妹的媒人,她们对多儿的婚事都很关心。皆月里,大姐分了房子地,就和丈夫商量:从我过门,逢年过节,也没给娘送过一个大浅的东西,我们过的穷日子,自己的吃穿还愁不来,她自然不会怪罪咱。今年总算足宽绰些了,我想到集上买点舡西,上娘家去一趟,顺便给小三的婆家说停当了没有。
丈夫遥个老实热情的人,答应的很高兴。到集上买了一串麻糖,十个柿子,冋来自己又摊上几个炉糕儿,字个红包袱果了,大姐就到小官亭来。
到了娘家,正赶上二姐也来了,她说村里正在改造她的懒婆獭汉。
多儿从冬学里回来,怀里抱着一本书,她的身子发宵的勻称结实,椚眼里透着秀气。姣儿几个围坐在炕上说话,一下就转到她的婚事上去。开头,这是个小型的诉苦会,六妲说可不能再象她那时候,二姐说可不能再象她那柞子;多儿把书摊在膝盖上,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