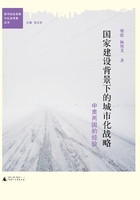彭家煌
晴朗的星期日的上午,他和她还没起床,对门晒台上的竹篙响了,他无目的的偶然抬头瞅了一眼,依然睡下,口里咕噜着。“这宵,要弄个帘子才行。”她也抬头看了一下,没说什么。因为那不过是个娘姨模样的女人,和他,相形之下,彰然的不能成为一对,而且这是移居后初次的发现,也不便说什么,只是在那“没说什么”里,形势仍然有几分严重。
约莫隔了十多分钟,第二次的竹篙响了,他躺着没动,她愤然的爬起,走近窗前,两目眈眈的盯着对门晒台上的女人,那女人很怯羞的将脸子隐在悬着的衣服后面,偶然偷视了一下,一面仍然晒她的衣服。
“贱货,不要脸的烂污东西,清晨八早就站在晒台上看,有什么好看!贱货!”她指手蹬脚的骂,等晒台上的女人下去了,又板起面孔对着他说:“这种女人不如到四马路去拉人,倒爽快得多!骂了好几句才下去呢,不要脸的东西!喂,昨天你说寄一封挂号信,信又没有寄,钱呢,拿来!”
“钱买了香烟,怎么样,又见鬼啦!”他朝她翻了一眼,仍然看他的书。
“像你们这种臭男子什么女人都要的,钱总是给那烂污的女人骗去了咯,这种女人几个铜板也要的!”
“你真见了鬼啦,无缘无故的骂别人,当心人家吵上了门噢!”他愤然的说。
“如果吵上门来,你看我打她出去。”她更凶的说。
他不再回话,只看他的书,室内寂静了,她找不着对手,便东摸西扯的收拾一切,只是每隔了几分钟,眼睛仍是向对门的晒台横扫着,而且每次上楼都这样。
他俩是经过长期恋爱而结合的,不知如何,老是为着像这样的空中楼阁而闹着,而且吃过许多的苦。他虽则思想很新,但每回吵闹,不曾有真凭实据落到她手里,然而她依旧是一回不了一回的闹。“妒嫉是美德,”人们对于妇女多是原谅着,但贞洁的男子看来,不免觉著有“人格上受了损失”的感慨吧!彼此间浓厚的爱情不免因女人们的“弄巧反拙”而淡薄了吧!
夕阳西下时,全弄堂里的晒台上都先后的有竹篙声,许是烂污的女人有日暮途穷之感,趁着斜晖努力的在勾引着野男子吧!他为了尿涨,几步跳上楼,在晒台的一角撒了一泡尿,瞩眺了一回远景,便掏出一本《桃色的云》专程的朗诵:
相思的朋友呵,
等候着什么而不来的呢?
太阳下去,月亮出来了,
等候着什么而不来的呢?
没有看见恋之光吗?
没有懂得胸的凄凉吗?
快来吧,等候着,
朋友们呵,相思的朋友呵。
“踢踏,踢踏”的,她赶上楼了,她在楼下听了一会,听见歌声,听见竹篙声才赶上楼来的。她上了晒台,失了魂的东张西望,看不见什么,只有前楼对面的晒台有竹篙声,但是屋瓦障着,看不见她早上教训过的那女人。
“唱什么,你,饿狗,一听见竹篙响就赶上楼,你这人,唉,堕落到这样子!唉,那了得呵;对门那女人倒不见得怎样坏,就是你这东西坏透啦,唉!”她晕头晕脑的只是咒,脸涨红了,急得只蹬脚。
“早上就说对门的女人坏,现在又是我坏了。听得竹蒿响就赴上来,赶上来怎么样?她在那边,这里看得见吗?真是鬼闷了头!”
“那末,你唱的什么?什么相思相思的。”
“桃色的云,桃色的云,你看明白啦再闹,哼,真是……”
那时,娘姨盛了饭上楼,关照着他们,他们各自不服的勉强就了坐,他口渴,叫娘姨泡了一口茶,静默了一会,他只吹着茶大惊失色的说:
“啊哟,不得了,不得了,茶杯里起了风波啦!”
她起首吓了一跳,既而,伸出指头在他的额上重重的按了一下,啐了一口,含羞的低了头,眼帘上还留着未干的半滴泪珠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