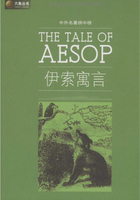“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一大标志,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也无不与工具的突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自身的进步史,就是工具的改造史、创造史。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学科研究课程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必须在转变思想提高认识的同时首先解决理论工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比我们明智得多,在我们还在用米尺度量微米并且为谁得出的数据更精确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人家的学科理论工具早已精确到了纳米,在认识高度统一的基础上用纳米技术开发并开始运用自己的纳米教学工具,并且早已获得了巨大成功。
西方人善于理性思辨,善于通过思辨制造先进的思辨工具,进一步提高国民的理性思辨能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人家的学科研究与教学自然会成功。我们中国人向来重感性轻理性,重感觉轻思辨,自己制造不出理性的思辨工具,也因为眼光问题,难以理解因而认识不到人家工具的先进性,不肯拿来为我所用。工具难以有什么实质性突破,我们只能原地打转,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学科研究自然难以进步。与其同时,到了实践领域,由于缺乏先进科学理论的导引,没有得心应手操作性较强的教学工具,认识与行为的混乱不堪,教学效率的“少慢差费”也便成为了一种必然。
就语文或者说语言学科的教学而言,人家的“纳米”理论工具就是运用理性分辨出的“形式”,人家教学的“纳米”工具就是“形式训练”,人家学科研究与教学的成功标志就是我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教学质量。
“形式训练”是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在语言(语文)教学领域的自然反映。作为18世纪启蒙主义的一种延伸,新人文主义在教学论上采取了“形式训练”的立场,而形式训练说是由笛卡儿等哲学家的唯理论,特别是康德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与论理学所构成的。这些唯理主义与批判主义将素材与思维、感觉与悟性、感性与理性二元化地区别对立起来,提出了思维和理性的“形式”,用以区别认识与行为的“实质”。形式训练的本质表现于以语言为中介,实现概念的大量扩充、规则的精确思考、客观逻辑的快速使用——形式训练就是以语言形式训练为依托的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形式训练。
在形式训练理论的认识系统中,其实存在着三种既有本质区别又关系密切的“形式”:一是“言语形式”;一是“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形式”;一是思维和理性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指的是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形式语言符号,是形式训练最重要的中介性“依托”。第二种指的是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相对稳定的形式思维模式,思维和理性的形式模式,或者说认知结构形式。这种“形式”同“言语形式”是一种表里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内化与外化的关系。形形色色的“言语形式”客观存在于丰富多彩的言语作品之中,人就是借助言语作品,通过人为的努力不断认知理解领悟言语形式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根据”,进而将其吸收内化逐渐构建自己的认知结构的(实现“概念的大量扩充”)——所谓思维和理性的“形式”,或者说人的思维形式,指的就是主体不断建构过程中某一时段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的形式。另一方面,主体的“思维形式模式”一旦稳定,交际或表达实践行为过程中,这“思维形式”便会自觉干预,让主体根据表达(内容)需要从头脑储备的“言语形式”中理性选择(选择的当然是当时主体自认为最恰当最贴切的“形式”,亦即实现“规则的精确思考”),交际或表达一旦客观化(以口语,或者书面语亦即文章形式呈现),“思维形式”便外化成了具体的言语作品的形式,亦即“言语形式”。第三种实际上指的是“形式运用”的“形式”,就是形式思维或者说悟性与理性思维模式运用的过程(亦即“客观逻辑的快速使用”)形式。前两种“形式”存在内化与外化的关系,而无论内化还是外化,其实都存在一个形式选择运用的过程,“思维形式”一旦相对稳定化,这个过程自然就会相对模式化,或者说相对形式化。有一点需要指出,人的认知结构形式可以自然建构,但完善的速度与质量显然不会太好,不如通过人为努力;主体个体可以自己理性建构,但个人能力毕竟有限,不如通过训练或者说“教学”,接受教师并且通过教师接受更多人或者说前人总结出的经验成果的持续不断的有效提醒——这实际上也便是语文学科教学存在的价值意义。所谓的形式训练,目的就是不断地优化这个形式运用的过程(亦即,完善这个形式运用的模式),而这个过程优化或者说这一过程模式不断完善化的过程显然是与主体形式思维或者说悟性与理性思维模式的建构完善的过程是高度统一的。形式训练以人类有着共性的生理与心理基础,这生理与心理又都是可以并且事实上也是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发展,特别是人的心理结构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科学训练人为建构完善为理论依据,通过加强对形式语言符号的认知与使用,致力于形式思维模式的不断建构与完善的。
上面三种“形式”其实都是西方人人为“二元化地区别对立”的产物,或者说是理性思辨的结果。“言语形式”对应的是形式语言,或者说符号语言,与语言承载的对象——“内容”,亦即我们所谓的语文现象、文化现象、人文现象等等相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文以载道”,其中的“文”即“言语形式”,“道”即“言语内容”。同样,“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形式”对应的是思维的形式,与思维自身运行必须借助的物质材料——思维承载的内容,如思想、意识、认识、感受、经验等等——相对。思维和理性的“形式”对应的是一种过程形式,亦即人理解把握“语言形式”后理性选择自觉运用这种“语言形式”进行思维的过程模式,与这一过程“生成”的“成果”(亦即认识与行为的“实质”)相对。
我们都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那么,工具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是运用,是形式,是其运用的形式!工具需要有内容材料构成,工具处理的是内容方面的材料,运用的成果也是以内容的形式存在的,可是,这些都不能等同于工具,我们不能将工具与构成工具的材料、工具承载的内容、工具运用以及运用的结果混为一谈。撇开纷纭的外在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工具都是以某种形式的形式存在的,其本质取决于其形式运用。我们现在谈论的语文工具,其物质基础显然是语言,语文其实就是一种语言工具。那么,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承载文化传承文明的工具,可是,语言承载思想承载文化本身却不是思想或文化,思想文化是语言承载的对象,亦即其介入生活后生成的言语作品的内容,语言本身只能是“形式”的“工具”,是舍弃言语作品具体内容后概括抽象其丰富多彩的“形式”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其性质与存在价值并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运用实践过程中的指导与规范作用——以前我们所谓的“工具论”失败的教训恰恰在于,我们只关注语言本身,而没有充分关照其运用实践,在运用实践过程中让其发挥其指导规范作用。
大家可能觉得笔者的阐释有些别扭,那是因为我们其实大都严重缺乏“二元化地区别对立”的意识,只关注事物的外在形态,却常常忽略其性质的本质区别的缘故。为了说得能够通俗一些,关于“工具”,我们这里不妨打个比方。比如,在我们面前,有实实在在并且完全一样的两把壶,一把用来盛茶水,一把用来做装饰品,那么,前者是“实用工具壶”,而后者就不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里,“壶”是为了用来盛茶水的,后者的性质(运用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异,彻底异化成了“装饰工具壶”,其本质属性与花瓶、与字画之类的东西反而没有了本质区别。
在我们传统的“工具论”的课堂里,语言成了“装饰工具壶”,而不是“实用工具壶”——我们所谓的“工具论”是彻头彻尾的伪“工具论”!
文字与口语都是记录传达语言的符号工具;语言本身显然也是一种符号工具,记录思维成果的工具;思维呢,也是工具,是人自我认识与表达的工具。前面已经说过,工具本身都是形式的,西方人为什么还要在“思维”、“语言”、“语言符号”等前面加上“形式”二字呢?是为了一种强调,一种提醒,特别强调特别提醒这里是人为“二元化地区别对立”的结果,特别强调特别提醒现在的认识方式与传统的不同,特别提醒特别强调“二元化地区别对立”的价值与意义——我们没有接受这种提醒,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的认识实际上还停留在人家的18世纪以前。
形式训练之“以语言为中介”,就是以形式语言符号为中介,以言语形式为中介,借助“中介”目的是为了构建人的形式思维模式。形形色色的“形式”客观存在于丰富多彩的言语作品之中,要以其作为中介性工具建构完善人的形式思维模式,还需要“训练”来完成。所谓的“训练”,实际上就是“教学”,“教”就是不断提供理性的提醒,“学”就是让学生不断接受这些理性的“提醒”,尽快将这些客观存在的“言语形式”认知理解吸收内化,储备于头脑之中,以备运用时理性选择自觉运用。“形式”储备越丰富,“形式”运用越理性,个体的形式思维模式建构得就越完善,就越能够保障思维和理性运用过程“形式”的质量,语文能力自然就越强。
言语形式内化为思维的形式需要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思维的形式外化为言语形式也需要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有过程才能有结果或者说成果,有高品质的过程才可能产生高品质的成果。我们与形式训练认识的最大区别在于,形式训练紧紧盯着形式运用的这个过程,亦即思维和理性的“形式”,我们则紧紧盯着这个过程的结果或者说所谓的成果,亦即认识与行为的“实质”。通俗一点说,中西方都关注语文工具,但人家在关注工具、关注工具运用成果的同时更关注这个工具自身的建构完善与工具运用过程的优化,致力于这一工具运用水平的提高,我们则只是看见了工具,现实的工具,工具的现实,因为工具是使用的便只是关心其运用现实,关心其现实运用“生成”的“成果”,而根本没有意识到,工具及工具运用的过程也是需要提升与优化的。比如,我们现在的时髦课堂上特别追求的是“个性”,是“生成”,是“创新”“创造”,这与西方语文界的追求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我们关注的是所谓个性化的“生成”现实与个性化的“创新”“创造”现实,工具运用能力方面追求的则是一种自然的“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只是满足于“个性”现实的自然呈现,却忘记这个过程的实质是思维工具与其外化的语言工具的运用,这一现实的提升因而忽视呈现过程的优化,我们的目的能否达到,其实完全取决于学生的天分与造化,我们几乎已经彻底放弃了我们教师的责任,我们教学的责任;形式训练关注的则是“个性”“生成”的“过程”与品质,强调的是人为努力,或者说负责任的“训练”(或者说“教学”),人家立足的是语言运用现实,考虑的是如何提升语言运用的品质,所以特别关注高品质“个性”生成、存在的“共性”基础,致力于学生相关心理机制的建构,关注并致力于这个建构过程的优化,亦即,特别关注如何才能高质量“生成”,如何高品质“创新”“创造”——所谓的“训练”或者说“教学”其实就是不断地给予学生理性的提醒,提醒其工具的理性理解准确把握以及运用的理性自觉。如果理解了这一点,不难发现,西方的语言教学普遍采用追求“共性”心理基础的形式训练,人家培养出的学生却大都有着光彩照人的“个性”魅力,我们的语文教学实质上总是在大讲特讲什么“个性”,除了个别的例外,整体而言,学生高品质的“个性”却越来越萎缩,并非偶然。
语文(语言)运用的起点是内容,终点也是内容,运用过程也离不开内容,但这一运用的“过程”却是形式的;语文能力实际上便是语文运用的能力,运用语文思维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一能力实际上体现于语文形式运用的过程。比如,我们平时所说的“有感而发”,所“感”(开发)的对象是内容的,“发”(发表)出的是思想感受情感态度等内容方面的东西,“发”的过程中自然也离不开对内容的分析辨别判断筛选,可是,“发”过程中体现出的语文能力却都是形式的:“发”(开发——分析辨别判断筛选——发表)是一种形式思维运用的过程,语言运用的过程,语文思维运用的过程,亦即运用理性收集选择整理筛选内容材料然后选择语言逻辑条理准确形象表达出来的过程,主体语文能力可以说完全体现于这一过程本身的质量。表面上看,语文(语言)能力往往借助言语作品来量化评价,可是,言语作品的质量却取决于这一作品产生过程的质量,能力首先外化于过程,我们只是借助已经客观化的言语作品,评价的其实还是主体驾驭这个过程的能力水平。语文能力显然不能看说了些什么,而是要看如何说的;如何说,体现的其实正是形式选择过程及这一过程的质量。语文能力的实质是行为主体驾驭语文(语言)的能力,亦即驾驭这个过程的能力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只是能力体现的一种工具性的凭借,而不是这一能力本身。
理性分辨是认识深入的前提,也是“创造”新的理论工具的前提。认识深入了提高了,有了先进的理论工具,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真正的深入,真正的进步。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向来讲究“道可道,非常道”,强调“意在言外”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严重弱化了国民的理性意识,压制了我们理性思辨能力。由于缺乏起码的人为努力,我们的理性运用与提高几乎都完全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甚至,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人家为什么要“二元化地区别对立”,当然也就难以理解“二元化地区别对立”的内涵与意义。我们的学术研究至今仍然广泛存在概念内涵不清、概念杂糅甚至偷换概念司空见惯的浅薄现象,许多简单的事实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分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