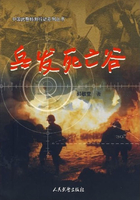王翰《饮马长城窟》诗中有云:“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骐驎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
对清廷统一天山南北的战争,早年的仲则颇多赞颂。除了《少年行》之外,仲则还作了一首《拟饮马长城窟》称颂其事。他当时的心气和愿景,我在开篇时已经做过剖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这首《拟饮马长城窟》和下一篇中会提到的《杂咏》组诗,是在差不多的时期写成的,约在乾隆三十一年,仲则十八岁时。因而我觉得是可以合看的,如此大略可梳理出他少年时的志愿和伴随着思索产生的复杂情绪,探知他性格思想的某些根源。
据仲则的挚友洪亮吉(字稚存)所撰的《黄君行状》记载:“亮吉携母孺人所授汉乐府锓本(刻本)……君见而嗜之,约共效其体,日数篇。”仲则甫一试笔,已让亮吉叹服,惊为天人。他后来写《江北诗话》,以仲则为例阐述诗的奥妙:“诗定不关学,沧浪之言,吾信矣。”诗是不可学的,靠天资而成,严羽的话我信了。
仲则与稚存为同乡,稚存幼时,其母蒋氏携其兄弟二人,寄寓仲则外祖父家,两家隔溪而居,自幼相识。两人正式订交是在乾隆三十一年,是年,两人同就童子试,于江阴逆旅中重逢之后,结为终生挚友。
仲则落落难群,个性狷介,不善与人交往,唯独与稚存的友情持续了一生。每当仲则忧难时,稚存总是毫不犹豫施以援手。这当中既有总角之交的亲热,也有自幼同窗的感情,更因对仲则才华的折服。
在稚存处看到的汉乐府刻本,激发了仲则的诗人天性。他便如拨云见日、大梦初醒,终于找到与自己志趣相契的事。与洪亮吉相约,效仿乐府笔法,每日数篇。这一部分诗作,是当时所作拟作的一部分,诗中所叙之事,未必是作者实有的经历,仅仅是借古人事,抒情言志。
洪亮吉在《玉尘集》中记道:青少年时期的仲则“读书击剑,有古侠士风”。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首《拟饮马长城窟》,看一看这位少年书生,如何在书斋中以笔为剑,点墨成兵,指点他心中的江山——秦城苍苍汉月白,秋风饮马城边窟。骷髅出土绣碧花,犹道秦时筑城卒。秦皇筑城非不仁,汉武开边亦可人。遮断玉关朝遣戍,长驱青海夜生尘。祁连封后焉支失,绝漠愁胡眼流血。残星点点散牛羊,霜天萧萧动觱篥。
闻道官家重首功,轻车仍拜未央宫。从此北庭常保塞,几曾南向敢关弓?射生旧日云中守,列帐传呼赐牛酒。三时禾黍种连云,四月桃花开马首。城郭安西净扫除,蒲桃天马贡长途。太平不用封侯相,卫霍于今只读书。
这诗的前四句不过是化用前人旧句,铺陈其意罢了,言秦汉人边役之苦,要害在此句:“秦皇筑城非不仁,汉武开边亦可人。”这一句定下全诗的基调,须知,此时的黄仲则是赞颂“合理”战争和“必要”的征戍的,连那沾染了碧苔的枯骨,在他眼中亦不过是历史的风尘旧迹罢了。
我想,此时乐府里的悲怨,古辞里的凄怆,并未影响他兴致勃勃的展望。他看见的是旌旗猎猎遮断玉关,车马萧萧长驱青海。他可不见征夫孤单的身影、思妇盈盈的泪眼。他看见的是名将功成安邦定国的辉煌,看不到战败一方溃败逃散的凄惶。
从不同角度看待历史会得出不同结论,解读有时并非那么绝对。秦皇筑长城,命蒙恬守边,使匈奴退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放牧,勇士不敢张弓射箭报仇。汉武帝遣良将开边,驱逐外患至大漠深处,极大地稳固和拓展了疆界。这些都是后来名垂青史、史笔称颂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却不见得是立竿见影的好事,穷兵黩武,国家疲敝,对外兴兵耗损了大量财力、民力,加速了秦的灭亡和汉的衰败。
贾谊在《过秦论》中精辟地阐述道:“秦王足已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汉代的开国者目睹了暴政的危害,是从秦的暴戾统治中挣扎挣脱,求生成功的人,所以汉初几代的统治者汲取教训,奉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与民休养生息。不折腾,就是心疼老百姓了。
相比于帝王的治世之功,我更惊叹于中国老百姓承受灾难的能力和复原能力,不管经过多漫长惨烈的战乱,只要给他们三五十年的喘息时间,民生很快就能得到恢复。从汉高祖刘邦时的“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到汉武帝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烂不可食”,经过三四代人的经营,国力已稳步回升,效果是显著的。
最关键是武帝时军马有了六十万匹,这与开国时只有军马三千匹,天子的车驾连四匹纯色的白马都凑不齐,王侯将相只能乘牛车出行上朝的寒酸劲不可同日而语。
有了强盛的国力和丰富的战备资源才可对匈奴展开反攻,夺回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对西域地区有全面的控制力,才有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盛。仲则诗云:“祁连封后焉支失,绝漠愁胡眼流血。”可以从匈奴人悲歌长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得到验证。
“残星点点散牛羊,霜天萧萧动觱篥。”觱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乐器,名称可能是由突厥语或匈奴语直接音译过来。其形质朴,竖吹,其声高亢凄厉。唐张祜有一首很艳美的诗或可抵消一下这种乐器带来的苍凉。
一管妙清商,纤红玉指长。雪藤新换束,霞锦旋抽囊。
并揭声犹远,深含曲未央。坐中知密顾,微笑是周郎。
——《觱篥》
这可看作觱篥留在我记忆里最初的印象。大唐的悠扬雍容,化解了这种乐器与生俱来的悲意,竟可成为婉转含情之物,但当我身在新疆的草原上,我所能想到的不是玉堂绮宴,公子美人含情顾盼。
即使是春浓花茂的时候,我心底依然有挥之不去的哀愁,需要竭力回忆、仔细辨认,才能寻见那些过往。
我总是不自觉想起这些过往的战事,马蹄踏过的,仿佛不是这片土地,而是我的心头,胡笳惊起的,不是胜利的自豪,而是千年不散的乡愁。
天空明净深蓝,草野一碧万顷,河水奔流不息,群山巍峨高壮,这一切的一切,时而温柔,时而峻烈,浩荡起伏成一曲悠扬古老的长歌,令人闻歌欲泪,思之欲归。
对自由奔放、心性热烈的民族而言,马上就是他们的家园和天下,荣誉感是他们生存的信念。他们奔走如风,到处征战,他们的存在曾经对中原有着致命的威胁,可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啊!血液里的骄傲!一旦被驯服,被汉化,这个民族的特性也就随之消除了。就像狼与狗,狼永远做不到狗的忠诚温顺,狗也永远不能了解狼的自豪和骄傲。
溃败不是不悲的,即使是能征好战的游牧民族。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匈奴被迫远徙漠北,东汉时内部分化,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与汉人融合,北匈奴,诗中所言的“北庭”远遁大漠,则又是另一番风云故事了。
“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疆土不可能一成不变,你争我夺,恩怨如何数算?
何况战争,哪有什么必要的战争呢?有的只是可以避免,却不能避免的战争。战争总是起于欲望,在彼是义,在此是不义,左右不过各执一词罢了。
战端一旦开启,其后战祸绵延,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胜或负,受苦受创最深的,始终是黎民百姓。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纵然胜了,亦只不过是一时,留下孤城嶙峋,白骨成堆,人世间生离死别、无穷憾恨却是长久。早知百年后胡汉皆枯骨,厮杀争斗又有何益?
站在胜利者的角度,黄仲则赞颂道:“闻道官家重首功,轻车仍拜未央宫。从此北庭常保塞,几曾南向敢关弓?”战胜之后,汉代设西域都护府,唐代设安西都护府。与前代做法相似,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之乱后亦设立伊犁将军管理新疆地区的军政事务,驻惠远城。
定边将军兆惠在平定回部叛乱时立下大功,回朝之后的饮宴上,吟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乾隆帝震怒,训斥道:谁是胡马!我大清就是从关外入主中原!幸亏这不是你作的诗句,不然饶不了你!此时正是清朝加强思想禁锢、大兴文字狱的时候,即使是有大功在身的兆惠亦只能战战兢兢伏地请罪。
乾隆是精明的,他知道兆惠此言一旦流传可能造成的影响。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已逾百年,民间“华夷之辨”的争端依然甚嚣尘上。他需要维护统治地位的合法性,防止汉人的民族情绪被煽动起来。虽然清朝的统治者选择接纳了汉文化,但在他心里,并不曾真正信任汉人。
我不合时宜地想起这个插曲,是因为仲则诗中借古颂今,饱含激情对盛世武功进行赞誉:“射生旧日云中守,列帐传呼赐牛酒。三时禾黍种连云,四月桃花开马首。城郭安西净扫除,蒲桃天马贡长途。”好一片边境安宁、万国来朝的胜景!
这几句可以作为边塞诗单看,用典之娴熟,造境之开阔绚烂,笔力不弱于唐人,这是我至为欣赏仲则诗才的地方。只是读着不免为书生的单纯可惜,自以为生逢盛世,安享太平,殊不知,在统治者心里,始终作怪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幻想是读书人的精神食粮。要是没有这点支撑,不想着反清复明,共襄义举,不知道清初那些明末遗民怎么打发日子。
现在是“盛世”了,早已忘却前朝。黄仲则正幻想着为明君所用。书生在纸上一往情深,略带惆怅地谈论道:“太平不用封侯相,卫霍于今只读书。”这是在称美统治者的功业,感慨太平时日缺少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可曾知晓?即使是功勋彪炳如卫青、霍去病,亦不过是帝王手中的棋子、心中的犬马,即便是为他生儿育女的枕边人卫子夫,一旦失宠见嫉,也免不了自杀了却残生。这份恩荣,不要也罢!
他可曾知晓?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是最频繁的。乾隆当了六十年皇帝,诗文之狱一百三十多起,平均下来一年两件,涉案者有官、有吏、有平民。有文辞专美者,亦有文理不通者,思想清理的剑锋所及,殃及者无数,下场如何只待圣心裁夺,但看龙颜是否震怒。
我不知道仲则这番热情洋溢颂圣之心,会被如何看待,幸好他没有因言获罪。
他可曾知晓?为统治者高呼胜利歌功颂德是愚蠢的,过分宣扬民族主义更是狭隘的,要持以冷静之心。
他可曾知晓?外患岂是一劳永逸可以灭绝的?明朝打退了强盛一时的蒙古,却免不了被女真所灭。清中后期闭关锁国,也没能封得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