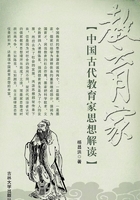文/李华伟
那个夜班的晚上我被一个孩子的眼神打动得柔情似水,母爱深浓,我不停地变着各种方式哄她,希望她能停止哭泣。
墙是白色的,灯光是白色的,她躺着打点滴的床也是白色的,孩子的脸色却因为费劲的哭泣通红,眼泪和鼻涕在孩子的脸上纵横,汗水把孩子的小脑袋上不多的头发染得也是湿漉漉的。
陪同孩子来的有三个人,一男一女和一老妇人。一直抱着孩子从挂号看病拿药到观察室来打点滴的都是那老妇人,起初我以为那对男女是孩子的爸妈,可当他们等孩子打上输液以后就一起走了。孩子个头很大我以为有一岁多快两岁的孩子其实才刚满十一个月,我不禁心疼起这幼小的孩子来。和孩子的婆婆聊起来才知孩子才从深圳由她带回来,水土不服拉肚子拉得厉害,原来胖胖的模样已瘦得不成样子了。孩子在深圳打工的父母听说后准备回来接。
由于孩子不住地哭,头皮针开始鼓包,婴幼儿针是很不好一针见血的,我这时不得不和孩子的婆婆一搭没搭的哄孩子,我从心底不想给孩子扎第二针,但鼓包的地方越鼓越大,我不得不对孩子重新扎针。
带小孩子打过点滴的父母肯定都知道那简直都像一场屠杀的过程,也许我有点夸张,为一个孩子打头皮针最少得三个大人,一个捉住手一个摁住腿一个按着头让护士扎针。初为人父母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几个不掉泪的。这对弱小来说真的是一种残忍的帮助。
也许我的叙述很平淡但是请你相信这是我职业精神的质的升华。
每天我是那么机械地做好我的工作,不就一针见血吗?每天习惯了孩子的哭闹,甚至不耐烦时还会埋怨孩子父母不会哄孩子。尽管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我的心在工作中几乎是麻木而又机械的。知道吗?这样的一种状态尽管是态度温和,言语轻柔,却整个一个机器人行动。
那天晚上也许是那个孩子长得原本惹人怜爱,一双眼睛总是那么无助地甚至是胆怯而又想寻找依赖地望着看她的人:也许是因为她的父母不在她是在寻找妈妈的眼睛爸爸的眼睛。我真的不忍心再给她扎第二针,我请了一块当班的同事重新给她打点滴。孩子已经哭得筋疲力尽,当开始摁住她的小手小腿的时候她歪起脑袋看正摁住她的婆婆,然后又使劲哭开了,她的婆婆这时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一个多么无助的孩子,需要关爱的孩子,她的妈妈如果在,她今晚是不是不会哭的这么厉害,病房里其他孩子不都在妈妈的怀里安静地打着点滴,哭也是短暂的。我忍不住动情地喊着就像喊我的孩子一样,宝宝,没事的,一会就好了。我用我的眼睛去捕捉她的眼睛,一边用心的呼唤着,宝宝没事的。我想孩子感觉到了另一个妈妈的呼唤,她真的有片刻的安静,眼睛一动不动的望着我,任我的手轻轻摩挲她的小脸蛋为她擦去眼泪鼻涕和汗水。进针的时候她居然没有哭,只扭捏了一下身体。
也许是她终于明白我到底不是她妈妈,挂上点滴后她又在她婆婆怀里不住地啼哭,我又想是不是因为拉肚子肚子疼,不住的没话找话逗她,宝宝是不是小肚肚疼,来,阿姨揉揉好吗?我一边给别的小朋友打针拔针一边逗着大一点的小朋友大声的和她说话;闲下来片刻我就拿个纸板挡着脸和她捉迷藏;我眼睛对着眼睛的逗她说话,十一个月的孩子正是想急于发音的时候;在点滴快完的时候孩子安静温柔的睡着了。
从那个夜班之后,我看所有的孩子就有种母亲般的爱从心底自然流露,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愿意和他们认真的交流,哪怕一个关爱鼓励的眼神,因为他们是那么一群柔嫩的生命,我真的希望我是他们眼里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