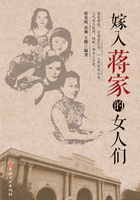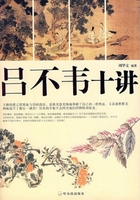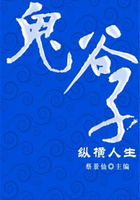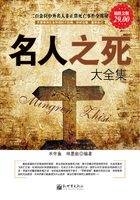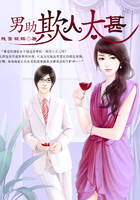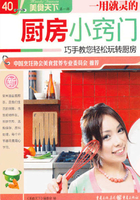梁漱溟晚年在谈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写作思路时,他回忆父亲并未像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家庭那样,要以《论语》《孟子》《诗经》等古籍开蒙,而是古今中外之书,任由儿子浏览,“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响,而从我好为观察思索的头脑,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厌世出世一路去了”;而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之正脉的主流的儒家孔门思想理趣却与此相反,如全部《论语》都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如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贫而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颇有新鲜之感,乃恍然识得中印两方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合起来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发展现世幸福的社会风尚,岂不昭昭然其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乎”。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出版后的第二年,梁漱溟在《我是怎样一个人?》一文中,一再申明自己并非学者,诚如他该书1921年第一版“自序”中所言: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有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要说的话。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沾滞的脾气,而有这本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条意义去走。因其如此,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变,愈收愈多,愈来愈变,就成为今天这样子。我自始不知道什么叫哲学,而要去讲它;是待我这样做过后,旁人告诉我说:“你讲的这是哲学”,然后我才晓得。我思想的变迁,我很愿意说出来给大家听。不过此次来不及,……我要作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把它贡献给旁人。这便是我不要谈学问而结果谈到学问;我不是著书立说,而是说我想要说的话的缘故。
正因为如此,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版再版的过程中,积极回应学界的评论,既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又不断在讨论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修正自己不准确有偏向的观点。例如,他在出版导言中所说:“到今日西方学术界思想输入的几何?固有的东方学术思想发挥者何人?……除横冲直撞的新思想家就是不知死活的旧头脑……”指名道姓地诘问***和胡适:你们说的那些宽慰人心的好话根据何在?
梁培恕认为:父亲那时便走上了一条崎岖的路--和新派辩论。在这里有一句潜台词,诘难旧派不会遭到反诘难。
在西方冲击下的中国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实际并且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梁漱溟在书中这样回顾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冲击:“这为东方文化浸润最深的国民(暗指中国人),不同凡众,要他领纳西方化是大不易。逼得急了,只肯截取一二,总不肯整个地承受”,这见之于同治、光绪年间设船厂、练海军等。甲午战败“始又种下观念变更的动机”,把眼光移到学术、教育、实业与政治制度上。看出问题在政治制度“较前可算得一大进步”;在光绪二十年到民国初年都是这个思想。人们不曾留意这种制度是什么精神的产物,与东方化“是何等凿而不入”,民国成立至今,闹了八年才晓得既不是坚甲利兵的问题,也不是政治制度问题,实实在在是因为两个文化根本不同。这时“方始有人注意到改革思想”,“把西方化从根本上引入”。中国人用了六十年才找到根本上。
这里的“方始有人”,是指《新青年》派。
接着,梁漱溟认为《新青年》派提出问题只是受到全世界在学西方这种大势的鼓动,自己还没有彻底弄懂就讲了起来。他们更有一项过失,那就是敷衍搪塞,说门面话。
这本书的导言和第一章绪论,几乎是一个内容:批评没有根据就说话,说门面话。
在绪论的第一小节中,从批评“吾友李守常”开始,接下来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守常)在所作《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里,把东方文化归结为“静的精神”,西方文化归结为“动的精神”。比喻东方文明不适合于西方文明好像是“以半死不活之人驾飞行艇,使发昏带醉之人驭摩托车”。以这样的精神治理国家社会“是世间最可怖之事”。“李先生的话说得很痛快,他很觉得东西文化根本之不同”,必须把静的精神根本扫荡。只因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来中国先后都说了一些肯定东方文化否定西方文化以及两者各有优点之类的话,影响到社会上说这类话的人多起来。李文还引用日本人北聆吉的《论东西文化之融合》讲融合的必要。文章结尾处说:“东西两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从先前的有定论转为论而不断,猜度着将来两大文明将会调和。
梁漱溟指出:“我总寻不出他们以什么见地把东方文化抬到与西方文化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地位与那融合之道在哪里。”
在绪论第二小节中,梁漱溟继续诘问陈、李、胡三位怎能说不出所以然来便讲两种文化将来会融通。
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里说,如果孔子之道适于“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那么所有变法维新、流血革命以及办新式教育等都是多此一举了。孔教与这些目标是“不可相容”的,因此“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
对印度,***说,印度厌世的人生观不合于宇宙进化精神。一笔勾销了。
一般人(包括新派)有一种模糊的印象,东方文化别的不行唯哲学和精神领域有些长处。梁漱溟反问:不是花费六十年工夫终于找到问题在文化么?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说:“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梁漱溟认为:胡先生的话“实在太客套了”。认为胡这样说“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诊断”。
梁培恕对这本书绪论的感受是:与其说讲研究不如说讲了自己的个性。父亲说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有要求”,因为自己个性对生活和行事“非常不肯随便”,凡没有确认为是对的,就不去做,如果去做,那就一定认为是对的。以前认为佛家生活对,立刻要过佛家生活,“而今所见不同,生活亦改”,父亲的思想和生活是一整体。
父亲拿一个个问题逼问朋友、同事,是不满他们的不认真,自己的见解还没有达到自信不摇,讲出来足以服人的地步便轻易宣布于社会(他说这个问题社会自然是看“知识阶级”怎么说。那时习用“知识阶级”)。新派虽指出一个改革的方向,用来“应付这险恶形势的仍旧是空空洞洞的一句泛常的话”。
往前追溯,梁漱溟在1918年发起东方学会的时候,已经把西方文化作过一番观察,有了一个看法。他曾请教顺天中学的同学张申府;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有两个特色,西方文化的长处都包括于此。那就是“科学的方法”和“人的个性伸展”。前一个是西方学术特具的精神,后一个是一个西方社会特具的精神。
张申府无置可否,而梁漱溟仍很自信并且觉得这是自己独有的见解了。梁给答案立了很高的标准。凡是要说一串话、举一些现象来说明什么是西方化都不算答案。标准是“把许多说不尽的东西归缩(现在叫归纳)到一两句话,可以表达出来,使那许多东西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跃然于我们的心目中”。他给张申府听的,已经归纳到“科学的方法”和“人的个性伸展”两点了,只算初步。因为他还要求用一句话便看到“活的东西”,而且把研究对象的特质来一个“兜根翻出”,才算是到家的答案。
清末曾国藩把西方化归纳为“坚甲利兵”;近代王壬秋《中国学报》的序里说:西方化嘛,“工商之为耳”。
杜威则把东西两种文化的不同归纳为西方人是征服自然的,东方人是与自然融洽的。这似乎过于简单。自由、平等--民主是西方社会的特异彩色--也能包括在征服自然里面吗?如果单看见它们物质上的灿烂而看不见社会生活方面的,这和只看见“坚甲利兵”有什么高下之分呢?
***借给梁漱溟一本《东洋文明论》(美George WilliamKnox作),说欧美之进步是由于科学和自由。后来陈独秀写文章说,能为中国治愈贫弱落后病的唯有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这比“征服自然精彩得多”,但是“仍有两个很重要的不称心的地方”。
第一个不称心:虽举出“赛先生”,但表出的是学术上的科学态度,未曾表出征服自然的精神。
第二个不称心:举赛先生和德先生两种精神代表西方文化是对的,这两种精神“有彼此相属的关系没有呢?”“把它们算作一种精神行不行呢”?好像没有相属的关系,非举出两种不可,则又像是“没有考究到家的样子”。
梁漱溟认为:现在大家都已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长处是科学和民主,可是为什么两年间总在这两点说了又说、讲了又讲,“却总不进一步去发问”?这两样东西“是怎么被它得到的呢”?“我们何以竟不是这个样子?这种东西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出来?”
梁漱溟看文化是活的,必有其趋往,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路向--朝着某个方向发展。西方、中国和印度这世界三大文化因所持态度不同而使它们的文化呈现各异的色彩。所以不要以为它们是走在同一条路上而只有快慢的差别。
基于上述看法,梁漱溟说:“大家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认为人类文化应该差不多”,“总是可以拿着比的”,“其实大误”,而是“三方各走一路,殆不相涉”。就这样,梁漱溟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观。后来,他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给学生讲话时说:“什么是哲学的道理?就是偏见!有所见便想把这所见贯通于一切,而使其成为普遍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