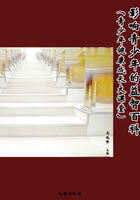1911年秋,梁漱溟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梁漱溟受革命形势的鼓舞,虽有机会去读书,但他不愿升学了。于是与甄元熙等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并任该支部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及外勤记者。
《民国报》报社初设在天津,后移至北京。社长是甄元熙,主要编辑为孙俊明(炳文),梁漱溟常为报社写点短评之类。京津同盟会还有一家报社叫《民意报》,主持人是赵铁桥。梁漱溟任外勤记者时,长驻北京,因为采访新闻,故常出人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
梁漱溟后来回忆:
我赶巧看着要袁世凯南下就职这一幕。当时南方派六位特使欢迎他南下。这六位特使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王正廷等。袁世凯表面上拿话敷衍着这几位特使,暗中却耍手腕,来个北京兵变,包围使者住处。旧历正月十二(2月29日)晚上,我陪母亲在广和楼看戏,忽然有人宣布外面兵变,不能让大家回家,当时士兵是朝天开枪,抢铺子。
六位特使回南京。只好定都北京。当时有临时参议会,在南京成立的,议员各省独立的都有,各省都督派的代表,一省三个人。要宣誓就职。议长是林森。我在楼上看得见。袁世凯手捧宣誓词,说话河南口音。读完宣誓词,就算宣誓了。林森领下来,经过穿堂门,到广场照相……
袁世凯刚刚从我右边过来,跟我差不多高,腿短,上身很宽大,穿一套旧军装,没刮脸,也不算留胡子。我心想,这人是坏东西!不管临时、正式,终究是大典,不刮脸,穿旧衣服,不尊重,我心想是坏东西。他根本看不上这个典礼,眼里没有这些事。
记者工作之余,梁漱溟还根据张继译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印了几十份送友人。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是日本人幸德秋水所著,梁漱溟认为:“此书当时已嫌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地来思索这个问题。……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我当时对于社会主义所知甚少,却十分热心,其所以热心,便是认定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对它。理由如上所说亦无深奥,却全是经自己思考而得。”梁漱溟后来又说:“那时思想,仅属人生问题一面之一种理想,还没有扣合到中国问题上。换言之,那时只有见于人类生活需要社会主义,还没有见出社会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有其特殊需要。”
1913年春,中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成立,《民国报》改为国民党本部机关报,由汤漪负责,随着编辑人员的更换,梁漱溟也与一些朋友离开了报社。
一年多的社会工作经历,让梁漱溟感慨颇深,认为:新闻记者似乎是社会上一项职业了,但其任务在指导社会,实亦非一个初入社会之青年学生所可胜任。“在做新闻记者时期,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此外,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国务院等处,我亦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许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却熟悉他。这些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之认识者不少”;“做新闻记者生活的一年余,连参与革命工作算起来,亦不满两周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梁漱溟后来在《谈我的思想问题》一文中说:“在我参加1911年革命的同时即有出世思想萌芽。”他在《择业》一文里也说:“就我来说,从前个性要求或个人意志甚强,最易看出的中学毕业后又不肯升学;革命之后又想出家。”
他的父亲也不主张他去搞革命,并明确地告诉他:“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仅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应该说,父亲的话对于对革命本来就有疑问的梁漱溟产生了影响,他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
在革命激情逐渐消沉的时期,社会上的贫富差异、恃强凌弱现象,也让梁漱溟心中愤愤不平。在其《卅后文录》的“槐坛”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北京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是一个白发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摔出血来,而我的眼里也掉下泪来了!又一次我在北京东四牌楼马路上往南走,看见对面两个警察用绳缚着一个瘦弱无力面目黝黑的中年男子,两边夹着他走。--看他那样子大约是一个无能的小偷。我瞪着两眼,几乎要发疯。这明明是社会逼成他这个样子,他不敢做别的大犯法的事,只偷偷摸摸救救肚饥,而你们如狼似虎地逮捕他,威吓他,治他的罪。这社会好残忍呀!
而在其个人生活方面,梁漱溟十七八岁时就曾有过出家的想法。当时梁的妹妹有一同学叫陈英年,人品极好,妹妹多次与梁母说,要哥哥与陈订婚,母亲愿意。其时梁母已病重,自知时日不多,乃拉住梁漱溟的手说:“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很好,可以订婚。”梁说:“我一辈子不结婚,很早有出家的思想。”梁母说:“你胡说!”梁父在一旁劝道:“这孩子他倒是有向上的意志,也许是怪癖,你不要勉强。”
1913年春,梁漱溟在护送他二妹谨铭到西安任教途中,他开始戒荤吃素,想出家当和尚,后念及家父尚在,不忍心绝然而去,但从此终生吃素,不食任何鱼、虾、猪肉之类,而每餐食量甚少,修身养性,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其座右铭。
由于对当时残忍、黑暗的社会现象日趋不满,梁漱溟于1911年冬及1912年冬,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
第一次想自杀,是准备去广西赴考留学。当时有两位旅京的广西老乡要去广西任法官,“我父亲托他们照料我回广西考试送出洋留学。由京浦路南下,到浦口,过天津时,这两位要做法官的先生,晚上出去逛窑子,我就很腻味。在天津如此,到下关住在大饭店,有许多娼妓出出入入,我很腻味,心里情绪很不好,同行者给我的印象不好,产生自杀念头。这是头一次,留了个字,自己走了。走到哪里?我有同学杨权,号通辅,我到无锡找他,想嘱咐他照料身后事,写信往北京家里。这位杨同学发现我不是常态,他就很关心我,陪送我离开无锡回北京”。
第二次想自杀,即是梁漱溟护送二妹回北京的路上。
其实,在去西安的路上,沿途风景很好,梁漱溟的心情也不错。当时铁路未修到潼关,修到一个叫观音堂的小站,从观音堂只能雇骡车,走潼关,再奔西安。有一天夜宿某一县客店时,梁要的上房,出店散步时,碰见一位法国神父,已来中国多年,中国话说得很流畅。他问梁:“你是头一次来吧?”“是。”“我看你就是头一次来。你所要住的上房不好,我就不住。我住窑洞,窑洞好,冬暖夏凉,我看你是初来的。”梁才明白,法国神父是老经验家。客店主人问梁:“吃什么?”“我喜欢吃面条。”“有。”面条端上来很粗,又没有酱油和醋,只有盐水拌面。“盐水拌面,是否给点油?”他说可用点灯的油,梁说不用的好。梁体验到这里人民生活的贫苦和法国神父的经验与适应能力。
梁漱溟的二妹教课很好,但学生岁数大,不大尊重她,教了三个月,二妹执意要回北京,又由梁漱溟护送。火车到郑州,梁氏兄妹在旅馆休息转车,“又看见乡下女孩子,穿着红的绿的衣服,脸上抹粉、打扮。撞进来到我住的房间,我推她出去,她看我陪我妹妹在坐着就出去了。这件事引起我对这现象的怨恶,不单是怨恶女孩子,而且是怨恨人生。对女孩子倒是同情、可怜,这些都曾让我产生自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