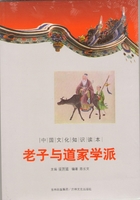何谓重刑?“所谓重刑者,奸之所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重刑就是让违法的人为违法行为得来的利益大大小于为此行为所受到惩罚所带来的损失的一种刑罚方法。从韩非给重刑所下的定义来看,他是从功效的角度来看待重刑的。很明显,“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他提出此说的理论依据。
缘于人性恶的思想根源,韩非对儒家以德教治国的主张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也”。他主张只有施行重刑酷法才能使人畏惧,不敢以身试法,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他认为轻刑等于无刑,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息暴;只有“以刑去刑”,才能达到政治的稳定。韩非继承了先秦法家的重刑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重刑主张:
(1)信赏必罚
“信赏必罚”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东西必须付诸实施,要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施行奖赏应该优厚而且要说到做到,使人们认为有所贪图;施用惩罚应该严厉而且要坚决执行,使人们畏惧。“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赏罚的作用不仅体现为受到赏罚的对象,更是为了扩大影响、以儆效尤、树立法律权威。
(2)厚赏重罚
在韩非看来,“厚赏重罚”中,厚赏是为了鼓励臣民继续立功,重罚是为了威吓臣民不敢犯法,即“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提倡重刑,正如韩非所言“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也”。实施重刑,就是要让那些违法的人为其行为负责,使其得来的利益相比遭受的惩罚小得多,而为此所受到非常重的刑罚。韩非强调“重刑”就是要重到能有效地预防犯罪的程度。“重罚”是为了造成一种恐怖气氛,用以威慑臣民,使之不敢再触犯法律。韩非认为,重刑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为了“去奸”、“去刑”。
(3)轻罪重罚
韩非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轻罪重罚”就是要形成刑与罪之间的巨大反差,告诫臣民不以小利而蒙大罪。杀一儆百是为了扩大刑罚的威慑影响,运用严刑苛法制止犯罪。只有“刑九赏一”才能“以刑去刑”。韩非说:“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禁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重刑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建立不使用刑罚的理想的“法治”国家。由上文可以看出,韩非的重刑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上文我们谈到韩非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的观点,其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人生来“好利恶害”的。由于人的本性是恶,那么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就必然会发生争斗。韩非认为要防止和解决争斗仅仅使用道德是不够的,要使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
韩非反对无条件地满足人民的欲望,主张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使人民的欲望得到满足,如果是法律不允许的行为,那么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要在全国的范围内推行法律,使人们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争斗的发生。如果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违反了法律,韩非主张用重刑来惩治人们的违法行为。因为他认为“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施用重刑就能使民众因害怕违法犯罪带来的严重后果,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尽量不去犯罪。
同时韩非认为对犯罪人适用重刑,还可以达到以儆效尤、预防犯罪的作用。因为人天性是恶的,是“好利恶害”的,为了自己的私利犯罪的可能性很大。一般来说,犯罪代价越小,获利越大,犯罪的意念就会强烈,如果对犯罪人使用重刑,那么他犯罪所得到的惩罚就会大于他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得的利益,那么他的犯罪意志就会被抑制,这就达到了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的目的。同时使一般的民众看到犯罪人所受的刑罚的痛苦,那么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会“三思而后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不实施犯罪行为,从而达到预防一般民众犯罪的目的。因此重刑不但可以惩罚犯罪,还可以预防犯罪。
韩非是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积极倡导的专制主义理论,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思想中的进步性和反人民性并存于他的具有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他只看见争取国君、打击旧贵族以满足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而没有照顾到其他阶级,如工商业者,特别是广大农民阶级的要求。
3.法、术、势的政治思想
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以法为本”的法、术、势三者的结合。它的出发点是历史进化观和社会矛盾观。根据他的说法,人口既然愈来愈多,而财富却相对地愈来愈少,争夺也就愈来愈激烈,所以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就必须用“倍赏累罚”的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他在《五蠹》篇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因此,韩非主张用暴力去镇压一切反抗者,建立君主专制的政权。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荀子。荀子隆礼重法。韩非丢掉了隆礼,而大大地发展了重法。二是源于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商鞅在秦变法,大有成就,本编已别有传。申不害,“故郑之贱臣”,相韩昭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不害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称其“学本于黄老而著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子》早佚,有《大体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慎到,赵人,与齐人田骈、接子、淳于髡、楚人环渊等,都是齐的稷下先生。慎到著书,《史记》称其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慎子》四十二篇”。慎到书,也久佚,清人存辑本。韩非把商鞅论法、申不害论术、慎到论势,加以分析扬弃,发展成为法家的新的思想体系,使他成为法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
韩非所谓的“法”,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法和术的显著区别,一个是向国人公布,一个是藏在君主的“胸中”,“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韩非子·显学》)。《定法》篇是韩非对申不害、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总结,并指出法、术结合的必要性。
韩非有见于申不害只讲术不重法的弊病,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所以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治国十七年,仍然不能使韩国实现“霸王”之业。韩非又见于商鞅只讲法不用术的弊病,指出鞅之治秦,虽有法以致富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它的结果是“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所以,凭借秦国的强大力量,长达几十年都不能实现“帝王”的事业,这是由于官吏虽然勤谨守法,而君主却不用“术”所造成的。为此,他用答客问的形式,说明法和术的不可偏废。他把法和术,比喻为衣和食,说明治理国家法和术缺一不可。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认为,申不害讲的“术”,商鞅用的“法”,也还不完善。“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他引申子的话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他接着批评说,官吏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说是“守职”,那是对的,但知道自己职权以外的事不说,那就错了。因为君主了解全国的情况,要依靠官吏。如果官吏知道了自己职权以外的事不说,君主还依靠谁做耳目呢?他又引商鞅之法说:“‘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他批评说,如果定这样的法令,叫斩敌首立战功的人做医生、工匠,那么,病就治不好,房子就盖不成。因为医生会调配药剂,工匠有专门的手艺,让有战功者做这些事与他的能力是不相当的。“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韩非拥护并发展了慎到的势治。在《难势》篇中,韩非认为“势”有“自然之势”和“人之所设”的“人为之势”两种。“自然之势”,是指世袭的君位,所谓“生而在上位”。他引慎到的话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看来,慎到讲的似偏重于“自然之势”,韩非所讲的是“人为之势”。“人为之势”是势和法的结合,就是所谓“抱法处势”,是指君主的法治权力。韩非认为像尧、舜、桀、纣那样的君主,“千世而一出”。因此,他所要着重讲的是“中者”的得“势”。所谓“中者”,指的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君主。他认为这样的中主“是比肩随踵而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对于中主来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又说:“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难三》这种势、法并举,势、法结合的“人为之势”,就是韩非对慎到“自然之势”的发展。
韩非在经过对前期法家学说的分析总结以后,把法、术、势这三个法治要素,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故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的法治思想,概括地说,是君主凭势,使术,用法来统治臣民。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就是生杀予夺的权力。君主有了这种权力,才能使术用法,使臣民服从自己,为自己所用。韩非认为君主必须把这种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同任何人分享,否则权力就会遭受削弱,甚至丢权丧身。
他认为,国和家一样,只能容许独尊,不能容许两尊或近似两尊的局面。否则,国家就要发生纷争。他说:“孽有拟适(嫡)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故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枝子配适,大臣拟主,乱之道也。”韩非认为君主要依靠官吏统治人民,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但君臣间又有利害矛盾,所谓“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在《韩非子》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法,在韩非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主要位置。在韩非看来,法是全国臣民行动的准则。有了法,行动才能有统一的步调。他说:“一民之轨,莫如法。”他认为如果依法行事,就能消除人间的不合理现象,社会秩序才会稳定。“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他还认为,如果按法行事,就是受到惩罚的人,也会心安理得。“以罪受诛,人不怨上。”否则,“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实行法治主要靠赏罚。在韩非看来,绝大多数人不会自动为善,必须利用人们趋利避害、喜欢受赏而害怕受罚的本性,君主只要运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臣民。他把赏和罚看做重要的统治工具,称之为“二柄”。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赐)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赏罚的权柄要牢牢地掌握在君主手中。如果君和臣共掌赏罚大权,禁令就行不通,所谓“赏罚共则禁令不行”,还会出现像宋国司城子罕劫宋君,齐国的田恒杀齐简公那样的事。
法治的对象是广大的臣民,与术只用于臣下者不同。依照韩非的看法,除了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所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韩非为了说明法治的历史根据,从先王中找出一些事例。《说疑》:“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圮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他主张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不论亲疏贵贱,只要按法行事,立下功劳,就可担任官职。“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一主张,有利于打破世袭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便于新兴封建地主分子参加各级政权,对发展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是有积极作用的。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统治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不需要什么诸子争鸣,只需要人民成为“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的顺民。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思想,是战国末年各国间走向统一,各国内部趋向君权集中的反映。世界观与认识论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的思想,并改造了老子书的若干观点。他的《解老》、《喻老》两篇,是对老子书最早的注解,反映了韩非世界观富有唯物主义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