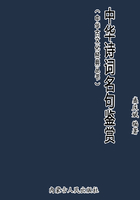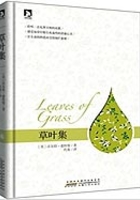侧耳凝听,时隔多年仿佛依然传来那蹒跚而又坚定的足音——这是回家的脚步。然而世事沧桑,家园又在何处?只有“回归”本身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最后的希冀。他们个人的囹圄受难,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时代的禁锢与受难。面对着这样一群柔弱的生命,令人困惑的是,这究竟是时代的玩笑还是命运的困顿?专制制度在用粗暴的姿态鞭挞着历史的精英;这究竟是荒诞的故事还是曲折的传奇?放逐与驯服的改造令人产生桎梏的幻觉,同时也锤锻着愈加坚韧的灵魂……历史的吊诡让一切变得难以言说。然而,他们毕竟光彩夺目地划过昨夜的星空,让人瞩目和永远铭记的不仅是卓著的贡献,还有苦难的历程。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增强了中国文学的底气也丰富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
这就是回归者以及他们的文字——苦难的岁月、坎坷的经历,甚至是凄风冷雨,都不能磨蚀和改变一个人内心的纯洁。无论是胡风的“侠骨柔情”,还是聂绀弩的“赤子之心”;无论是曾卓“温情”地抒写,还是绿原“冷峻”地思辨。他们所有的热情和感动,他们胸中翻腾的黄河和长江,都源于一颗质朴而又崇高的心灵,面对这一群时代精神的执火者、世纪的歌手、提醒者、目击者和某种证词提供者,我们将因为曾与他们同行而骄傲。
一独立的人格建构——胡风散文论
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彰显他的主体意识。文学批评家刘再复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作家最重要的,应当有自己的心,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人格。”胡风的一生是可以说是抗争的一生,他既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与国民党政权不懈斗争,在左翼作家内部和新生政权里也难以同构与和谐。自认为是得到鲁迅真传的弟子,在新国家建立之后却不被认可,投奔即被边缘化,排挤于新文学的领导层之外,“三十万言书”成为他镣铐加身的符咒,继而是近三十年的牢狱之灾。可是,在胡风的身上不仅有着湖北人的火爆脾气和固执个性,而且还显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想意愿与顽强的人格精神。
傅光明曾在《胡风散文》的《前言》中这样写到:“胡风是人如其文,也文如其人的。读本集中的理论和杂感类文字,会感到他惯常的面孔:刚硬,有棱角,摸上去真扎手;深邃,有内涵,读进去有韧劲。而读他的纯散文作品,我竟读出往常不知的一面:侠骨,有血性,一副义气肝胆;柔肠,有情愁,颇具丹心豪情。”⑧应该说,“侠骨”与“柔情”,构成了胡风人格精神的重要两面,他用他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刚硬又不乏柔情的文艺理论家形象。正是通过阅读他为数不多的散文,我们时刻能感受到这些文字中涌动着一股“独立人格”的精神气脉。
一、人格的“刚硬面”
胡风既是“五四”时代启蒙精神的继承者,又是“后五四”时代启蒙现实主义的坚守者。当我们解读胡风的人生,发现他作为一位来自民间、有着极强独立精神和现代大众意识的精英式知识分子,既继承了鲁迅式的批判性传统,同时也接受了鲁迅式独战方式,他的“不识时务”和耿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能见容于国民党政权,在五十年代又不能见容于主流话语,似乎也就成了某种必然,最终导致了他和“七月”派作家群在时代转换中被冷落以至在“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艾青《向太阳》)的悲剧命运。
如果我们将时代环境下的失败看作胡风“独立人格”精神的失败,是不应该的,也不明智的。历史终究会证明这一点,胡风坚硬的性格与原则的坚守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在时代的炉火中锻造了一位独特的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
在胡风的创作活动中,“启蒙精神”与“现实主义”构成了胡风“硬性”散文的两大主题。
首先从“启蒙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后五四”时代的执旗手,胡风传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他主张文艺应该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具有改造国民性的功能,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有学者这样评价胡风,说他是一位以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精神搏击历史和黑暗现实,感受人生和心灵苦难的艺术家。在他的散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表现:一方面,他注重对鲜活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在《半仑村断想·想到几个小故事》中他思考了几个“所谓小儿女的故事”,虽然在别人看来是“上不得台盘的”,但在他看来,与其听有些人嘴里说着“节义”“廉耻”,滔滔不绝地登台演说几小时,“倒不如这类小故事反而能够使我感到活人底意义,活人底平凡的意义和非平凡的意义,就说这伟大的解放战争罢,能够支持下来而且一定要胜利,难道不是依靠着我们民族底意志和人民底气节么?”在文章结尾,他总结道:“肯定人民底生活实状,肯定人民底对于生活的忠贞,综合这些,用科学的精神寻出现实历史底特征和发展方向,向伟大的理想引着走去,这才叫做民主。”另一方面,他的启蒙观表现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胡风认为文艺的作用不在于向民众灌输某种具体而现成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强化民族精神,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激发其生命的“原始强力”。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他更偏重于把群众看作改造和教育的对象。在纪念五四的文章里我们看见了胡风对五四革命传统的眷念。也看到了他发现的“市民阶级底另一个灵魂,怯懦的妥协的根性”在文学上的反映:“于是,认识现实的精神变种成市侩式的商场机智和淑女绅士底日常腻语,自我扩展的精神变种成封建才人底风骚和洋场恶少底撞骗,而五四当时一般所有的向‘人生问题’底深处突进的探究精神,却变成了或者是回到封建故园的母性礼赞,或者是把眼睛从地下拉到天上的流云似的遐想了。”(《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纪念写》)这里以讽刺的手法,揭露出这种劣根性在文学上的表现。
其次,从现实主义创作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接受过五四文学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胡风直接传承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胡风把作家对客观存在和自我的认识统一起来,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和自己的双重责任。这是承接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文艺观和人生观。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他扛起了“五四文学”的旗帜,站在左翼文学阵营中,对国民党当局统治政策和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广泛锐利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以林语堂和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小品文流派的所谓“闲适”、“超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和评论相结合,指引着左翼文学行进的方向。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坚持着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原则,不愿去迎合主流文坛文学只能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艰难地在“忠实于自己”和“认识客观现实”之间行进。即使在“归来”后,在胡风的许多回忆文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对冤案相关人物和自己文艺思想的阐述,在与文坛隔断多年后,他依旧坚持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原则。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我们又听到了他倔强的声音:“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容的精神力量而写。”
正是对“启蒙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坚守凸显了胡风人格精神的“刚硬面”,有评论者称胡风是一位硬气文人,他的这种“刚硬面”既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同时也完成了其个人的人格塑形。李辉曾在《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随感》中也谈到:“也许他有太多令人非议的性格特点,譬如说偏激,譬如说不宽容,但他做人的根本原则是正直、真诚。他从来不愿掩饰自己,他把虚伪视为人格的天敌。他的性格使他招致厄运,但他的性格也使他做一个真正的人。⑨”
二、人格的“柔情面”
如同一个硬币拥有两面一样,胡风除了在散文中表现他的硬骨头精神,细细品读他的散文,我们也会发现他内心深处的那一丝侠骨柔情翻看胡风的散文集,有些发黄的纸叶间布满了战斗的记录和奋不顾身的影子,但一个完整的人远远不止这些,在与现实和灵魂的搏斗和撕扭之外,那些面对友人、妻儿与人民的文字,一股温情流溢其间。
胡风曾经强调,艺术(文学)作品的内容一定是历史(社会)的东西。离开了人生就没有艺术(文学),离开了历史(社会)就没有人生。而人生不是空洞、抽象和单面字眼,它蕴含着人类的丰富与多样的情感。所以他说:“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的确,有爱亦有憎,它们共同支撑起完整的人生,而作家是上帝派下来的使者,是扑扑跳动的良心,来揭示所有的隐秘。
胡风散文中“柔情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乱时期的感慨之作。他在战乱中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的途中写下的《人环二记》(《出西土记》和《浮南海记》),《出西土记》写于民族战争结束后“复员”之前,《浮南海记》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将要崩溃,从上海出走后记下来的。在中国现代历史中,这两段历史是至关重要的,胡风一改往日犀利,锋利的笔法,在文章中流露出对友人,对妻儿的关心与留念,也写出了自己在出走的途中的无可奈何,从侧面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的时政的不满,看似平淡朴实的文字,却蕴含了默默温情。
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友人,对于人民的关爱。他用无比的真诚来拥抱人民,比如对老舍“真”的赞赏与评价(《我与老舍》);对丘东平牺牲的悲痛的悼念(《忆东平》);对日本共产党的思想斗士宫本百合子坚毅顽强的肯定(《越过大海和火网的悼念》);对被俘的中国朝鲜志愿兵与敌斗争的高度赞扬,感动于他们的宁死不屈,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忠心(《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对解放以后工人以及劳动模范的赞赏,深深的折服于他们克服艰险的英勇经历和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坚贞情操(《伟大的热情创造伟大的人》)等等。
最后,他的这种情感还表现在对于他的“精神导师”鲁迅的崇敬之情上。胡风在他的散文中一方面展示了鲁迅式的嬉笑怒骂,展示了鲁迅所代表的独特的战斗精神,这是与他刚硬的性格以及坚守现实主义的原则相印证的,但同时当他面对与鲁迅的交往,面对先生的辞世,他的笔端流露的是默默的温情与高度的对先生的崇敬之情。他用自己的笔来悼念先生,如《悲痛的告别》中他告诫朋友们“凭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悲痛、我们的仇恨所融合起来的伟力”继承先生的志愿;《即令尸骨被炸成了灰烬》中回忆起突接先生辞世消息的震惊,默默发誓用先生永不泯灭的精神鼓励自己继续前行。
胡风的这类抒发内心感受的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展示在文艺评论中的硬汉形象不同的胡风,但是这类展现侠骨柔情的文字正是他内心深处情感的外露,同时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了胡风的独特的人格魅力。“恨之深,爱之切”,因为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深切痛恨,所以他关注弱者,关注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一群善良的人们,他不仅启发他们,更用自己拥抱真理与信仰的真诚来拥抱人民,无论是自己的友人,妻儿还是普通的人民大众,他都心怀真诚,用自己最柔软的文字来表达对他们最坚硬的爱。
无论是刚硬还是温柔,无论是横眉怒目还是侠骨柔情,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胡风的独立的人格魅力,他可以在他的文字中尽情地嬉笑怒骂,展现喜怒哀乐,因为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的文字是独立的,他的人格是独立的!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实际上代表了作家在创作所孜孜以求的境界。这对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文坛无疑是有着深刻的意味的——在他胡风散文中所体现出的这些品格不容置疑地构成对新时期散文精神的大胆预言与深情呼唤。
“时间开始了!”仿佛听到作者发自心底的呼唤,摩娑着《胡风文集》发黄的封面,我们盼望着,一段真诚的时间真的开始了……二“雪风难掩赤子心”——聂绀弩散文论
论及中国当代散文中的湖北作家,读者不会对既叱咤文坛又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蕲春作家胡风感到陌生;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与胡风同一个时期,湖北的京山小镇孕育的另一位同样饱经沧桑、身陷囹圄的、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他就是聂绀弩。
1903年的除夕,湖北京山县城关十字街聂宅迎来了一个新生的男孩,家人祝福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为刚刚出生的男儿取名叫国棪——他就是后来活跃在现代文坛上的作家聂绀弩。也许是上天对他的垂青,也许是命运给予的考验,这个出生在交子除夕的男人注定要经受严冬中大雪风暴的冲刷和春寒料峭的洗礼,注定要在黎明前的暗夜中争取最终的光明:他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风雨飘摇,见证了中华民国短暂的由民主革命走向伪民主反人民的穷途末路,他曾经热情憧憬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美好未来,也亲身体验了“胡风运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摧残。出生在书香世家的聂绀弩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国学教育,18岁他进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读书,不久就开始接触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讨论集》、郭沫若的《女神》等这类进步书籍,19岁加入国民党。1924年,他成为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第二期学员,次年获得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苏联求学期间,他不仅自修了中国文科大学的主要课程,接触了各种中国当时前沿哲学、政治学著作,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的熏陶。聂绀弩的求学经历使他增长学识和文化底蕴,更为他建立独立坦荡正义的人格,树立民主主义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起到了催化的作用。聂绀弩的散文记录了中国民族战争、民主革命的动荡与转变,反映了中国从封建社会被强行拉入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与挣扎,映射了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肩住黑暗闸门的人文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