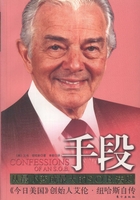【文洁若】
文洁若,女,1927年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著名文学翻译家,日本文学研究家。有《我与萧乾》、《芥川龙之介小说选》等著译多种。
冯雪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他在冷落与冤屈中溘然长逝后,我不断地读到怀念并描述他的文章,从而使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位德高望重的首任社长更加深了理解和尊敬。五十年代我在他手下工作过,“文革”期间又在“牛棚”中共过三年患难。那以后还在咸宁干校一道劳动了两年。其间,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向阳湖我还同这位半生坎坷、备受折磨的老人同台讲用过一次。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成立的,由三联书店抽调一批干部,在文化部旧楼借几间屋子办公。冯雪峰只身从上海来京,住在该楼的一间小屋里,筹划创社事宜。入秋后,简陋的三排筒子楼才竣工,我们遂搬进去办公。
1954年后,这位耿直不阿的社长就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一再挨整。他写的寓言被斥为毒草了,他被扯进了“丁陈集团”,最终,一顶千斤重的右派帽子压到这位参加过长征、并被关进过上饶集中营的老干部头上。
一连串惩罚纷至沓来。他本人连降好几级还不算,子女自然也受株连,或被赶到外地,或被调到基层,迫于形势,老两口主动提出由原来的小独院搬进大杂院中勉强能容身的两小间。好在这位长征干部两袖清风,身无长物。若干年后,总务科一名科员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交代,当他为遭到贬黜的冯雪峰清理苏州胡同那个小独院时,曾把一块地毯偷偷卖掉,饱了私囊。那原也是冯雪峰自购的,他的住房缩小,就留给出版社了。降级后,生活当然颇受影响。
冯雪峰一向律己甚严。解放初期,身为领导的同志往往乘机为妻子及亲属安排工作。那时缺额多,这种做法相当普遍。雪峰的爱人何爱玉比他年轻六岁,高中毕业。三十年代以来就协助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完全有资格调入社里。只要雪峰稍有表示,人事科肯定就会为她安排个岗位的。然而,雪峰非但没这么做,他还让爱人在编制外当一名不拿工资的秘书。
1953年萧乾曾告诉我,头年晚秋雪峰同志到外文局去看望他,对他说,胡乔木同志派他去征求萧乾对回归文艺队伍的意见。萧乾对雪峰心仪已久,那次见面,感到他为人谦逊和蔼,胸怀磊落。几个月后,萧乾就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筹划创办《译文》杂志事宜。
雪峰戴上右派帽子后,降为一名普通编辑,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译所。1961年6月,萧乾结束了三年多的“监督劳动”后,也从农场调到那个编译所来,从事翻译工作。冯雪峰是那一年第一批摘帽的,还见了报。次年春天,他被邀列席政协会议。出版社这才把他的住房调整到北新桥的宿舍里。这时,他提出请创作假,去完成他那部于1937年就着笔的、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但未获批准。于是他准备写一部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还为此亲自到广西和湖南实地考察过。然而,小说刚开了个头,就又奉命赴河南安阳参加“四清”。他用的是早年的名字福春。他工作出色,当地干部不晓得他是摘帽右派,还提出表扬他,但上面未予批准。
“文革”开始后,他也被送进了“牛棚”。有个时期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顾不上管我们。我每天完成了那点指定的劳动,就无所事事。在桌上摆本《毛主席诗词》,一首首地背诵,倒觉得比一部部地校改译稿省眼睛。那些年我们中间最忙的是冯雪峰,成天络绎不绝地有人向他外调,他总埋头写材料,片刻也不得清闲。
196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只留下少数人搞“样板戏”,工作人员“全锅端”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去围湖造田。早在1941年,冯雪峰被囚在上饶集中营的时候,就害上肺病,奄奄一息。幸而被营救出狱。1959年又患胃病,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老弱病残”四条,他都占全了。然而纯粹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67岁的冯雪峰也佝偻着腰,不由分说地被赶到干校。当时,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摊到那些在“牛棚”里受过审查者的身上,动辄就是:“派几个右派”。雪峰出身于农民家庭,干活卖力气。这位奔七旬的老人往往被当成壮劳力去使用。例如,有一次修桥,雪峰、萧乾和另一个右派被派去挑石头。雪峰挑得又多又快,萧乾比他还小七岁,却不如他。第三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地道的文弱书生。下工时,外连那位领班把雪峰留下,教另外两人自次日起,“不必再来了”。
由于雪峰劳动得格外出色,有一天军代表和连干部派他在四排讲用,还指定由我去奉陪。
我所在的十四连四排共有三个班,三四十人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自从1957年在文化部小礼堂听雪峰做“大鸣大放”的动员报告以来,已经多年没听见他当众讲话了。
雪峰用浓重的浙江义乌口音开腔了。他的嗓音再也不像五十年代做报告时那么洪亮、那么充满自信了。
其实,雪峰是最有资格讲用的了。咸宁干校的“五七”战士虽然达数千名,但像雪峰这样与毛泽东、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直接交往过,又曾爬雪山、过草地、蹲过集中营的,诚然是绝无仅有。倘若谈谈他这传奇般的生涯,该是多么生动。然而对这位饱经风霜的瘦弱老人来说,这一切都已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属于连提都不能提的禁区。
在干校所举行的多次讲用中,就数陈早春所做以放鸭为主题的讲用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把鸭子的生态描述得绘声绘色,从此大家亲切地称他作“鸭司令”。后来雪峰一度被选作早春的“接班人”,在沼泽地跟着早春放了几天鸭子。尽管雪峰像对待任何工作一样,依然豁出老命去干,但终因体力不支,打了退堂鼓。早春比雪峰年轻三十岁,而且身体健康。军代表和连干部真是过高地估计了风烛残年的雪峰老人的潜力。
总之,雪峰那次的讲用缺乏中心思想。他只谈了谈自己对党对人民犯下过严重错误,表示今后决心通过劳动来改造世界观,重新做人。雪峰讲毕,军代表绷着脸训斥他说,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
说实在的,不论雪峰怎么讲,也讨不了好,因为那顶帽子虽然摘了,他却还是“摘帽右派”,他的命运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轮到我了。我知道军代表和连干部为什么指定我来讲。一周前,同屋的一位资深女编辑约我为墙报写一篇稿子。我和她在“牛棚”里共过三年患难,在干校又编在同排同班。没想到我借着昏暗的油灯熬夜写的那篇稿子竟博得了连部的好评。“红八月”以来,我的头上突然也出现了光圈。连总抱怨我劳动不够卖力气的班排长,也开始表扬起我来了,甚至早晨出工前,我在“天天读”时漫不经心的一句发言,也受到一向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一位“响当当”的称赞。好几天我很不自在。因为我读过苏联的长篇小说《不需要的荣誉》(伏罗宁著),暗自担心被人为地捧得越高,有朝一日会跌得越重。不过,既然要我讲,也只得“赶着鸭子上架”。我没有怎么准备。当时我原想表一表全家四口人走“五七”道路的决心(1969年11月,为了“备战”,我们就把一对儿女都接到干校来了)。然而听着雪峰的讲用,我猛地领悟到,这位老人的头脑实际上是非常清醒的。他之所以讲得那么平淡呆板,是因他既不能说真话,又不肯说假话。那是1971年初,“五七”干校的始作俑者、靠谎言起家的副统帅还在台上。就拿我那篇获得军代表和连干部好评的墙报稿来说,我写的又何尝是真话?我才没那么心甘情愿地丢下自己的专长、让子女荒废学业,全家四口人一辈子走“五七”道路呢?我顿时泄了气,只把墙报那篇稿子大致重复了一遍,把场面敷衍过去。
那之后不久,在“拉练”中,雪峰受到了一次摧残。“拉练”本是部队练兵的做法。军代表把它搬到干校来了。不定哪天,半夜里突然吹号,要求这些大多数已年过半百的“五七”战士像棒小伙子那样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叠好被,紧急集合,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跑步行军。一天晚上,雪峰和萧乾都跌了跤,因而远远地落在队伍后面。年富力强时,雪峰曾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精力快耗尽了。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
1971年6月,雪峰随着一批老弱病残到了丹江口。虽然再也不用自己种稻种菜了,但拉着大车去运粮油肉菜的任务还是落在他身上。亏得转年秋季修订《鲁迅全集》的工作上了马,雪峰被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才避免像侯金镜那样在干校因劳累过度猝然身死的命运。
1973年7月至1978年,我们蛰居在东四北门楼胡同的八米“门洞”里。那儿离雪峰所住北新桥宿舍不远。一天,萧乾去看望老友孙用,承蒙他惠赠一包红艳艳的宁夏枸杞子。萧乾马上蹬自行车专程到北新桥给雪峰送去一半。第二天,雪峰又从北新桥步行到门楼胡同我们那个“门洞”回访,并且还送了一包黄豆。可惜那阵子我“以社为家”,住在办公室里,无缘同这位老领导再见一面。1975年3月,雪峰就因肺癌在协和医院动了手术。大夫说是由于他体质弱,又由于多年的劳累,再加上心情长期郁闷造成的。术后一个多月就被迫出院,及至发现扩散,再住进医院,就已经回天无术了。
1976年1月31日,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去世的消息传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个办公室,大家都十分哀伤。尽管“四人帮”下令不许念悼词,并规定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不得超过二百名,然而自发地前来参加的还是突破了三百人。追悼会由胡愈之主持,茅盾、叶圣陶、宦乡和不少民主人士都参加了。及至雪峰同志的问题正式平反后,又重新开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聊以告慰九泉之下的雪峰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