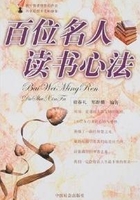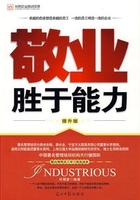一
我是后半夜逃出来的。
坐火车,转汽车,一天多的路程。
傍晚时分,到了。西边的太阳已在发困,带着烦乱与憔悴的情绪,憋红着脸,颤颤悠悠地往地平线上靠拢,想尽早躺下休息。村庄已有几缕袅袅飘升的炊烟,好像受了夕阳的感染,疲惫而又懒散地在空中漾着,调子很低沉。近了,才看清村庄的最大变化就是比十年前零散地成长出一些砖瓦结构的房屋来。它们在温热的黄昏中努力地透视着大别山老区的农村经济。
人们都还在田野里劳作,整个村子显得很是空落,没有什么生气。我家的院门虚掩着,推开门也没有什么反映。院中一棵上了年纪的枣树,枝条上正在有事没事地悠着小枣,样子很寂寞。星星点点的枣儿被晚风摇曳得很不高兴的样子,晃着满脸的小心。地上的一群蚂蚁正在围着一颗通红的落枣转来绕去,激烈地争论着怎样才能把它搬运到目的地。一只飞鸟经过枣树的上空,不走了,落了下来,站在一枝树杈上东张西望的,考察着这里是不是临时休息的理想场所。西墙的影子漫不经心地铺满了庭院,把整个院子弄得都很忧郁。墙头上的一声鸡鸣和屋角处传来的猪哼才透出一些生机,有了活气。我干咳了一声,屋内方有了响动,接着便走出了一位老人来,是我母亲。母亲比两年前从我那里回到农村又老了许多,背更驼了,生活的重负压弯了她的一生。一脸皱褶层层地叠印着日子的艰辛,这让我想起母亲她许多苍老的岁月,心里便发酸,想哭。
老母两眼花花,暗淡无光,已看不清人了,添了许多斑斑点点的迟钝。等我颤着声叫了声妈扑了上去后,老人家半天才意识到是儿子回来了,惊喜得泪水都流了出来,忙冲着里屋喊道:“小芳,你学良哥回来了!”
随着母亲的声音,房门里出现了一位婷婷玉立的姑娘来。看样子很忧愁。我一时想不起她是谁了。长得很文静,山青水秀的。大大的眼豆水汪汪地衬着红润润的苹果脸,一颗黑溜溜的美人痣光明磊落地袒露在下巴上,不偏不斜地点缀着清秀的五官,一条又粗又长乌油油的大辫子垂到腰下,强调着她美丽的程度。她冲着我叫了声哥,脸就红了,缅腼腆腆的,很害羞的样子,更增加了农村女子特有的那种质朴素雅的清纯。听母亲说后,我才知道她是三姑家那个长流鼻涕的大丫头。真是女大十八变,无论如何去想我也无法把一个爱流鼻涕的丑小丫与眼前的大天鹅联系在一起。
晚上自然是“团圆饭”。弟弟和弟媳又喜又怨地说我事先也不来个信,家里好有个准备。我有苦难言,没法把真情告诉他们。回来是我突然决定的。昨晚我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舌战群雄、疲惫不堪地把单位一些要分流出去的人员在夜晚十二点多打发出家门后累得我躺在沙发上气都懒得出了,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正赶上部门机构改革,我被卷进了层层叠叠的关系网里,剪不断理不乱。不是张处长来找我讨职务就是李处长来向我要位子。软磨硬缠,连求带闹,那表情,那声调,让你见了如不同情就简直不是人,让你听了如不答应就是一种罪过。良心话,我理解他们,也同情他们,年龄到了,职务没有升上去,要分流了,还不知今后如何。分流前他们总要提个条件,好求得一下心理平衡,比如职务啦,位子啦,工资啦,待遇啦等等,让你无法办到而又难以拒绝。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没场合没时间地缠着你,除非你蹲在厕所里别出来,不然逮住你就不放过,好说歹说,声泪俱下,甚至恐吓,轮番轰炸。使你头晕脑胀、耳膜起茧、口舌生疮。白天还好说,特别是夜晚,他们一拨一拨地来,塞得客庭涨满。孩子学习受到影响,爱人休息受到干扰。可你还不能粗暴地回绝他,让他们滚蛋!人心都是肉长的,毕竟是同壕战友工作了这么多年,交情还是有的,人吗,总是要讲点人文关怀的。如此这般,真是让我欲哭无泪、欲笑无声,整天泡在他们悲悲哀哀、凄凄怨怨的求诉声里,扰乱得做事、吃饭、睡觉都没了心思,一刻都不得饶人。现在我确确实实感到当领导不易,整天撕撕拽拽,纠纠缠缠,上下左右都得考虑,都得周旋。我实在受不了了,真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爱人过来给我盖毛毯时,我才惊醒。她见我醒来后就坐下来用手抚着我的额说“唉,看把你累的,你总是在挥霍身体赌明天,身体再这样透支下去你定会垮的。看你两眼都陷下去了,眼圈也黑了,是不是真的有了病?我建议你还是先看看医生去,工作要紧,身体更要紧。”
爱人的话使我心里不觉一动,是的,我为什么老泡在家里和单位呢,搅得工作干不成,人情又难做,为何不到什么地方躲上一躲呢,不然,我真的要被这些人给拖垮的。
到什么地方又成了问题,出去开会、学习,近期没有安排,躲进医院,他们会找进去的。想来想去,有了:回老家。老家虽然离这里只有一千多里的路程,因工作繁忙,有十多年没回去了,母亲和教书的弟弟也常怪罪,说官当大了,家也忘了。这一次回去其不是两全其美。爱人也很赞同。主意拿定,就给上司挂了电话。上司开始还真的认为我有病了,连夜要派人来看我。最后听了我的口气才意识到了什么,就同意了。于是我连夜偷着溜号,连车子都没敢招惹,随便打上点行装,做贼似的叫了个出租,逃到火车站。我把这些真情给埋伏了,没敢告诉他们,借故说出差路过这里,想他们了便拐回来看看。
晚饭后,乡亲们知道我回来了都来看我。屋里屋外的全是了人。问寒问暖,忆旧话新,亲亲热热,动了真情。还有几位年纪大的老人竟哭出了声来,引出了一汪我那缠绵悱恻的怀乡思亲的泪水。真是最纯洁的是乡情呀!我完全被乡亲们的情感给打动了。
二
第二天,母亲让我去看望二姨。说二姨常念叨我,我与二姨是有母子之情的。从小家里很穷,基本是二姨把我带大的。舐犊之情怎能忘怀。
当弟弟、弟媳在给我准备看望二姨的礼物时,表妹一脸秋色地把我叫到了一边,未启口脸先红。羞羞嗒嗒地说了半天,我才听明白表妹想让我帮忙。说她原来别人给她介绍的对象她不愿意相处了,男方让她赔偿青春损失费八千元,这是经过村里处理的,说一分钱也不能少,并且限期付清。表妹昨天来说是找我弟弟借钱的,见我要去看望二姨,表妹就灵机一动,有了想法,求上我了。说村支书和我二姨是一个村的,让我去找支书说说情看能不能少给一些。我一听就紧皱了眉头,大脑如吹进了一股寒风,我犹豫着,想着怎样才能推脱,可母亲此时也颤着小脚来难为我了,给表妹求情。我没法了,为了母亲,只好答应。
在二姨家吃午饭时,姨哥把村支书请来作陪。这个村的头面人物看样子五十多岁的年纪,相貌平平,精瘦、矮小,各个部位都好象是在做小本生意。但身体很好,红光满面的。头顶一块亮,头发全支边了。实际年纪也许没那么大,农村人显老。寒暄几句后我们便开始喝酒,酒是劣质的,菜也是猪肉为主力军。这就算农村人最好的排场了,平时谁也享用不起。几杯酒下肚,村支书便没了斯文,话也多了起来。看样子他很健谈,这可能是长期的农村工作给他赏赐的结果。话虽然有点土,但味道却很浓,臭豆腐似的,耐人回味。看来是个精明人,聊到高潮处,我瞅个机会就把表妹的事无可奈何地抛了出来。我一直担心这是给村支书出难题,怕他办不了,说了后又有点后悔。可没想到村支书对此事慷慨得让我吃惊。他没考虑一下就给答应了,嘴里正在全力以赴地忙着对付一块猪肉皮。来不及应声,就只好点头表示。这确实让我好一阵感动,忙起身连敬了村支书三杯酒。村支书受宠若惊,胀着脸,一口气喝出了个关公。
谁知还有一个更让我吃惊的事却早已悄悄地潜伏在我的身边,到话别时,村支书亮牌了,要把他的小儿子托付给我,说到我管的单位“混饭吃”。语气虽然有点试试探探、迂回曲折,但让你不好回绝。我忽然生出一种生意人亏了本的感觉来,但不得不暗暗佩服这位村支书的精明,受人一礼,还人一情,天经地意,岂能拒绝。恼得我牙根痒痒,暗暗地咬出了两个字来:交易!
现在人都懂得交易。
第二天早上,我在二姨家还没起床,就被一阵耀武扬威的汽车马达声理直气壮地把我从晨梦中叫醒。二姨没进门就敞亮着德高望重的嗓门对我说:“学良呀,快起来吧,乡里陈乡长开着车来接你呢。”我一时懵懂了,哪个陈乡长?当我还没完全彻底地从梦境中走出来时,就见一个气势磅礴的汉子喜笑颜开地走了进来。我心里一紧:这人怎么这样,满脸水土流失的样子,粗门大嗓,发笑时蠢不胜收,谁个见了都会胆颤心惊,让你自然而然地想出一个无法友好的词汇:匪气。我半爬起身,伸出手,虚晃着握了握对方送来的我极不情愿接纳的友情。
陈乡长可能没想到我对他的热情拜访和真诚客请会不屑一顾,听了我对他婉转曲折地回绝后马上就有了一脸坦白的不高兴。一张口便抖落下了随心所欲的直率:“汪局长,乡里乡亲的,给个面子嘛。咱们乡里就出了你这么一个大人物,多年不回来,大伙都想着,既然回来了,得去看看大伙吧?家乡人团聚团聚,哪又不去之理呢。”我想这家伙以前会不会是“屠夫”出身,不然怎么一张嘴,就这么直白和袒露?我直直地盯着陈乡长那张让人怒气横生的沟壑脸,论证了好半天,精心地在研究着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乡里的领导人。
我最终还是被陈乡长给俘虏去了。
乡政府还在老地方,与以前公社时期不同的就是多了一座气宇轩昂的五层办公大楼,这座大楼看样子对周围自惭形秽妄自菲薄的平房来说显得有点趾高气昂的样子。我到了乡政府,如答记者问似的接待了乡里的各位领导。人们群星拱月似的塞满了一屋人,一个个都向我投资了虔诚和敬意,这倒让我很受感动。
中午的酒宴是在政府会议室里摆开的。不苟言笑的会议长桌不得不一改往日的庄重和威严,委曲求全地担任起了酒桌的责任。美酒佳肴整整排满了一桌,透着家乡人的敦实和厚道。一只整鸡笑眯眯地蹲在瓷盆里对着憨头憨脑卧在盘子里的元鱼抒情。而元鱼却是一副拒色情永不沾的样子,只顾冲着支离破碎的兔肉出神,感叹着现代的人们对生活不知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奢侈,真是不可思议。旁观的鳝鱼可能出于同行的缘故,似乎在责怪元鱼的多管闲事而不识时务,眼看人皆醉,何忍独为醒?其他菜肴也都抱着苍天塌了大家顶,任你东西南北风的态度,急不可待地等着人们的光临和青睐。
人们入座后,把我吓了一个猛跳,足足不下三十人。乖乖,这是百鸡宴,还是吃大户?陈乡长来了一通大刀阔斧、气壮山河的祝酒词后就指使着大家给我敬酒。我自知不是打虎上山的杨子荣,一看他们喝酒的阵势和野气就心虚胆怯了,更不敢与他们轰轰烈烈地“甘洒热血写春秋”。这群人开始还算说得过去,似乎还有点知书达理的规矩味儿,可几斤白酒下肚后就不成了样子,要起义似的。在一阵咀嚼、咂嘴、饱嗝、恭维、吆喝声中,又开始了两军对垒,赖酒、推让、打赌、扯皮。紧接着便出现了剔牙缝、抠眼角、抹嘴巴、扒衣领、钻桌子、松裤带、上厕所……丑态百出、惨不忍睹,个个都露出了本性。划拳声、嘈杂声粗野蛮横地在小会议室里经久不息地冲撞着、厮杀着,把墙上挂着的那块“秉公廉政”的匾额惊得目瞪口呆,大惑不解。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粗暴蛮横漫无节制的声音在胸腔和耳鼓里横冲直撞,只好借尿遁上了厕所,点上一支烟蹬在那里悠着,想着农村贫血的经济怎么能支撑起这种大吃大喝的日子。可厕所的臭气不容忍我忧国忧民地去想,不多时就把我给哄撵了出来。
三
酒席还没有散去,乡政府大院里便又驶进来一辆小车,不一会儿,会议室外就走进来了一条汉子。陈乡长等人见了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呦,王县长来了!”
王县长打着哈哈,说句好热闹之类的话就把手伸向了我:“您就是汪局长吧?”
我忙站起,与他握手、寒暄、落座。王县长看来是专寻我来的,不知是谁告的密。看来这真是你方喝罢我登场。王县长一定要把我请到县政府去,并一脸坦诚地埋怨我眼里没有家乡的情份,回来也不和县政府打个招呼,没能得到县政府应有的照顾等等。我有一股苦涩之味上心头:家乡人这是怎么啦?热情得有点不讲情理了吧,偷着逃回来就是想寻找一个自由和清净的,这可倒好,一回来就落到了这种圈子里了,可这一切你又不能拒绝,还不能耍脾气,这是乡情,是友谊,是国粹,懂吗?想拒绝吗?对不起,不就是个司局级干部吗,回到家乡还这么拿架子?你见过毛老人回韶山的镜头与照片没有?那么大的伟人还对家乡人投注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呢?你算老几?唉,一切都由不了你!我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一声苦涩的叹息。
上车时,陈乡长作为家乡之主的身份非要送我一程不可,便不由分说地挤进了车里。可能是酒精的作用,一路上只有陈乡长说话的份儿,唠唠叨叨的,霸道地吵闹了一车厢的空气。前面有一段公路坏了,修路工人正在给公路开膛剖肚,车阻了好长一截。王县长下车去疏路,陈乡长逮住这个空当就把厚嘟嘟的嘴巴伸到我的耳边说:“汪局长,我自己有个小事想求你帮帮忙。我有个弟弟,在乡镇企业局干过好多年了,想动一动。我已经与县领导打过招呼了,王县长是抓人事的,想请你再帮我做做工作。”那口气好象我们早已是挚交。说着就给我塞“信封”,被我生气地回绝后,又厚着脸皮说事成之后一定有重谢。
我恼着脸,心里发出一层厚重的叹息。一路上,因心情不好,我的话语一直都很经济,直到王县长透露出我们是校友,又都是一中的学生、虽然隔了五届但都是陈老师教出来的弟子时,我才换成了一幅生动的图像来,话语也不那么绅士了,亮开了一脸的厚重。校友吗?毕竟是层关系,又何况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呢,就没有必要再去玩什么道貌岸然了吧。
到了县政府,王县长出于校友的情分邀请了我到他家里小坐,表示一下对校友的感情投资。他从内室翻箱倒柜地捧出一个精美的瓷瓶。启开封口,一股清香夺口而出。可能它们在瓷罐中禁锢得太久了,逮住这个出头露面的机会就拼着小命地朝外扩张,撩拨得满屋里都有了茶香。
“好茶!”我夸张地吸了吸鼻翼。
茶叶在玻璃杯里被沸水一冲,紧缩的体积就没了安分,慢慢地舒展开来。叶子渐渐还原了本来面目,充盈着碧绿,在杯里开始慢慢蠕动,转眼变成了浮浮沉沉荡荡漾漾的活物。喝一口,回肠荡气,沁人肺腑,疲劳顿消。我忍不住又叫了声好,问是什么茶。王县长一笑,轻描淡写而又无不夸耀地说:“贡品。上面有位领导让我们给他一家住在我们县的亲属安排工作,就给我馈赠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