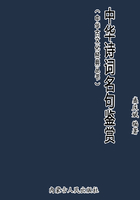石油工业部有两家大型炼油设计院,一个在北京,另一家在抚顺。抚顺炼油设计院文革期间迁至洛阳,即现今的中国石化总公司洛阳炼油设计院。他来了以后被分配到机械室。机械室的李主任是一位爱惜人才、刻苦实干的专家,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他分配到李主任手下真可谓三生有幸。他报到以后接受任务,先后编写了十二本炼厂设备设计准则,这个准则改变了技术上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况,取世界各国之长,主要是参考了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标准,使整体炼厂设备设计水平向前进了一大步。这个规范为抚顺炼油设计院采用,同时也为北京炼油设计院及当时国内一些炼厂的设计部门参考采用。这个规范大约用了二十年。
古巴卡斯特罗上台以后,中国由古巴取得了一全套美国在古巴所建炼厂的图纸,其中包括催化裂化等等,这比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先进一大步。这一套技术中国当时称之为“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中所采用的加热炉也比苏联“傻大黑粗”的方箱炉先进得多,但那种立式炉结构相当复杂,炉管和耐火砖都挂在钢架上。这种钢架用解析法很难计算,他与另一位工程师共同努力采用弯矩分配法(一种渐近法)藉助手摇机械式计算器进行计算终于获得成功。他还被邀请至北京炼油设计院做了讲座,后来这种方法在电脑推广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应用。几十年以后他碰到大庆炼油厂一位老专家,还谈起他和那种计算方法,不过那时他已离开炼油设计院从事管道工业了。
时隔数十年,回想起那段岁月能有机会为祖国做些贡献深感十分欣慰。李主任后来调至抚顺石油机械厂任厂长。相隔近四十年以后,有一次他和石油部一位副部长去东北“视察”,到抚顺石油机械厂后他提出要见见这位老厂长,可惜不巧这位老厂长在外地,未能见面,至今仍感十分遗憾。
他来到抚顺后,他们夫妻住在“鸡房”里。所谓“鸡房”是由养鸡场改造的“宿舍”。那是一个长条形的房子,中间用板隔开,住着许多人家。厕所在外面,是半露天的,在公共食堂吃饭。去时正值夏季,房间潮得长蘑菇,冬天外面北风呼啸,房间里点一个小煤炉子取暖。房间隔音很差,相互间只有10毫米的一层硬纸板。一年冬夜,隔壁一位老妇去世了,他清楚的听到老妇人痛苦的呻吟、越来越急促的喘息以及由这个世界走向那个未知世界的全过程,实际上他与老妇躺的位置相隔至多只有一个手掌长。
条件是艰难的,但夫妻相依为命、互相鼓励,感到内心还是温暖的,甚至算是他们的第二次蜜月。
在饥饿的年代,“人整人”暂时平息了,在文革之前他们分配到一间新居,是与另一个家庭合住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每家一间住房,合用厨房和厕所,条件比以前改善多了。他们非常珍惜这文革前短暂相对平静的几年,大家都争分夺秒的为祖国做工作并修补心灵上的创伤。
右派摘了帽子后称之为“摘帽右派”。和他同在机械室工作的另一位“摘帽右派”——老丁是地下党员,1949年以前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可谓出生入死的为共产党卖过命。1957年以前与党委书记闲聊时曾谈到一些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意见。反右时被那位书记“出卖”了,于是被打成右派。老丁平时沉默寡言,技术上也是精明强干。不久以后他与老丁成为挚友。他发现老丁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在文革初期在他还迷惑之中时,老丁一语道破,并分析那时的形势和可能的后果,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真与老丁所言几乎一丝不差。在他若干年以后下放到农村时,老丁已调至洛阳工作。老丁还辗转数日专程来农村看他,还带上六七岁的小女儿同行,这小女孩与他的儿子年龄相仿,大家挤在一个炕上,真是说不完的话。
大约三十余年以后这一切均已成难忘的回忆。老丁在文革结束后调至上海工作。他曾照原地址去过多封信都退回了,才想老丁可能已搬家了。有一天突然接到老丁的来信,原来老丁也正在找他。他因公去上海的机会很多,多次与老丁相会。老丁说那位书记曾写信来表示忏悔。并说该书记文革期间被整得更惨。他想此人能够忏悔也还有一点良知。有一天他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写一位女性在文革期间还是小学生时批斗北京原市长吴晗的场面,并写到她曾向吴晗脸上吐了一口痰,几十年过去了,她已四十有余了,内心仍感内疚和忏悔。他想这是一位好人,而那些曾沾满受难者的血的打手至今是否有忏悔之心?他们怎么教导自己的儿女?
抚顺市石油系统的右派初期都集中在一起劳动改造,他常常听难友们讲起张大勇(化名)的故事。大勇是个共产党员、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立过战功。复员后任抚顺某炼油厂的保卫科科长。鸣放时他对厂内某些领导搞特殊化提出意见,还说:“国民党才成立时提出建立共和、打倒列强,当时还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后来腐化堕落、脱离人民群众,最终被推翻了,我们要引以为戒”,反右时说大勇要组织群众推翻共产党,被打成极右分子。极右分子已接近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了,只给最低生话费、监督劳动。大勇曾有一位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四五岁的儿子,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祸从天上来,家庭分裂了,妻子离婚后去外地了,小男孩送到某收养所收养。大勇从早到晚干着苦力。
1960年中秋节,大勇和两个难友陪同一道去看望儿子——小胖。同屋的几个难友大家还凑钱买了几块高价点心。
当时正值饥饿的年代,小胖已经变成小瘦了。大勇拿出点心,儿子说:“爸爸,你先吃一口我才肯吃”,离别时小胖对大勇说:“爸爸,你把我接回家去吧,我再也不顽皮了,我还会帮助扫地、擦桌子”,父子二人泪如雨下。收养所的阿姨说:“小胖情况不好,肝炎已经腹水了。”
大勇回来后经常眼睛发直,总反复说一句话:“我的小胖脖子这么细,肚子这么大,我对不起儿子。”同房间的难友商量,把小胖接回来,大家还凑钱给孩子买了小被褥,和简单的玩具。在一个假日,两个难友陪着大勇去接孩子,另一个难友收拾房间,准备迎接小胖。他们凌晨出发要走上几个小时才能到收养所,傍晚回来时,孩子没有接来。
他们去晚了,几天前小胖已经离开人世了。阿姨说:“你的小胖真懂事,等到最后时刻,阿姨们要把他移到另一个房间去,小胖两个小手紧紧的拉住床头的木条不放,用最后的力气喊:“别把我抬走,我爸爸来就找不到我了。”
大勇两天没说话。大勇疯了。送入了精神病院。同房间几个难友凑钱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去看望大勇。大勇已经不认识人了,只会傻笑。难友把水果罐头给他,他把装水果的玻璃瓶子扔在地上,瓶子打碎了,然后趴在地下吃,把手、嘴都扎破了。
一个幸福家庭就这样破灭了。一个家庭和个人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是如此脆弱。
在饥饿的年代他们有了自己的唯一的孩子。妻子就在“鸡房”度过了妊娠中的困难的几个月。许多那几年生下来的孩子由于缺乏营养都是“O”型腿或“X”型腿。他的父母经常给他们带一些罐头等营养品来,孩子生出来腿是直的。他父亲是民主人士、著名专家,有些“特供”,他的父亲由自己的口中省下来的食品间接的给了孙子。1961年冬季他送妻子到火车站、扶她上了火车。两人商量孩子生下来就养在上海她的母亲家中。右派摘了帽子还叫摘帽右派,可能排到十八层地狱的第一层,但与“人民”、“同志”还有区别。他们不愿意让儿子看到父亲的屈辱,伤害了幼小的心灵。在火车站候车室中他们还为肚中的孩子祝福。在难分难舍中,火车徐徐开动了,他照例跟着火车跑了一段路,为了多看妻子一眼,为了多说一句话。
1961年11月6日他接到妻子打来的电报,“顺产生一男孩,母子均平安”。他在高兴之余也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在饥饿的年代,上层的政治斗争和下层争斗以及关于仇恨的宣传似乎平寂了很多。周末有时还举办个舞会、演场电影。可能对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摄取的那点热量只够勉强维持生存,“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也暂时来个中间休息。
据说有统计数字表明,那几年全国人口下降了,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有人说只甘肃省就饿死了四十余万人。是估多了,估少了,只有天知道。
经过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形势大有好转。但“阶级斗争”的形势也逐渐随之升级。设计部门开展了“向党交心运动”,每个人要写成书面材料,把从大跃进到大饥饿中的想法向党汇报。重点人物,包括他在内都要在会上讲,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那怕“一闪念”也不放过,把自己臭骂一顿。
几十年以后看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一篇散文,讲到当时一位人士向党交心时讲:“看了史记总觉得那位伟大人物有点像刘邦”,谁知这“一闪念”,惹下大祸,几天以后来了一辆警车,把那位人士带走,从此去向不明。
向党交心对重点人物也要人人过关。他谈了“自己感到大跃进时有些做法不讲科学,违背了自然规律”等等,虽然别人不断“提醒”、“启发”,他毕竟有了五七年的教训,决不会说出“×××像刘邦”这类话。总算蒙混过了关。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报纸上首先出现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接着是“破四旧”。再下来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摘帽右派中除了少数几位装的像乖孙子的人物以外,都列在“牛鬼蛇神”之列。他平时总是挺着腰板走路,他不懂得卑躬屈膝装出一副可怜相,所以牛鬼蛇神中当然缺不了他。妻子开玩笑对他说:“咱们是牛鬼蛇神中的神”,他说:“咱们做一对儒子牛也可以。”
在第一次批斗会上,主持会的人恶狠狠地指着他说:“你一个摘帽右派,有什么可神气的,你想翻天么?”他说:“我没有什么可神气的,更不想翻天,我只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地球上”。是啊,在那个时期,仇恨的教育和宣传,使一部分人习惯于看到一些人的卑微与下贱以显出他们自身的高贵。
他的话激怒了一些人,主持会的人大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口号。在这些口号声中他也听到一些牛鬼蛇神的边缘人物声嘶力竭在喊,似乎比别人喊得更起劲。他忽然想起童年时期一个邻居,当天黑时走进安静无人的小胡同时总要扯开嗓子唱几声京剧,而且多半是黄天霸、窦尔顿的花脸唱腔。他问这位邻居为什么养成这个习惯?邻居说:“唱几句壮壮胆子。”
可怜那几位边缘人物没隔几天照样挨了批斗,而且有的还吓得大小便失禁。
因为他“态度”不好,走廊上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他和他的妻子再随便加上一位就成为“三家村”,于是形成了好几个“三家村”,而且村村他都是村长。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人与他妻子点了一下头,他问:“这人是谁?”,他妻子笑着说:“你太官僚了,这不是你的村民么?”
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委幕后导演的,这些人已经习惯了,来了运动,先把“运动员”推上台,绝对整不到他们自己。他们没有想到这次突然方向一变,来了一个“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群众斗群众”,他立即解放了,但也没有参加运动的权利,仍然每天搞设计。但这个大转弯使他感到迷惑。他的好朋友老丁说:“一定是中央内部分裂了”,果然如老丁所说,不久***被揪出来了。
此后,各级的“当权派”开始挨整了,而那些过去挨过他们整的人成了大大小小的“战斗队”,“造反团”中的积极分子。那些“神气活现”的各级“长官”戴高帽、挂牌子、挨批、挨揍、90度大弯腰——。他们求饶、检讨、臭骂自己、互相揭发“狗咬狗”,居然和过去那些“运动员”们的表现如此相似。
人啊,都是一样的人。各级“整人者”就像木偶一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面都有几根绳子牵着。有一次斗争会上他看到一个“当权派”,大约五十多岁了,深深地弯着腰,不时还有造反派把头按下去,这人汗水向下流,聚成一摊水。台上的人控诉这个当权派如何整人。他一时思绪万千,他想难道他们性本恶么?还是那种环境使他们的灵魂彻底的扭曲了?是上面的绳子牵着他们不得不这么做还是他们自身的病态心理,就像有的德国**爱听在酷刑中人的嚎叫声么?他一时想不明白。
几十年以后他遇到一个曾经做过某大学书记的老相识。这位书记在那个年代整过不少人,造反派起来也把他整得死去活来。这位老相识邀他共同进餐。进餐中那位老相识说:“我真羡慕你呀!”他说:“世界上那有羡慕右派的?22年的苦啊!人生有几个22年?”老相识说:“我整过人,你当我心理好受么?你当我是自愿去做的么?上面的指示不执行成么?白天动员,晚上自己偷偷落泪!”他又说起木偶的比喻,那位老相识说:“不光是一举一动上面绳子牵着,会上动员一副面孔,会下回到家了对着不会出卖自己的妻子把面具拿下又是一副面孔。”老相识的夫人几十年前还算是一个美人,如今已满头白发。她指着自己的丈夫说:“这位经常偷偷流泪,至今患着失眠症,就是那时留下的根。”酒喝到半醉,那位曾做过书记的老相识说:“我对不起一些人,如果真有天堂、地狱,我应该下地狱,也宁可下地狱”,他说:“别难受,你可以向挨整的人道歉,这些人会原谅你的”,老相识回答说:“来不及了,这些人已含冤走了。”说着竟放声哭起来。这位老相识在中学时是他的好朋友,在一段时间听说那位的一些“劣迹”,他内心只承认是他的老相识,此后在他心中这位老相识又成了老朋友。
在文革中他写了“我有一个梦”这首诗,这梦能成真么?何时能成真呢?还永远是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有一天从梦中醒来
在我的祖国
不再把人分成梭罗门刹帝利和
不可接触者
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是兄弟
我有一个梦
有一天从梦中醒来
在我的祖国
摆脱了世袭的诛连
人们只按他的内涵
来判断他的善和恶强与弱
而不是根据他的老子
和祖宗
我有一个梦
有一天从梦中醒来
大家忘记了仇恨的宣传
当一个人跌倒了
多数人都会伸出手来
拉他一把
而不是落井下石再踏上一只脚
当一个人取得成就
多数人都会为他庆贺
而不是暗中捅他一刀
我有一个梦
多么甜蜜的梦
终于有一天
在我的祖国
没有皇帝也没有奴隶
没有黑名单也没有告密
没有规定
作家必须写什么
画家必须画什么
没有规定
必须歌颂什么
必须咒骂什么
必须怎么想
必须怎么说
我深深相信
终于有一天
从梦中醒来
窗外是灿烂的阳光
孩子们拉着手唱
我们都是好朋友
在群众团体之间的武斗开始了。武斗漫延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场面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他成了真正的逍遥派,利用这短暂的自由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年迈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