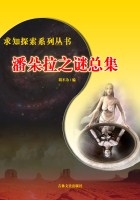当然,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是不能和这些伟人们相提并论的,但由此我们可观照到,我们所面临的痛苦是何等的渺小,没有理由感到痛不欲生。或者说我们要用知识扩展自己的视野,提升我们的境界,只有我们的思想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承载更多的我们自以为是的痛苦。
用我们的老话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2006年8月5日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阅读笔记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获奖小说的名单中,有两位我对其作品熟悉的作者,一个是葛水平,一个是迟子建。葛水平的《喊山》看过,但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没有看过。我急不可耐地在网上找寻。幸运,找到了。我之所以那样急切,一是因为迟子建并不陌生,二是从媒体上得知,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蒋巍于颁奖前夕辞职,所以我想知道这篇小说获奖的理由。
迟子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魔术师丈夫因意外车祸丧生,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哀伤,决定去三山湖旅行。在路上遇到山体滑坡,在一个叫乌塘的地方下了车。
真正的故事从这里展开。
乌塘是一个盛产煤炭的地方,这里寡妇特多。原因是大多的男人在井下劳动时死亡了。这种现象导致外省的女人都喜欢往这嫁,叫嫁死。
女人嫁过来以后,就是等着男人在井下死亡,这样好继承一份分不菲的死亡赔偿金。在这个小镇上作者“我”遇到了蒋白嫂。蒋白嫂的男人在一个煤矿发生事故的当天失踪了,失踪原因有些扑朔迷离,煤矿说他没有上班。蒋白嫂说早晨上班走后没有回来。蒋白嫂为此而疯癫,和镇上不三不四的男人喝酒。害怕黑夜,尤其害怕停电的夜晚。偶遇停电的夜晚,她就像疯了一般,大呼小叫,而电一来她就平静了。看作者对蒋白嫂一次停电后的描写:
蒋白嫂跺着脚哭叫着,我要电!我要电!这世道还有没有公平,让我一个女人呆在黑暗中!我要电,我要电啊!这世上的夜晚怎么这么黑呀!蒋白嫂悲痛欲绝,咒骂一个产煤的地方竟然还会停电,那些矿工出生入死的掘出的煤为什么不让它们发光。
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为了争取光明而如此激愤,而这光明又必须是由电而生的。
作者在行文过程中通过次要人物交代,说煤矿死十个人要上报,所以矿上只准九个人下井,九个人下井如果发生事故死亡,那这九个人也就算白死了。如果你从事过煤矿工作或生活在生产煤炭的地方时,这个时候,你也许会明白作者往下要讲的故事,或者会对故事的结局有几分把握了。当我读到作者对蒋白嫂生疑,要和蒋白嫂喝酒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在暗黑的苍穹中一道闪电,知道不久会有一声响彻夜空的炸雷在头顶掠过。我虽然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当我看到谜底的时候,我仍然惊诧不已:
我将冰柜上的东西一一挪在窗台上,掀起冰柜盖,一团白色的寒气迷雾般飞旋而出,待寒气散尽,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情景:一个面容被严重损毁的男人蜷褪坐在里面,他双臂交织,微垂着头,膝盖上放着一顶黄色矿帽,似在沉思。他的那身蓝布衣裳,已挂了一层浓霜,而他的头上,也落满霜雪,好像一个端坐在冰山脚下的人。
我没有想到我看到的竟是这样一幅画面,尽管作者提示到了里屋传来嗡嗡的声音。
我曾长期生活在矿山,我家乡的煤矿随处可见,我也写过这类题材的小说。比这残酷的场面我也见过,但面对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艺术修养的欠缺。我看到了作者怎样将生活中的事件巧妙地融进了小说里,怎样将生活中的事件进行提炼,成为一件接近完美的艺术品。
小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脑子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这篇小说仿佛一个透明的琥珀,琥珀里有只蚂蚁,看上去是一件非常精致的艺术品。
迟子建的能力在于她把琥珀里那只静静的蚂蚁在被树脂缠绕的过程中的那种痛苦、挣扎的过程表现出来。这是我要学习的东西。要是我来结构这篇小说,可能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迟子建仍在叙述她的故事……
第六章是小说的最后一章:“永别于清流”。清流是离三山湖最远最清澈的一条小溪。本来作者“我”的终点是三山湖,怎么又跑到了清流?
这又是一个单独的故事。在三山湖“我”看到了一个独臂人和一个孩子在卖火山石,这个小孩不像一般人一样吆喝,而是变些小杂耍吸引游人。
一天兴致颇高的我给他顺手展示了一个小魔术,以此便走进了孩子的内心世界。这又是一个不幸的家庭……
当“我”和小男孩儿云岭在华美、清丽的月光下、在蜿蜒曲折、水声潺潺的清流河边放起一个蓝瓜、一个莲花形的河灯的时候,作者的境界升华了: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夜晚是迟子建的夜晚,也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夜晚,世界上可能有多少个像蒋白嫂和云岭这样不幸的人群,他们的夜晚不仅充满悲伤,甚至是悲惨的。那么我个人的哀痛和这些人比较而言也就不那么的举足轻重了。因为迟子建曾这样说过“我要回到虚构的生活中,我忽然觉得我为之拥抱的我很衷情的甚至视为生命的现实生活,能那么轻易地把我抛弃了,能那么快地把我的生活变成另一种状态。只有我的写作生活,我的文学人物还很安静地、原封不动地在原位。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有一种生活——我虚构的生活,它们是永恒的。
迟子建个人的哀痛是真实的。因为几年前自己的丈夫不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在自己的哀痛中她将自己的内心转向写作的时候,将她的视角转向大众底层的时候,她发现了令她更大的哀痛——底层人群的哀痛的时候,个人的哀痛也就显得那么的微弱了。她通过写作从个人的哀痛中走出来,获得了艺术创作以及她个人的生命的幸福。
这就是迟子建。把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能作为有用的素材用在小说里,表面看起来是依靠作者的生花妙笔,实际上是对作者的考验,是作者功力的显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情节是用作者“我”的一次旅行这根线串起来的,把一路的所见所闻组织成了一篇小说。实际上是作者平时对生活的思考和积淀。正应了那一句老话: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换句话说,生活中有的是写作的素材,缺少的是用一种睿智、敏锐的精神高度来思考生活。
我觉得中国的鲁迅文学奖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鲁迅的精神,《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奖就是例证。愿真正的作家们能够永远保持鲁迅的风骨和精神!
看她的小说我想到关于语言的叙述问题:我们可以不可以和作者较真。
在小说里,实际上有两种语言,有人物纯粹的语言,有作者自己的语言,有作者在代替人物叙事时无形中使用了自己的语言,在这篇小说中也同样地出现了。当然在全知的叙事方式中无可避免地要渗透作者的语言风格,在小说中通常看到,在貌似人物的语言里看到了作者自己的语言,看来一定是被允许的。
2007年11月21日
荒诞中的真实
——读余华的《兄弟》有感
读余华的《兄弟》后,有种明显的感觉就是,感觉到余华在语言的叙述和情节的推进上从“文学的神坛”走向“文学的大众”。我这里所指的意思是有一类文学作品是评论家、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属阳春白雪,这类作品大多供奉在神圣的文坛上,有一种作品通俗易懂属于大众的文学,是普通读者都喜欢看的文学作品。而《兄弟》的问世,评论家不看好,普通的读者却喜欢。本有想法表达,恰巧在网上看到李敬泽先生的一篇文章,正好借题发挥。在余华的《兄弟》未出版之前,负有远见的、着名的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写了一篇《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一文。他在文中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兄弟》是简单的。简单到足以令人震撼。
二、四十年来的经验被简化为善恶斗争。
三、他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
四、余华不是站在人物的里面,他是站在人物的外面来写,说到底余华也就是讲了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
五、余华降低了他的志向,误用了他的才能。说到底,《兄弟》是一部失败之作。
这就是着名的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对余华的《兄弟》所作的评判。
我们不能贸然说李敬泽先生所作的评论是错误或者是武断的,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们只能认为李先生的评判《兄弟》所用的标杆是非常之高的,高到什么程度?令普通的读者匪夷所思。不过正好表现出评判者的高深。在李文《原谅我的不恭》中原话是这样讲的:小说家余华的神秘力量在于,他在根本上是简单的,他一直能够拎出简明、抽象、负于洞见的模式,告诉我们,此即人生。如同真理是朴素的,余华的简单总是令人震撼的。
分析李先生的语言有些自相矛盾,如果余华的简单具有神秘的力量,那么余华是简单的吗?余华的简单足以令人震撼!李先生是正话反说?
还是在真的讽刺余华的简单?如果是说余华真的简单,起码应该在震撼两字加上个引号吧。是疏忽?还是大家风范?如果不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李先生可以不遵守语言的规则,你们这些草民也必须明白“评论大家”所表达的意思?
如果李先生把余华的《兄弟》说成是四十年来的经验被简化成善恶斗争,那么李先生真的把余华的《兄弟》说简单了。《兄弟》真的像李先生说得那样简单吗?我看未必。
我认为,余华利用他的荒诞的故事、荒诞的情节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现实生活中上演的故事远比余华的小说来得更荒诞,更真实,也更犀利。作为一本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现实生活的本身有许多的极限性,作者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窠臼”对作者的掣肘。这是任何人不能荒诞中的真实
回避的。所以用荒诞的故事,荒诞的情节来表现真实的现实,是余华的聪明,这也恰恰是余华的不简单。
撇开李光头不说,林红的性格转变轨迹,可以说振聋发聩的,林红是一个多么纯情的女人,她的堕落使我想到了陈希我在《抓痒》中描写的女主人公。如果《抓痒》的女主人公和老张的偷情是人性的使然,那么林红的变化可以说是社会在裂变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宋刚可以不死,但活着也只是苟且偷生。
李光头的发迹,是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李光头上升。李光头是简单的,但裹挟着李光头上升的社会却是不简单的,是复杂的,是令人深思的。
李先生在文章中说:余华一向是冷静而决断的叙述者,现在,他的决断发展为无根据的武断,发展到蔑视人的可能性和人的选择。我觉得这句话正好适用于李先生,他对《兄弟》的评判是武断的。是一管之见。
李先生说:余华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他对人在复杂境遇下的复杂动机并不敏感,他无法细致有力地论证人物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对余华是否是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我不做评论,只是觉得李先生所说:他无法细致有力地论证人物——这样的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
余华是写小说的,如果作者在一篇小说里细致地来论证人物,它还是一篇小说吗?李先生作为一个评论家可以论证作品的人物是否可信,而余华却不能在他的小说里来论证它的人物。比如李光头这个几岁的孩子一定要去摩擦电线杆子,这是用细节来表现人物,你可以论证这个细节的真实与否,但是你要去再仔细推理李光头为什么会去摩擦电线杆子,那么余华的《兄弟》会不堪重负的。
李先生认为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
作家在描写作品中人物的时候,视角的选择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作家可以用全知的视角描写,也可以深入人物的内心来刻画人物。李先生的论调是一种苛责。如果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光是站在人物的外面来写,那是无法想象的。可能《兄弟》靠叙述来推进情节的发展的地方较多,略显急躁和行文的仓促。实际上也不尽然,一部上乘的作品和酿酒一样需要过滤、发酵,而余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透视现实,聚焦现实生活中荒诞的一面,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余华的《兄弟》
是简单的,那么还有什么作品是复杂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西方工业革命后出现的道德沦丧以及文化的危机,相当一部分的人,甚至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都无一例外成了物欲的奴仆,但愿通过智慧的人们去努力、去尽量缩短这种残酷的过程。
我认为余华的《兄弟》已经触及到了我们的灵魂,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丑恶、荒诞甚至是可怕的一面。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能读到余华《兄弟》中的荒诞中的庄严、调侃中的严肃,而作为着名的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却看出了《兄弟》的简单。当然李评论家高瞻远瞩,见多读广。是否可以给文学的草民们,推荐一些李先生认为复杂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厚重之作?因为作为一个着名的评论家是有话语权的。
谈到评论家,使我想到,评论家、作家应该是什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责任?我忽然想起格非先生的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作家他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应该形成一种对视。实际上,余华是一个有勇气的作家,他并没有消融现实中的紧张感,丧失锐气。相反,在荒诞的背后,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在《兄弟》中我看到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的良知。凭余华多年积累的经验还不至于江郎才尽。他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荒诞的李光头,和蜕变的林红,还有无法活着的宋刚,那么,足以见证到生活中李光头和林红之流实在不是少数。如果李光头和林红成了生活中的大多数的话,我们的生活将是多么的悲哀?仅凭这一点,能说《兄弟》是简单的吗?
2006年5月7日
读《紫阳花日记》
作者在小说中这样写道:紫阳花自古以来在日本是野生的,有“聚集蓝色”的意思,故也被叫做“集蓝花”,另外也叫“盔甲花”。紫阳花的颜色会根据土壤性质的不同而改变,如碱性的就开红花,酸性土壤就变成紫色的。所以又叫七色花或八色花。
此花的花语是:花心、水性杨花、善变。
渡边淳一是日本一位特殊的作家,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原因就是作者写了众多的婚外情。紫阳花日记,也是一篇有关婚外情的小说。
不同的是不像以前的小说,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而在这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最后对自己的另一半给予了妥协。
作者本人因对性爱大胆的描写,曾多次受到社会的抗议,但作者毫不为此所动。作者认为:做爱是男女情感的最高境界,它可以融化一切,这很重要。作者自己说:移情别恋,不能用好坏来判断,作为小说家,我只想写出人的本性,写作过程中,我追求人的本质和真相,从不考虑这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我想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作者才能写出男女之间感情丰沛、感人至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