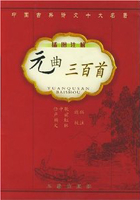母亲送走瞎子回来,我尿湿了半条褥子。我踢腾着小脚为自己的杰作高兴着,还把小拳头擩进嘴里,使劲地啃着。
母亲掐着我的两条小胳膊把我抱起来,我把屁裙子和小棉裤都弄湿了。母亲给我脱掉屁裙和裤子,用一条干褥子把我裹起来,放在炕的另一头,再把我尿湿的褥子拿到火炕上去“礴”。
“礴”是村里的人的叫法,就是把东西铺到火炉子上烘干。把红薯切成片放到炉火沿上叫“礴”红薯,把花椒放到炉火沿上叫“礴”花椒。
褥子“礴”干了,就看见上面印下一幅地图,母亲就亲着我的小脸跟爸爸说,快看看,你闺女画的地图。父亲就抱着我在屋子里转圈,一边开心的笑。
母亲说,我在三岁的时候就不再尿床了。母亲说我三岁的时候,其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刚刚一年零八个月。母亲说的是虚岁,算上了我在母亲肚子里呆的那十个月。
母亲说,我是村子里最干净的孩子,三岁上就不尿床了。不像别的孩子,上小学还尿床呢。村里有一个男人,母亲说他18岁的时候还跟他娘睡觉,晚上尿床弄得他娘一身的尿水。我就“哧哧”地笑,觉得母亲说得有点夸张。
但在我6岁的时候,我就突然尿了一次床。
那天晚上,母亲很晚都没回家,我一个人睡在炕上。我记得那是个冬天,也许是快过年了。父亲也不在,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在。我半夜醒来时,一盏煤油灯孤零零地立在墙头上,灯里的油好像快熬干了,灯捻子上的火苗一跳一跳的,也快要熄灭了。
我害怕极了,缩在被子里,竖着耳朵,想听到母亲回家的声音,哪怕是姐姐哥哥有一个人在家也好啊!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屋背后隔墙传来闹洞房的声音。我记不得当时是谁娶媳妇。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人尖着嗓子在唱村里人非常熟悉的那种小调:“一颗鸡蛋两头光,两颗鸡蛋配一双,三颗鸡蛋不成对,四颗鸡蛋成一方,五颗鸡蛋一不溜溜长,同志们今天来送房……”
我知道全家人都去看娶媳妇去了。妈妈去给人家当“跟随婆”。“跟随婆”
是什么呀,就是包着被子,提着尿盆儿跟在新娘后面转圈的那个人。这“跟随婆”在村里是有讲究的,黄毛丫头(没结过婚的女孩)不能当,死了男人的寡妇不能当,跌了孩子不够百天的妇女不能当。村里人说小产孩子叫跌孩子。人家说母亲是个全乎人,就是符合“跟随婆”条件的最佳人选。
对这个角色,母亲很是乐意,连孩子都撇在家里不管了。当然母亲一定是交代姐姐哥哥在家看我的,姐姐哥哥却趁我睡着的时候,悄悄跑出去,看闹洞房了。
父亲呢?父亲也不要我了吗?我非常伤心非常失望地窝在被子里。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那天晚上在家伙上帮人家拉二胡。父亲会拉二胡,谁家娶媳妇嫁闺女,他都去凑凑热闹。其实我父亲是真的很喜欢乐器,可惜在他几十年的村干部生涯中,他的特长没有派上用场。
那小调没完没了的唱着,似乎要一直唱下去,我简直是忍无可忍了。要知道我是被尿憋醒的,我紧紧地夹着两腿,生怕尿了床,妈妈说了我是全村最干净的孩子,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尿在床上的。
尿憋得我忘记了害怕,我爬起来对着窗户大声地喊:“妈妈——妈妈——”
听见母亲回家的脚步声,我忍不住“哇”
地哭了。我尿了床,带着满心的委屈冲湿了整整半条褥子。
第二天,母亲把湿褥子拿到太阳下去晒的时候,我就躲在家里,羞得一天没有出门。
那是我最后一次尿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