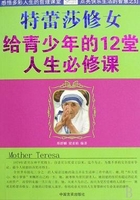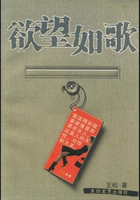村里有狼,村里真的有狼。母亲说,她从山上摘松蛾子回来,就看见过一只狼,一只全身银灰的狼,直立在村对面的黄土圪嘴上。狼的两个耳朵尖尖地朝天直竖着,狼的两只眼睛闪着幽绿幽绿的光。母亲远远地看着狼,不敢走也不敢动。姥姥说,碰见狼,千万不能跑,要么站着不动,要么低下头慢慢挪开。总之,“山神”是惊动不得的。
村里人把狼敬为山神,守护着大山,守望着村庄的山神。于是在半懂不懂的幼提时代,我对狼就有了一种神秘的敬畏。我常常在梦里梦见一只大灰狼摇摇摆摆漫步在山村的沟沟岭岭,以守护神的姿态巡视着大山,巡视着山村。山村与狼的种种传说与故事也在懵懵懂懂的记忆与幻想中沉淀成一种情愫,对狼,对山村,对童年,或远或近,如真似幻。
我四岁半的时候,开始在老西屋和老院子进进出出地玩。母亲说,不敢跑远了,村里有狼。母亲的话让我感到害怕,我就站在老院子的大门外,目光怯怯地四处张望。我看见村子对面土圪嘴上的那棵黑松和土圪嘴下面的那个山洞,我把眼睛使劲瞪得很大,母亲说,土圪嘴上有狼,我怎么只能看见那棵黑松,是不是狼藏在了黑松的背后,那个山洞一定是狼的家吧?狼为啥不出来呢?狼会到村里来吗?狼会吃人吗?
我就坐在老院子的大门口奇离古怪地想着,这时候,老东屋奶奶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在我旁边的石头上坐下,她把两只“粽子”一样裹着的小脚搁在大门外的石台阶上,然后把我的头搂过来。她说,丫头呀,你娘怎敢让你一个人跑出来?让狼叼了去,看她哭荒天也没泪。你那大伯伯就是让狼叼了去哩,我那可怜的孩儿,都是娘不操心,害了我那苦命的孩儿啊——老东屋奶奶眼泪哗哗地就哭开了,我被吓坏了,挣开老东屋奶奶的手,撒腿就往大门里跑。
我边跑边拼命地喊妈妈。母亲听到我急促的叫喊声,以为村里小男孩欺负我,急急忙忙从屋子里奔出来,一把把我抱进怀里。母亲问,咋了?咋了?我说,老东屋奶奶哭了。我指着大门口。母亲一句话没再说,抱着我回了老西屋。
我坐在炕头上。火沿边搁了一圈煮熟的红薯,我一边吃一边问母亲,大伯伯是谁?老东屋奶奶说他被狼叼了去。母亲告诉我,老东屋奶奶有个儿子,论辈分,你该叫他大伯伯。他三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家人铺了草席在院子里乘凉。天上有月儿,有星星,老东屋奶奶高兴地教儿子数星星。突然刮来一阵冷风,天就黑了一阵儿。等月儿再露脸的时候,大伯伯就不见了,一家人急得满地找。找了一夜,也没找着儿子。村里有人说,看见一只狼叼着一个小孩往村外跑了。老天爷,不当活活的,真伤眼儿呐!母亲说的时候,眼睛也有些红了。我却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害怕,真正的害怕。好多天,我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尤其不敢出大门。
我生怕狼把我叼走,狼把我叼走了,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我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恐慌。出门紧紧地拽住母亲的衣角,村里人就说,看看这个小尾巴。
那天晚上,父亲背着我去古庙听书,回来的时候,四周都是黑糊糊的。我特别紧张,爬在父亲背上动也不敢动,唯恐一只大灰狼从后面扑上来,把我拖了去。
父亲却不知道我害怕,还学着说书人的腔调,唱起了“谷子好,谷子好”。这是瞎子富才的名段。我说,爸,我害怕。父亲说,怕啥?爸爸背着,你还怕?我说,我真的怕。父亲说,怕啥,狼又不会吃你。我说,我就怕狼。父亲说,不怕,狼不吃好人。
那天晚上父亲给我讲了一个他和狼的遭遇。
父亲说,他从川康边境打完仗,一路步行着到了西安。在西安,部队给士兵发战利品每人一双黄球鞋。父亲领到的是一双一顺鞋,父亲就穿着那双一顺鞋回到了家乡。我不知道父亲是坐火车还是走路回到高平县城,但我知道,从县城到村里,父亲走了两个小时,到村边的时候,天已经是半夜。父亲从来不怕走黑路。可那天晚上,父亲却非常恐惧,因为在村口,一只狼跟上了他。父亲感觉到了身后的声音和狼带来的冷飕飕寒意。父亲不敢回头。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从背上取下战友送给他的一把二胡拉起来,“吱吱咕咕”的二胡声在寂静的山村回荡开来,狼的脚步慢了下来,远远地跟在父亲后面。父亲的手在瑟瑟地发抖,或高或低颤颤巍巍的二胡声像是无助的求救声,远远地就传到奶奶的耳朵里,奶奶知道是父亲回来了,急忙起来开门,没等奶奶把顶门圪叉放好,父亲就一头撞了进来,嘴里喊着,快,快关门。奶奶赶紧把门关上。父亲慌不择言地说,狼,狼,山神,山神。奶奶和爷爷惊得大睁着眼。父亲说,山神用脑袋顶我的屁股。父亲吓得话也说不成句。奶奶说,谢天谢地,不当活活的,狼不吃苦命的孩儿。
第二天,奶奶去庙上给山神烧香。
父亲的故事让我迷糊了很久,狼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居然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苦命人,谁不是,可大伯伯也是苦命孩儿,怎么会被狼叼走?我简直想不明白,越想越迷糊。
在我6岁的时候,姐姐15岁。母亲说,女孩念书不顶甚。
就叫姐姐去村里的碗窑上离碗边,挣工分。一天深夜,我被一阵哭声惊醒,我看见姐姐坐在炕上哭得泪人一样。母亲端着一碗热汤给姐姐喝。母亲说,不怕,孩儿,山神老爷不吃好人,不吃善良的人,山神老爷是怕你一个人回家害怕,把你送回来了,山神老爷也送过你爸,山神老爷对咱家有恩呐。
第二天,母亲就带了我和姐姐去庙上给山神老爷烧香。
路上,我问姐姐,你看见狼了?姐姐说,看见了,还不止一只。
我说,你看见几只?姐姐说,三只。我吓了一跳,问,三只什么?
姐姐说,三只狼。我说,怎么就看见了?姐姐说,从碗窑上加完班出来,走到大庙底,就看见那三只狼了。我说,你不怕?
姐姐说,起头,我以为是狗,它们一直跟着我走到咱家大门口,爸出来接我的时候,脸都吓白了,爸跟我说,那不是狗,是狼。
是狼把我送回来的。我一听是狼就吓哭了。可母亲说,狼不吃好人,姐姐就不哭了。
我也很想看见一只狼,看见一只充满了人性和灵性的“山神”,可是直到我长大离开山村,也没见过狼。
村里人和狼的感情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敬畏与对立的恐惧中一代代延续下来。他们无法想象,大山里没有狼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一种似乎缺失了威严与敬畏的生存状态,也许并不是村里人所想要的理想状态。
狼的劣迹与善行在我心里留下一个个矛盾的结,就像大山里一个个不知名的山洞一直盘存在我的心里,那里似乎永远藏着一个人类无法到达无法揭开的秘密。
而我确信村里有狼,确信狼就像一个淳朴而又凶狠,善良而又狡黠的猎户,守护着大山,守护着我们永远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