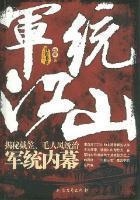从一早起,当王通司向我们宣布这间遥远的石房,我们的情绪就活跃起来了。古工程师特别兴奋,他想个屋顶快想出病了,有两次,他的大肚子差点被飞石击中……一块像他肚子那么大的飞石……
我得让他住进去,不管什么代价——除了杀人。
“你跟他说,我给他烟,带酒味的烟,包里的全给他……”
“他不会要。”
“他要什么?”
王通司摇摇头。
好吧,豁出去了。我在那个摔扁的包里掏摸了一阵,把枪交给许元元,只身推开门。
藏人退了一步,异常敏捷地抓起枪……
我朝他摊开手心。
他不相信地看着我……我的手仍摊着——两块核桃大的岩盐……
他一把抓了过去,用舌头舔了舔,舔完一块再舔一块……轮流地舔,不断地,轻轻地,狂热地,久久地舔着,久久,久久地舔着……他女子伸过舌头,被他推开了……那暗红色的灵巧的舌头又伸了过来……
他从土色的藏袍里取出一只脏脏的羊皮小口袋,万分小心地将盐装了进去……口袋藏在胸口,拍了两拍……一遍遍舔完手掌……他没说话,出门,拎着赵子军的背包又进来了。
他们也进来了……
我陪她爬了次山,爬到叫“鸡心包”的采伐点。
路上我才弄明白,她叫王兮,不是王分。怪字。
(“帝高阳之苗裔兮”的“兮”,她说。)
几乎没路。常常得从倒桩的树身爬过,从枯朽的树下钻过。坡度在40°-60°之间。她喜欢伸手抓点什么,第一次抓到一手野木耳,她高兴地叫了,第二次抓住了“美人脱衣”的荆条,她也叫了,不过叫得伤感。
——真疼!哦,刺人的东西也这么美!
翠绿的荆条,刺是嫩红的。确实美。
她喘得像头母牛……
——还走么,歇不歇?
——走。
已经听见油锯的叫声……
倒桩了——
那是树精,树王……即使倒下,也把周围的草木吓个不轻……它死得不失尊严。
大树倒下了,长长的一声叹息……用力一挣……山跳了一下……
她数着年轮。
35°以上的坡,只能用青冈斧,最先进的工具往往也是最死板的。我注意到,不总是按着部颁标准。规定:伐桩不能高于上坡面5公分……
在鸡心包的那两个小时,她从一棵树转到另一棵树。居然没转晕,她的上衣红得呛人,像一团跳动的火焰……她为每棵树送葬,像个尽职的神甫……她也扮演了屠夫,挥着青冈斧没上没下地砍,不到一分钟,连人带斧子甩了出去……她跪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没让她用油锯,我要他们别给。她很不高兴,但她对我无可奈何。我看得出,她那骂人的话就要出口了,强咽下去。再过几天,可就没这么客气……
她学到了一组新的术语:伐区,伐块……迎门树,砍片,留弦,挂耳……一直到倒桩。倒桩后的断筒、圆头、小头小面……更新林,过熟林,防火道……长材,材积……移床育苗……
她用斧背敲着树干,试弹力,听声音……如有空响便腐朽了……但愿不是……
午饭在山上吃了。工人们匀出干粮,在火上烤着,挺香,挺脆。山高了,饭不容易煮熟……她的上衣红得耀眼。她一口接一口地吞着馒头,她敢吃麻辣了……冬天只能吃冷的,不能生火,连抽烟都不自在,“一人带火,集体抽烟”……
工人们看她。
她不怕人看。
他们的家眷百分之八十几都在山外……
下山时,她拄着工人给她削的树棍,一跳一跳地走在前头……她夸着天,夸着地,夸山,夸树,夸水,特别夸工人……当然,她不会夸我。
我捡起她的采访笔记还她。她把掉出来的花草标本一一夹好。
谁都没有说话,谁都不再洗脸。连有洁癖的古工程师也免了。他即使在山里也天天擦身,擦半小时,直到那个大肚子红扑扑的……
地上铺着草,我们围着火睡。很挤。枪在我的手边,我把子弹退出,藏了……苏富贵紧跟着赵子军睡着了……一片鼾声……
经过这一回,我大概死心了,我想,他没什么盼头了。那藏女和衣睡在火塘的另一边,脸朝着我们……眼睛睁得很大,藏人朝她说了句什么,她仍看着苏富贵……我睡在最外面,古工程师靠墙而眠,他心满意足地打着鼾……她看了一会儿苏富贵,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
真暖和……
藏人坐在门边,不断地抽着自产自销的蓝花烟(呛人得很),眼睛不时瞥一眼屋外。我没去理他,他不会怎么的。
他怕头人派人来杀我们。
他放了一夜哨。
他不是个称职的哨兵。
清晨,许元元大惊小怪地把我推醒。
“醒醒……跑了……醒醒!”
包还在,跑不了。只是人不见了,那女子也不见了。
“没事(王通司说),他跟那女子去放羊耍了……”
“耍?”
四川话中,这“耍”字可大有讲究。
我朝大山乱吼一阵,我像受伤的老熊……他胆敢骗我……惊起几只雀子,惊走一只松鼠。查不出脚印……
山很大很大……天气很好。
藏人在砍他的柴,动作准确有力……我让他们整好行装,就等苏富贵了。
他在羊吃饱后回来了。他一个人朝山上爬来,爬山爬得气喘,他脸红了……他背起背包,把古全良的那个也背上。
“上哪儿了?”
“上山……看林相。”
“看清楚了?”
他说,看清了。
“你眼力不错呵!”
他把背包放了下来。他看看许元元和古全良,指望他们能说几句。他们没说。
“想生儿子了?”
他说没想过。
“走吧,没什么大事(王通司拦在中间),算不上……”
我要他站开去。我用的是“诛心术”。
“你要是还干净,背上包前头走。要不,自己找路吧……”
“不要我了?”
“把钱拿着,够花到川西坝子的,咱们算是朋友一场,两清了。”
苏富贵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跟了好长一段,跟得人心疼。他无声无息,像头觅食的豹子。他以为我会叫回他的。我没松口(我叫许元元别管闲事,于是,古工程师也住了口)。我就当没看见他,连晚上他生起的那堆篝火也没看见。
他跟了我们三天……
我背着古全良的背包,背得出汗,背得只想骂娘……
看完正在整修的渠道,我们上麻尔柯河边的208场,那里住着二百七十三个职工,一九八○年才建场。十五公里公路,花了一百六十万元。
围着火开会……听……讲……她手忙脚乱地记着,还不时提问。她对那张《四川森林分布图》兴趣十足。
回202场的路上,小张把车停在崖边,从工具箱摸出几管炸药。他说今晚上有鱼吃了。他吃鱼的劲头和赵子军一样大。
她胆战心惊地看着,给他递绳递石块。装雷管时,小张叫她走开,去路边望风,见人见车就叫一声。
他两管一组地缠着,小心地夹上雷管,还绑了块石片加重。一组有半公斤黄药。
第一声闷响从水底传出后,我们都瞪着水面(回水区,震昏的鱼漂不走)……一股浊流,冒了几个泡……完了。
第二组和第三组齐爆,炸药脱手正是时候,脚下微微一震……依然空空的。剩下一管药,没雷管了,小张死了心。
——没鱼吧?
——有!运气不好……
小张开着他的车,这以后,再没说活。
晚上,在她住的寝室里,满满的一屋人。孩子都认识她了,自信地进来,排列在墙边……发电机不正常,电灯时亮时暗,灯丝红红的……小伙子们先是端坐着,然后,靠在一个个空床上。山里人直率,豪爽。
端来收录机,干电绑成一束,放着软软的歌……
她的床头点着蜡烛,她在本子上记着,不时记一两句。
孩子们被赶了出去。小伙子们一个接一个讲着或心酸或甜美的爱情故事……大部分是心酸的,太甜的故事只能自己享受……他们想家,也想家乡的姑娘。家乡……金堂,双流,温江,蒲江,射洪,北川,旺苍,盐亭,江油,什邡,绵竹、绵阳,中江……一个人就是一个县,每个县都有美丽温柔的姑娘……
白天,他们是快乐的一群……
电停了好久,他们才散……明天还得上山。他们把自己的心事倒给伙伴,倒给了这个“下江佬”后,各自去寻他们的梦了。
她还在写着……我进去时,她正在写信,用圆珠笔写在赤桦的树皮上,那是好心的小伙子们为她剥来的,厚厚的一卷。
皮尺的头拴在许元元的后腰,他像游着蛙泳,双手向前,拨开枝条荆棘。有时得用砍刀。我们走在獐子路上。走五十米,许元元停下,等拉着他衣角的古工程师描画草图,技术上的问题,我们都听他的。
要不要苏富贵得听我的。
我用望远镜察看河道和林相。实测和目测结合。
石头的大小,数量,位置;河道的宽窄,走向,流速,主流,支流,岔河……树种,树龄,材积;坡度,覆盖率……
就这样一米一米地量过去,从汉源的富林镇量到分水处的可尔因,量到足木足河的龙头滩。
没等量到丹巴,我被王海的电报召了回去(这个电报走了三天)。
王通司溜走了。
他以死亡相威胁,不叫我们过惊心梁子。我不听他的,我们只有过去。他劝了又劝,一直劝到我发了火……
那晚,我们露宿在大岩嘴下。
他是半夜里走的,只带走唯一没打破的那瓶泸州大曲,他不贪。他大概逃向了四家寨。
地上,是他用树棍画的草图:
大岩嘴,落鹰陀,响水沟,惊心梁子(!),阎王土扁,财神岩,猴子岩,巴郎沟口……他也画了俄日、四家寨、孔玉的位置(那时,孔玉区在山上)。
他在草图边画了面大大的经幡,想叫佛保佑我们,谢谢他的好意。他确实怕了,不然,不会在离怀抱石还有四五天路程时就匆匆逃走……他连钱都没领,只带了一瓶酒。
绝壁……
惊心梁子玄又玄,
牛舔盐巴二百钱……
大渡河上下谁都会唱。
阎王土扁的对河是鬼招手……
怀抱石在金星梁子上,贴着绝壁的路,到这里拐了个弯……抱住石头,慢慢转过去……千万别低头看河……在宽仅一个脚窝的毛毛路上,把麻窝子脱了,光着脚板死死巴住……踩巴实了,慢慢地转,像牛舔盐巴似的拱身抱石……抱紧了……
下去就是一百多米,水葬是现成的……掉进喧嚣的大渡河,连声响都听不到。
古全良的身体前倾,转成背部向下,朝河坠去,手抓着空气,叫声像一声叹息。他没来得及为这最后一声吸够空气……
他下去了,没有声响。
看着他下坠,觉得自己也在沉降……
慢慢地,浮起两个字:枪毙。
我不怕被枪毙,但怕这该死的路,怕到心里……
古全良还没走到怀抱石就下去了,赵子军走在他后面……他的粗壮的腰被崖边突起的石头碰了一下……腿本来就是软的。
古全良成了大渡河的第一根单漂……
他不知漂到了哪里,始终没人知道。
“煤矿工埋了没有死,流送工死了没有埋……”
经过达维公社时,她执意要下去看看。
她的红衣,凉帽,照相机,它们引来的孩童……
索桥上飘着许多幅经幡……
她捧在手中,读不出白布上的经文。那是用印板印上去的。
——你也不懂?
——不懂。藏民一般也不懂,喇嘛可能懂几句,也可能不懂。
——哦,藏文是这样的……
它挂在桥上、杆子上,据说是图个吉利(民族的事,我知道不多)……风整日整夜吹着,一遍又一遍读着经文,能消灾治病,祛凶呈祥……
——据说,红四方面军曾在这一带开荒筹粮。
——可靠?
——不是据说么?(我喜欢她的红上衣了。山里,红色特别艳。宽宽松松的,却又合体,后背的风帽一跳一跳的,像她的小辫。)红军到过这里,这是历史,不是传说。中共中央曾在小金开会……
——懋功会议?
——是的。四十多年前。
——我们到不到泸定?
这一路,非得经过泸定。
——安顺场……哦,跑马山呀!
跑马山不算什么,它不像唱的那么美。
——不美也去,不会不美……
于是,她老是唱那首《康定情歌》,“溜溜”个不停。
喝完茶出来,我们上山,去烈士墓。她在路边顺手采了几颗野花椒,揉搓着,放在鼻尖下闻闻。
陪我们的派出所所长不爱多说,他是羌人。
蓝天白云,阳光灿烂……
它比画报上介绍过的那些烈士陵园都小,建在坡上……我到过这里。她上前,读了简短的碑文,还在本上记着。
……叛乱。土匪包围了区政府,全部汉人束手就擒……那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夜,火烧得很红……一刀一刀地杀,没一个幸免……事后,开来了大军……于是,达赖逃亡出境,各地相继平定……
她把花椒籽撒在坟前。她采了几朵小小的野花放在坟前,放在一个六岁男孩的小坟前。花是蓝的。
——这,真的?
我点点头。
——你怕么?
她问羌人。羌人习惯地摸了摸手枪,他笑了笑:
——现在不会了。
我们被压到河边。我们没枪。
土匪要工人交出队长,工人请他们抽烟,告诉说队长上雅安开会了。他们信了,他们不狡猾。他们说,是头人要他们来的,佛的旨意。他们不打工人。头人说,这是和毛主席打冤家,头人说,队长是毛主席的娃子,要杀。
他们抢走我们的工具(藏人非常喜欢铁),留下的话是叫我们滚蛋——这山这水是他们的,佛赐给他们的。
很快,开了杀戒……
我杀过一个报信的土匪。我通知附近的寨子去收尸。我要他们想想清楚。
再来,他们没占到便宜。山头架着机枪,从朝鲜回来的汉子们在日夜警戒。弹药充足……河边炮声隆隆,炸山清河……他们集体冲锋,个个挺胸而立,非常难得的肉靶……我没要工人瞄准(他们和美国佬干过),能不打就不打……子弹在他们头上划了几组扇面,想把他们压得趴下。
他们从不趴下。
这有点像……狩猎。他们几乎撞上了我们的枪口……退却来得和冲锋一样快……我们并不追击。打扫战场,竟不见任何战利品。
打了几次后,我们奉命撤出。
大军进山……民主改革……
我们队损失七个工人(土匪的枪法很准),都是被土枪击倒的。其中的一个追随古工程师下了河,其余的都埋在山上。
一百多人,轮番刨坑。土层太薄,不得已,放了几炮。
我听信工人们的话,下葬时,全队的干部提着哭丧棒,全都披麻戴孝……
从可尔因起,是大水局的区段。
水运处建在克什米。
下午,她说去爬可尔因水运处对面的山。这儿的山都没名,见上面有个废弃的碉堡,人们叫它“碉堡山”。
我记不清自己是否爬过。
从索桥过河,从学校的后门上山。
山高不足二百米,虽没正式的路,还算好走……小雨……她让我在学校里等,我摇摇头,跟上她……操场上有一大群孩子。
她走得很快,气也喘得很快。
一个孩子在山下叫……
他拼命挥手。走错路了,不站在路上就看不出路来。我们回头,他才住手,依然抬头看着我们。
路是一串“之”字。
从岩洞前经过,门是木板草草拼成的,岩壁已被熏黑……门前用荆条挡着。
她说想进去。
——有人吗?
门没上锁。她因没主人而退走了。她渴望看一眼洞内陈设,她说,说不定能找到一幅岩画呢!她说她酷爱岩画。
她在一丛紫蓝色的野花前不走了。她在衣袋里掏摸着。
——采花?
——不,不是。你回避一下。
我回避了。她始终没有叫我,我尴尬地等了很久……傻够了,我朝山上大叫了几声……她的回音很弱。
她已到了山顶。
——你在哪儿?
——进洞了,我在碉堡里。别进来,好黑!
碉堡用河边的有棱有角的石块砌成,手艺不坏。笔直的十几公尺,没一点灰浆……它至少已有三十年……绕过去才发现洞口,唯一的一个进口,枪眼式的进口……洞口离地三米,没梯子很难上去。她是抠着石缝爬的……一失手可能坏事,下面是陡坡,只长灌木的陡坡。
——有银子!刘利长,你走开,扔出来啦,富矿!
她扔出一块地地道道的石头。她说“见者有份”,我让她别傻了。不过有几颗云母碎屑罢了,丹巴遍地都是。我坐在碉堡坍了的角上等她。那儿能避雨。我抽烟。
碉堡用来防范匪患——一家子躲进去,底层常年备枪备粮备水。也为了名气,修得越高越有名,这不是一般人家修得起的……石头从河边扛来,上万块石头,上万人次的上山下河……周围的树木一律剪除,以开阔视野,以杜绝火攻……如今,既没土匪也不要名气,修好的也废弃了,人都搬下山去。
她爬到最高的那个枪眼,朝远山笑着。
她的声音渐渐近了。
她恐怖地宣布,发现了绝命书!
——搞错了,不是的,一张学生作业……
照完相,我们在望得见碉堡的一块坡地上坐下。她砍来一根“美人脱衣”,将嫩红的刺一颗颗掰下。她说,它美得可以,接着又说,是恶毒的美……她还记着被扎的疼痛……后来,她终于息怒,说它只不过调皮罢了。
我含着一颗“救济粮”。
她一颗接一颗地吃。
相传断粮的红军吃它,因此叫做“救济粮”。红果又小又涩。大自然总是有点仁慈的。
她吃着,吐出硬硬的籽。
——告诉你,刚才我怕了。
——会吗?
——我怕你不上来,我忘了招呼你。听到你的喘气,我觉得安全。我知道是你,别人不这么喘气。听熟了。
我问她碉堡里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