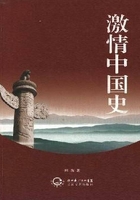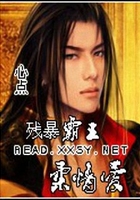“对啊,我确实是掉了魂。慢慢地,我悟出来了,回味到十四年前我也有这种压迫的痛苦感。那时,我孑然一身下放到偏僻、闭塞、穷困的龙源大队,我是被剥夺了助产士的权利下来的——说我为父亲鸣冤叫屈,对红五类实行阶级报复,等等,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就别提了。从冬到夏,开头半年,我失魂落魄。干了六年的接生工作,听惯了婴儿坠地的呱呱声、产妇呼天唤娘的呻吟声,看惯了产妇‘苦尽甜来’的疲惫而幸福的笑脸,生活在来苏水的特殊气味中,一下子转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真不是滋味。记得那是个繁星满天的夏夜,我拖着就要肢解的身架回到我的‘窝’里,举目无亲,‘双抢’一整天,还得自己动手煮饭烧水。我蓬头垢面、懒心懒意地坐在灶前烧火。透过窗棂,夏的夜空映入我的眼帘。我突然发疯似的想念你们,幻觉出现了,你们果真来了,我哭呀,笑呀,叫呀,再也不是孤零零的一人了!然而一阵阵悲怆的、撕人心肺的哭喊声把我拉回了现实,凭我多年的职业习惯,生离死别亦不过如此,我本能地冲了出去——是隔壁程婶家。她那临盆的媳妇浑身痉挛,两眼翻白,牙关紧咬。程婶跪在厅堂中连连叫菩萨保佑,程婶的亲家母在呼天抢地,另两个好事的老太婆慌里慌张地拿剪刀、菜刀往房门、堂屋门上挂,吆喝着,驱邪呢!这是破旧立新的岁月中真实的一幕。‘子痫!’——大脑皮层很快作出了判断。我旁若无人地冲了进去,抓住产妇的手按了下脉搏,便镇静地下达命令:‘筷子!毛巾!快请接生员!’也许是我确实有医师的气质,一时间,筷子、毛巾很快递到,程婶也不拜菩萨了,帮着我用筷子卷着毛巾强行塞进产妇上下牙之间,防止抽搐时将舌头咬断。程婶结结巴巴地告诉我:‘根生去叫接生员了,去了好半天呢。’这时,接生员——大队书记的邋邋遢遢的婆娘背着药箱一颠一颠地赶来了,她一看就傻了眼:‘哎呀,这还救得到?你们家往公社抬吧。’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产妇正在发作中,需要绝对安静,公社离这里还有二三十里山路,路上出危险怎么办!我吸了口气,平静地问:‘有胎头吸引器吗?’我晓得她最近参加了县里办的‘接生员培训班’,怀着一线希望问。‘好像有吧。’这位没文化年纪也不轻的冒牌‘知青’支吾着。还好,总算从药箱里找到了。我果断地说:‘你配合我!程婶,您快快准备好开水、肥皂、两盏马灯!根生,快把吸引器和橡皮手套放到一个干干净净的锅里煮半个钟头!煮好后连锅端来,千万不要用手去拈!’我的头脑异常清醒,临危不乱是医生应有的素质。啊,魂灵又附体了,我又感受到叱咤风云的指挥员、奋不顾身的战斗员的滋味,什么忧郁惆怅,全见鬼去吧!我守候在产妇身旁,在接生员的帮助下,给她的人中、内关、照海扎针灸。开水来了,我洗了三遍手,戴上皮手套,进行检查,产妇的宫口开全了,产妇此时也处于间歇中,我拿起了‘胎头吸引器’,准确地插到胎头,让接生员协助我吸出吸引器里残存的空气,利用真空吸附的原理助产,幽着劲一下、两下……婴儿出来了!浑身青紫,羊水窒息。我二话没说,一把将胎头吸引器上的小皮管拔下,将一头插入孩子的口腔内,用嘴猛力一吸,一股腥臭味直冲鼻喉,一口羊水来不及吐出就咽了下去。顾不了这些,我不停地一口一口将婴儿呼吸道中的羊水吸出来。然后,人工呼吸、口对口呼吸顽强地交替进行,婴儿终于‘苦哇……’哭出了第一声!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一下晕倒了。待我醒过来时,已是旭日临窗了,程婶端了一大碗荷包蛋和面条来,她老泪纵横:‘你是华佗再世哟!吃价的妹俚,菩萨保佑你找个好老公!’从那以后,老表们没有哪个不大鸣大放地喊我魏医师,他们早就提前给我‘平反’了。”玲玲停了停,文静地呷了一口橘子汁,慢慢地品着,像品味着幸福的乳汁。
女伴们钦佩地望着她,分享着她的幸福。
“可是现在……”玲玲兴奋的脸色突然黯淡下去一口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说你呀,也不要太和自己过不去。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也还是绿叶精神噢。”憨大姐居然来了点文学色彩的词语。
“我却更愿做一朵山野的小花。”玲玲动了情,眼中波光闪闪,不知是泪水还是激情的火花在闪烁。一个人的心恐怕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吧!“人心不得足”是句贬义的老古话,可是,人生的追求哪能停止呢?!
“快十一点了,我免了吧。”柳青举起瘦嶙嶙的左手腕,就着月色吃力地看看那表壳发黄的半钢上海表。
“这两天住院部修理大门,不关——”叶芸话一出口,立刻后悔了,赶快带住。
难堪的沉默。
玲玲突然冲动地说:“柳青,我回去就跟老莫说,要他通通路子,你马上转院到上海广慈医院看看。”
叶芸也把烟蒂一扔,立了起来:“我这就去电讯大楼拍加急电报,要老头子电汇三百元,再为我续假一个月,我陪你去上海、无锡、苏州到处逛逛。”
淑华粗糙的手掌又急急地抹了一把鼻头的汗珠,急不可待地说:“对了,对了,我家老杨跟文教局人事科长原是同窗好友,我要老杨今晚就去求他,你一定得调回省城来,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眼镜片一片模糊,喉头哽噎得厉害,柳青什么也说不出。猛地,她抓过纽扣奋力向上一掷,掉下来,在石桌上滚了几滚,掉到脚下的青草坪上了。三位女友不约而同地蹲下去寻找,淑华干脆蹶起个大屁股匍匐在草地上。叶芸的火柴发挥作用了,一根,一根,又一根,微弱的火苗跳跃着,绿茵茵的草地上,璀璨的有机玻璃扣闪闪发光。“乌拉!”叶芸和玲玲同声欢呼,淑华也出人意料地灵活地“蹦”了起来。
充满激情地相望。此时无声胜有声,也许应该结尾了吧!
“真的,我是幸福的,真正幸福的。真的。”柳青的声音微微颤抖,她取下眼镜,撩起衣服下摆揩了揩镜片——唉,岁月改变人呵。这动作,全是农妇下意识的举止;这“真的、真的”,不禁令人想起祥林嫂的口头禅。三位女友不觉怆然。也许该赶紧说“明儿见”了!
“再坐一会儿吧,让我说说。”柳青不容分说地坐回到石凳上。
女友们只得狐疑地坐下。她将说什么呢?她能说什么呢?
“你们如果能像小时候那样理解我、信赖我,该多好呀!”柳青微微蹙着眉,注视着迷茫的夜色,像是执着地寻觅什么。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叹: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柳青的吟诵像山间泉水叮咚,但淌进三位女友心中却是透骨的冰凉,令人无不愀然。
“古人哀叹‘终需一个土馒头’,今人也得正视‘骨灰撒江河’,两眼一闭,好像什么荣辱毁誉全不相干了,追悼会是开给活人看的。哦,我要给你们讲的是——我却已经享受了真诚的追悼会的幸福——”
“你胡说些什么呀!”淑华一跺脚,厚实的大手掌一下捂住了柳青的嘴。
玲玲拼命用手绢扇着风,明天,明天无论如何要强迫她作个全面检查,神经该不会受过什么强烈刺激吧?
叶芸狠狠地把另一只口袋上的装饰扣硬扯了下来。
“看你们呀,一个个心情沉重得像是跟遗体告别似的。”柳青掰开淑华的手掌,眉开眼笑起来,“我也是凡人呵,当死神过早地向我招手的时候,我何尝不害怕?不悲痛欲绝?况且我还是一个孤身的敏感的学文的女人呢?……记得前天早上四点多钟,晨星寥落,清风习习,我孑然一身,拎着一只瘪瘪的旅行袋往汽车站走去。前一天,我在县医院办好了转院手续,拒绝了汪校长派人护送的好意。眼下正值‘双抢’大忙季节,农村中小学老师多与包产到户有瓜葛的。何况我除了消瘦、没劲之外,一切都能自理。我要汪校长不要惊动任何老师,否则我要变脸!我逼着他回去,我自信是坚强的。然而,走着走着,我却后悔了。巨大的孤独感包围着我,从几天来医生的眼神、护士吞吞吐吐的言辞、校长过分的热心和深藏的焦虑中,我判断出我的病情是严重的。四十岁就要回首平生,未免太残酷了。在农村执教十五年,山野村小九年,公社中学六年,虽然被老表们视为‘文曲星’,被学校当做‘顶梁柱’,然而逝去的岁月只能用‘默默无闻’四个字来概括!到了汽车站,看看表,离开车还有十来分钟。汽车站前已是沸沸扬扬的一片:叫卖肉包子糖烧饼的,摆开场面炸油饼油条和煮香喷喷猪血汤的,卖西瓜、梨瓜的……把个寂静的黎明搅得乌烟瘴气,却硬是热热闹闹,充满活力。我的心战栗了:生活,毕竟是令人留恋的。”
夜,静悄悄。大概是最后一批回院的病人好奇地瞅着她们。
“我晓得开往地区的大头客车总是停在场地的东北角,像老表们一样,我不进站,却从破围墙斜插进去。怎么?今天去地区的人这么多?黑压压的一片,农忙还有这么多‘跑单帮’的?莫不是我眼花了?我使劲地眨了眨眼,透过薄雾般的星曦,啊,我像电击一般呆住了!
“天啊,我看见了什么?我听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在我的眼前,是我的一群学生,大至离校数年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客客气气的小村姑,小至奶声奶气的初中崽仂妹俚,还有妹俚的小弟妹——穿着开裆裤的鼻涕娃!他们密密集集地将我围住了。呵,汪校长头天黄昏时才骑车回去的,这么说,孩子们——真的,在老师的眼里,学生不论长多大永远是孩子——是连夜赶了四五十里山路来的呵,一抹曙光照在他们热汗淋淋的脸庞上……
“我听见了,我的忠于我、爱我的学生们的呼唤:
“‘柳老师!柳老师——’
“‘看好了病就回来噢——’
“‘开学时我们来接你——’
“我像疯子一样扑向我的学生,泪眼婆娑,不能自禁。我弯下腰,紧紧地抱住了近前的一个鼻涕娃——他是女生香妹的老弟,我允许女生带弟妹上学。要不,多少女生得失学呵——我的灼热的嘴唇疯狂地吻着他那张满是汗水还有点鼻涕的小脸蛋,我已是热泪纵横了!痛痛快快地哭吧!
“这是幸福的哭泣!我自小没有父亲,参加工作不久又失去了母亲,没有兄弟姊妹,没有丈夫子女,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时至今日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来的山村女教师,可我,却得到了人世间最崇高、最纯真的爱。真的!”
柳青泣不成声,她取下了眼镜,又撩起衣角擦拭镜片,用手背揩了揩满脸的泪水——瞧,地道的老表动作。然而,三个女友却悟出了什么;她们深情地注视着她:“真的,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哦,我太激动了。”柳青戴好眼镜,轻轻地吐了口气:“后来呀,人围得越来越多,老表嘛,孤陋寡闻的,总想碰上不要钱的新闻。这时,喇叭声响个不停,夹杂着耀武扬威的司机们粗鲁的大喝大叫声。糟糕,我脱车了?一位排除万难挤进来的女检票员拉着我的衣袖:‘你是要去地区的老师啵?快上车?’我启齿想解释一下,她却只管扯着我往外挤:‘我都晓得,你们校长全对我们讲了。’拉扯着上了车,我正准备接受司机的斥责和乘客们的埋怨,谁知满车的人对我嚷嚷些什么呀:‘老师,你坐前面,1号座位归你坐。’我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时,几个乘车妇女已手忙脚乱地把我按在1号位上了。忙乱中,我发现我的旅行袋不见了?而香妹、秋菊、牛崽、田生几个正吃力地拎了一只饱饱鼓鼓的旅行袋上来,是我的袋吗?怎么?我还没反应过来,又有几个学生硬往车门上挤:‘我的蛋?我的还没放进去呵?’‘还有我的?’……天?鸡蛋在农村中是视为最佳营养品的,尤其是这大伏天。‘不要?不要?’我忙不迭地摆手,又急急地弯下腰去拉提包拉链,香妹她们则拼命按住我的手,挤进来的学生又把蛋往我身上放,全乱套了?乱套了?司机霍地站了起来,他把半个身子探了过来,递过一只司机用的铁水桶,粗野地吼道:‘吃得?没有毒?把蛋放进桶里,震不坏?快?’
“车缓缓开动了,乡下妹俚崽仂哭成了一片,我忽然感到生的欲望是这样的强烈。车拐上公路时,一个矮笃笃的老头扯着嗓子对着车厢喊:‘我——不准——老师来?同学——劝不住?你好了——就回?我们——等你?’是汪校长呵,我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号啕大哭。”
玲玲用手绢捂着嘴,不叫自己哭出来,叶芸和淑华不约而同地递上果子露和苹果,柳青不偏不倚地呷了一口果子露,咬了一口苹果,气氛又活跃了。柳青朝着叶芸说:“叶子,我违例了,现在补一段格言吧。‘当我死时,世界呀,请在你的沉默中,替我留着“我已经爱过了”这句话吧。’”
“泰戈尔?”玲玲和叶芸都叫了起来。
柳青却自顾自地说下去:“长时间以来,我总以为是对他的奇特的爱才使我如此眷恋这块贫瘠的土地,他——是位医科大学生,十五年前跟我一道到公社报到,‘同是天涯沦落人’,可是,当我们的爱刚萌芽时,一个电闪雷鸣的夏夜,他为抢救一位病人出诊,失足掉下了山崖?他爱我吗?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可是我爱他、刻骨铭心地爱他?”
三位女友震惊了,她们心中掀过强烈的爱的波澜——原来是这样!
“然而现在我明白了,是他对人民的博大深沉的爱激发了我,是他对事业不屈不挠的爱振奋了我?我爱他,我就该爱我的事业!那山野中的不正规的学校,那平庸朴实的乡下崽仂妹俚正是我的理想结晶所在。”
柳青昂扬地站了起来,潇洒地两手一摊:“邂逅畅谈到此结束,让我们携手去迎接更美好灿烂的明天吧?”
“你——还是我们的圆心儿。”
四双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月儿高挂在深邃的夜空,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依依惜别。
事业、理想、奋斗、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一切,是多么的复杂,处处是问号。女人们啊,答案在哪儿呢?
(原载198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