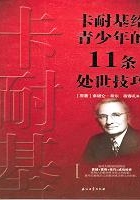十九岁,学生头,粉红衣,白球鞋,上课,看书,批改作业。学生哭我也哭,学生笑我也笑。生活像水一样透明、单纯。
1986年8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我坐在窗下看书,突然听到你唤我的声音,甜美,满含春花绽放的笑意。
你,头戴红旅行帽,身穿靛青短衫,一手扶着、一脚搭着似乎随时会飞走的旧二八型自行车,正汗津津笑微微地在台阶下望我。
“你……你是王希?!”我竟一下子叫出了你的名字,至今想来都觉惊奇,因为我从没和你说过话,也没在意过你。那个读书时一直坐在我前排、个头矮小、笑起来露出整齐白牙的初中同学。
见我叫出你名字,你更欣喜地望着我。奇怪,在你我四目相对的刹那,我在你眼里发现了黛绿色光芒!我从未见过的黛绿色,我们黄种人眼中所不可能有的色彩,它四射的光芒触电般击中了我。我一惊,心“咯噔”一下:依稀记得哪本书上说过,凡能在常人眼里看出不同的光彩,一定是与之有不寻常缘分的人。“不可能!”我自嘲了一下,立马镇定下来。
可缘分还是先你一步抵达。那一眼,多年来我铭记于心。在今后不管多长的岁月里,它使我相信:世界上最动人、最含蓄、最不可言语、最富有想象隽永的诗,便是你那一眼。
是不是我们身上具有能相互感应的特殊物质,一相遇就把奇异的现象汇聚到你的眼眸里?
我没问过当时你见我的瞬间感觉,也许感觉是双向的。
自那一眼后,我们便开始了通信往来。你告诉我大学里的见闻、想法,我告诉你其他同学的情况、我的学生趣事。你称我颦儿一样的姑娘,我叫你王希同学。你是我生活的染料,有了你,水一样的生活多彩起来。这样过了半年,你说喜欢我。我看信后,哈哈大笑,称你小小弟。那时我已有了朦朦胧胧的情愫,但对象不是你。直到有一天,我和他“不可以”,失落回家的车上,恰巧遇上放长假回家的你。你给我买来了我爱读的书,还意外带来一条粉红色紧身裤。第一次送女孩礼物,岂有送内裤的?多不好意思啊,我怎么也不肯要,你放到我手上,就跑,说我穿了一定很好看。最动人的是你的笑,你笑起来很感染人,那是糖溶入水的感染力,再怎么阴雨的天都能在你脸上看到明媚的阳光。你的歌声也很动听,富有磁性。你把学校学来的新歌,一首一首唱给我听,还给我讲故事念诗。夏天,我休息,你站着或坐在一边,帮我打扇、驱蚊蝇。冬天,有一回,你趁无人的时候,羞涩地帮我暖被褥。几乎整个寒暑假,你都找借口,想方设法赖在我家,帮我家割稻子、插秧,年前扫灰,我还记得你红肿的手。即便你父母责骂、兄嫂讥讽,其他求婚者隔三差五来我家,你仍一如既往。但你又是那么稚笨!一次,你来我家,大老远见我妈从菜园回来,你大步迎上去,情急中竟昏头呆脑地连叫了两声“老吕”,只因我姓吕。我妈左顾右盼,方知你叫她,气得不行。再怎么,你也不该叫四十来岁的我妈“老吕”啊!记得你和我妈闲聊时,毫不忌讳地说,你跟班上的女同学关系很好,你知道她们藏钱的地方,她们称你小弟,你甚至说,跟她们跳舞怕对不起我。我妈听了故意拷问你,会不会对我负责?你随口答道:现在做朋友不要负责,今后做妻子要负责。你的坦诚让我感到隐隐的不安。
但青春的激情如连绵的芳草,密密匝匝,满天茵绿。爱情是芳草地上的风,从一株草到另一株草,忙碌穿梭。我们爱上了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迷上了缠绵婉约的唐诗宋词。有一次,竟然相隔几千里在同一时间读琼瑶的同一篇小说。我们在写信等信中开始了“甜蜜的苦役”。你靛青色短衫、像女孩般用扇子遮脸的俏皮一笑、好看精致的牙、习惯性的轻咳、出门拍整衣服用手理发的动作、你靠过的树、坐过的椅子……你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我百读不厌的经典。因你的只言片语、一颦一笑,我要么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要么神魂颠倒、悲伤垂泪。为了慰藉我的思念之苦,你曾花去半个多月的课余时间,别出心裁录制了一盒磁带,捎来了你的歌声,寄寓了你的相思。我收到后如获至宝,一个人反锁着门,在房里痴迷地听了一遍又一遍,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发呆,一个来月沉醉其中茶饭不思。除了你,我谁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想看,只想将心一把掏出来压到你的心上,脆弱得像晶莹的露珠,一有风吹草动,便“扑”地一声碎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瘦成一根线都吊得起的人。
那几年,世间万事万物都映出你的影像,发出你的声音,连和我朝夕相伴的书都成了魔镜,自然而然映出你的笑脸。爱屋及乌,我喜欢上了殷勤的绿衣邮差,喜欢他带着诡秘的笑说:有你的信!成天想着“得成比目何辞死,做成鸳鸯不羡仙”。
你把最美的诗句“莲子青如水”中的“莲子”二字,带着“怜子”爱我之意送给我。我制造了一个有着“清泉石上流”境界的“沰”字送给你,白天黑夜地唤着。爱在诗情画意和自我臆想中茁壮成长。
爱情是一个危险的客人,这个客人却长居我心。你四年大学求学生涯,一年仅两次的见面,使得我“莲子青青心独苦,一唱将离,日日风兼雨”。因为爱的自私和强烈的占有欲,我常常幻想连篇,疑心重重。记得一回,你在信中无意说了美人鱼由爱而幻灭成泡影的童话,使得我心绪难平,似乎你就是那个多情王子,终将爱上另一位公主。于是情到深处人孤独,“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结果失眠多梦、头痛心悸,患上了神经衰弱症,足足折磨了我一年多。
尽管头痛,我仍精心算好日子,用芙蓉花瓣拼贴了一个“沰”字寄给你,恰在你生日那天抵达。由爱而成诗人的我在花瓣图上赋诗,名曰《莲语》:“假如你用心泉汇成池/我就是你万千碧波/亭立的莲/二十年的期待/催开粉红花瓣/片片融合清露与阳光/我将用我一生的凋零绽放/化作节节的相思/守候你缤纷的梦想。”我希望自己的爱像阳光,包围着你,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
那段日子,我天天吃茯神、当归、远志、天麻……炖鸽子、鸡等加强营养,仍无济于事。我知道,你便是我最好的补品、最好的药。1988年正月,你我有了一个月的倾心厮守,我的病才豁然痊愈,也有了我们的初吻。还记得么?我们齿齿相吻的笨拙。你窘着脸羞涩地说:我……我吻不来。尔后,我们模仿琼瑶小说里写的样子,伸出舌头,缱绻着嘴唇,吻得昏天暗地。我们巴不得钻进对方的肚子里,融为一体。这年夏天,我穿一件玫瑰色连衣裙,显得楚楚动人,你怔怔地看着我,忍不住用灼灼的目光乞求:“我想看看你的……”我不忍拂你的意,用仿若不是自己的手褪下了衣领,在你的惊愕面前,不由自主地哭了。当时我想,自己最宝贵的身子都让你看了,你会一辈子珍惜么?而我自这时起,已决心嫁给你,守身如玉地等待你。
吻我之后,你赠给我一首歌德的《对月》诗:“你用慰藉的目光/照我的园邸/就像知友的眼光/怜我的遭际……我曾一度占有/可贵的至宝/我永不能置之脑后/这真是烦恼/喧响吧,莫要停留/向山谷流去/流去,合着我的歌/鸣奏出旋律……”我的身子、我的心被你的眼、你的吻敲开了心花,不能,再也不能回归平静。
那时,就连写信,我都左思右想下不了决心。不写信,恐你挂念;写信,也恐你挂念。课余饭后,一有时间,我就要在信上和你说几句。每次将你的信投入邮筒后,心里便若有所失、怏怏不乐,仿佛是与你分别。你成了我残酷的白马王子。
记得一位诗人说过:女人一旦爱上了某个男人,就想和他生个孩子。果然,深爱你时,原先烦孩子的我,见着胖嘟嘟的孩子就发痴。我很想很想有个孩子,很想跟你生个孩子。当我想你想孩子时,心底就会滋生一股柔情,直从脚尖涌入心脏。我用这股柔情把孩子取名为“湄”。“湄”是亦水亦岸亦草的地方,是那一注横如眼波的水上,浅浅青青、温温柔柔如一黛眉毛的地方。这个字太秀丽,我简直不敢轻易出口。我们心心相印,你回来,给我捎来了一件工艺品——用我喜欢的石子拼成的一家三口,中间歪头、调皮的小女孩,你叫她“湄”。你还买来一幅着名的摄影画,画面是一个五六岁的漂亮女孩,正低头穿着她妈妈的大皮鞋,试着走路。你说,那是我们成长中的“湄”。你把这幅画喜滋滋地贴在我床前,想你想孩子时,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它。我很喜欢这幅画,一直保留着,几次搬家,我们的女儿——湄都上了高中,至今仍挂在厅堂醒目的位置上。
王希,你还记得好友贝青么?为了我,他没能考上大学。当年,我一直把他当知心大哥,有烦恼、忧愁一股脑儿地倾泻给他。神经衰弱期间,我甚至把你写给我的情书,时不时地拿给他看,让他帮忙分析你对我的情感。谁曾想,他会痴迷疯狂地爱上我,跪在我面前流泪,还写信给你,求你把我让给他。我无法猜测当初你的心境。当贝青把我和他有意被他表姐拍下的合影照,及我写给他的几封信,交给我妈百般恳求时,连我妈都不相信我和贝青的清白。而你家人更是添油加醋,百般嘲讽,说你是睡在床上“醒眼屙尿”。面对这些,你毅然跟家人解释:“莲子不是那种人,我相信她!”尽管事过多年,你就是经过贝青的旧住所,仍忍不住会吃醋,但当时我是多么感激你的信任啊,我为自己的幼稚行为后悔不已。
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欢快,如花蕾掩映着春天。我们一起在花下葬石子埋誓言,一起看夕阳采野果,一起到河里洗澡游泳,一起躺在竹床上看牛郎织女星……在爱情的镜子面前,谁能把自己的灵魂遮掩?还记得1987年腊月二十八,我们相约在母校——我的单位拟写春联吗?为了把家中景色、我们的希望、相思融入春联,我们嬉耍斟酌,不知不觉到了家家亮灯的时候。那天,天冷得出奇,又下着冻雨,你怕父母责怪,回了自家。而我一人在淫绵的雨中骑车走山路回娘家。那时我刚学骑车,歪歪跌跌,十来里路,黑咕隆咚,我又怕又伤心,淋雨推车一步步摸回家,一到家,就发烧生病。结果惹得全家过年不开心。
从此,担心你毕业分不回来、对你没好感的母亲愈发反感起来,数落你脸生负心骨,剑锋眉,肤色黄中带黑,跟着你定没好日子过,要我和你分手。你来我家,我妈拿粪勺追赶你,你不怕羞辱,前门出后门进,满脸歉意。见你如此,我心如磐石央求母亲。你走后,母亲骂我、打我,我不依,骑车偷跑出去,疯狂地奔向你,车速像心一样飞快。我孤立无援如一条涸辙之鲋,只等你的救助。万想不到,恰在路上遇到了来我家的你!我们把车一甩,真想在车水马龙的大路上尽情拥抱,但羞怯的我们只无比兴奋地对望着,一同笑出了泪水。
到你家,我们又遭到你父母的冷遇。你父母怕你耽于恋爱荒废学业,亦担心我的流言飞语、你的工作分配,故极力反对我们。可相爱恰似春江水,船犁桨划又如何!
还记得1988年正月初五你家的晚宴么?酒桌上,我向你哥敬酒,你哥不喝,傲然说道:“是我弟媳,我喝这杯酒;只是我弟同学,我不喝这杯酒!”我气得直跺脚,当场离席。那晚下着大雪,已至九点,我冒雪不辞而行,你悄悄跟上我。我们一路快活地迎着雪花,唱着你教的新歌《结伴同行》——“我们结伴同行,走一走人生之路;我们携手同游,渡一渡岁月的河”,走了十五六里路,到了我单位。你父亲吓坏了,第二天,天花花亮,踏着厚厚的雪寻到了学校。我们怕羞怕责骂,竟躲到房里不出声。你父亲把门敲得嘣嘣响,前后来回三次,低三下四询问留校的老师,我们则屏气噤声,任由你父亲着急叫唤。估摸他走了,从门缝里看看四周无人,我们才悄悄开门,只见雪地里纵横交错的,全是你父亲深深的脚印。
尔后,你舌战父母搬来的两桌说客——你的叔伯舅姨们!你用雄辩的口才和坚定的爱情说服了他们。迫于无奈,你父亲于这年暑假到我家定亲。而你哥却千方百计找我的茬,认为我是中师生配不上你,还跟贝青相好过,订婚第二天,便开了辆公车,得意洋洋地到我家悔婚。你哥是乡长,在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你被他气得心痛,为了我,不惜兄弟反目。去你家,你父母脸不是脸、嘴不是嘴地冷淡我,你奶奶甚至故意拿一把扫帚,我走到哪扫到哪地赶我。一个姑娘家哪受得了这般轻慢!我晕了,把你叫到一边,正色道:“沰,我们分手吧!”你一听“噔”地一下傻了,脸上淌着大滴大滴的泪,急傻了。你眼光笔直,眼神痴呆,连颈脖都僵直了!俨然初听中举的范进,又像林妹妹要回老家急疯了的宝玉。我吓愣了,拉着你的手,只一个劲儿望你。你母亲紧张地晃着你,连声唤你,你没反应,吓得只知道哭。你奶奶急得边哭边不停地拍腿呼嚷:“怎么得了噢!怎么得了噢!”全家上下一片慌乱。你父从外面赶回,见状唬了一跳。只听你母亲问你:“你晓得我是谁么?”你簌簌流泪傻痴痴答道:“不晓得……”你奶奶问你:“你认得我是谁么?”你摇摇头。你母亲又指着我问道:“你知道她是谁么?”你紧拽住我的手不放,“莲子,莫走,莫走!”你父亲失望至极詈骂起来:“不争气的畜生!为了一个女人成这样!”接着便“呼呼”扇了你两耳光,重重一脚把你从厅堂踢到另一侧门里。你爬起,定了定神,方清醒过来。“扑”地一下跪在你父亲跟前。我腿一软,情不自禁“咚”地一声跟着并排跪下……我想:不管千难万险,这辈子非你不嫁!非你不嫁!你母亲吓病了,卧床不起。
我回娘家,父母因为你家悔婚,在四邻八舍面前丢尽了脸面,越发决意反对我们。母亲哭闹、恶骂、撕扭、掐拧,撞我的头,咬我的手指、耳朵,咬得血淋漓,见我不松口,扯乏了抓累了,就用棍棒打,直打得我全身青肿不堪,疼得呼天抢地。第二天晚上,天清气爽,我想与其让双方父母伤心,不如一死了之。也许,只有死是爱的最后呈现。我跪着拜别了生养我的天地父母,毅然跳进村后的水库,结果被赶来的弟弟救了上来。看我水淋淋的狼狈样,急匆匆赶来,从没舍得打我的父亲第一次狠狠踹了我一脚。你知道后,火速赶来,我父母责备你,懦弱的你却不敢承认我是为你自杀。我气得甩东西赶你出门,你慌了,不停地求饶。不过从此,双方父母再也没敢执意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