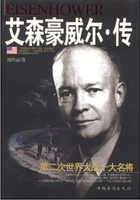当年九月,孙冶方、陈启礼等少数同学因暑假期间打工挣了些钱,被同学开玩笑地逼着买肉做中国菜吃。那天,趁暑假结束就要开学的机会,孙冶方的小屋里又挤满了江(苏)浙(江)同学,其中也有湖南同学左权、陈启礼等,大家嬉笑打闹,亲如一家。不料,这情景被从窗下走过的学生会干部王长熙看见。王长熙为了讨好王明,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王明,并添油加醋地形容他们是“江浙同乡会”。
王明立即放下《资本论》,去校长米夫那里汇报。
原来,不久前,对共产主义很感兴趣的蒋经国,也来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学校学习,中山大学几个江浙籍学生给他写了信,开玩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选你当会长,希望你这个会长以后经常接济一点钱。”因是半开玩笑的信,蒋经国看完并没在意,随便扔在抽屉里。没想到这封信被人发现,送到了王明手里。蒋介石的儿子要当江浙同乡会的会长,这还了得!
王明一九○四年四月九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一个贫苦小商人家里,贫困的童年生活,激发了王明有朝一日要出人头地的愿望。一九二四年,他怀揣着母亲零星积攒的七块大洋,走出皖西山区,进入武昌商科预科学习。刚满一年,他来到莫斯科,开始留学生涯。在校期间,王明除了对俄语和马列主义感兴趣,其余时间大都用在跟米夫套近乎上,为此,一九二六年九月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自上次把来自蒋经国手里的信件转交给米夫后,米夫就叫他多搜集一些证据,以便向“江浙同乡会”出手。身为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的米夫,为什么要打击江浙同学呢?原因是,不少江浙学生反对他当校长,认为他的校长职务是通过挑拨原校长和书记的关系得来的,很不厚道。米夫要拿政治问题的“铁证”,搞臭反对他的中国学生。
米夫接到王明的报告,决定立即由中山大学支部局成立调查组,展开对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调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调查结果认定:“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结果,十二名江浙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受莫须有罪名打击的同学,不甘王明以恶劣手段置他们于死地,义愤填膺地来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住处,申诉了这一冤案,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和张国焘,在广泛听取同学汇报后,派邓中夏和余飞到中山大学调查。
米夫、王明对调查人员制造障碍,不予合作。
瞿秋白不得不亲自到校,一一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联合审查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审理。审理结果是,摘去了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的同学的“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这件事平息后,为了避免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瞿秋白、张国焘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建议:米夫不宜再任校长,该职务应由鲍罗廷担任。
没想到瞿秋白、张国焘对米夫不满的议论传进了米夫的耳朵,从此以后,米夫越发加深了与中共代表团间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中山大学斗争的愈演愈烈,直到后来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九二九年,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对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在支部局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斗争,米夫要借此机会,整掉一批反对他们的人。他们给这些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并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总后台。
在一次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秦邦宪(博古)受米夫的指派,批评张国焘是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山大学的正常斗争开展。
一九二九年上学期结束时,中山大学所在地联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按照米夫的要求,在一次党员大会上猛烈抨击中共代表团和一些学生。中共代表团代表张国焘当时在场,他毫不妥协地回击了芬可夫斯基等人的指责,支持多数同学反抗米夫和王明。芬可夫斯基批评中共代表团的时候,与会的大多数同学以吹口哨、跺脚来表示抗议,闹得会场灰尘四起,混乱不堪,使得大会开不下去。
苏联“老大哥”芬可夫斯基哪受得了中国“小老弟”的嘲笑,当场拍了桌子,叫学生滚出去!
几个被冤的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冲上讲台,要把芬可夫斯基赶下台去。
张国焘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劝阻这些学生。在劝阻这些学生时,台下的何克全走上台来,帮助张国焘做劝解工作。何克全认为,既然代表中共代表团的张国焘要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肯定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他没有理由保持沉默。没想到,身材中等、俄语说得不够流利的何克全的这一行为,引起了秦邦宪的特别关注。
秦邦宪一九○七年生于江苏无锡,小时候在老家无锡上小学,十七岁在苏州省立第二技术学校毕业。一九二五年到上海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作为第二批中共留学生赴莫斯科留学。今天在米夫的安排下,秦邦宪坐在了主席台上。他的座位正好挨着张国焘。骚动平息后,趁芬可夫斯基继续讲话的时候,秦邦宪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别看何克全平时不说话,关键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
张国焘问:“是吗?”在武汉,张国焘从报纸上对何克全有了一些了解,来到莫斯科后,终于认识了这位来自萍乡的老乡。他乡遇故人,便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在一起回忆家乡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但是一谈到“江浙同乡会”的事情,何克全就三缄其口,说自己刚到莫斯科,情况不熟。为此张国焘对何克全不站在中共代表团一边感到失望。可万没想到,这个看似中立的何克全,今天居然冲上讲台,来劝阻冲击芬可夫斯基的同学。这种行为,看似听从张国焘的指令,实则在帮米夫的忙。因此,张国焘对何克全的行为有些不悦。
秦邦宪说:“克全同学在武昌中山大学当团支部书记时,总是做出些叫进步学生由衷赞叹的事。那次叛徒供出在校党团员的名单,要不是他事先有准备,不知多少同志要被抓走。”
张国焘说:“不这样,党组织怎么会让他来莫斯科深造呢?”
秦邦宪说:“同样来莫斯科,何克全却跟有些江浙学生不一样,非常珍惜学习机会,一有时间,就找我和米夫请教理论上的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简直称得上是孜孜以求、废寝忘食地钻研。”
张国焘知道,秦邦宪是想通过称赞何克全,以使自己对他产生好感。张国焘是党中央要员,也是中共一大会议召开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他的一句话,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张国焘说:“光在米夫那里找理论恐怕不行吧?中国不是苏联,没有那么多平原草场,更多的是高山大岭,山路怎么走?大岭怎么绕?山头怎么登?能从米夫嘴巴里找到吗?”
秦邦宪问:“你的意思是,克全和我们还得多向中共代表团的领导请教?”
张国焘说:“我可没这么说,就是说了,你们也不会听。一个‘江浙同乡会’,米夫说是反党组织,王明和你不也跟着说是反党组织吗?”
听张国焘这么一说,秦邦宪的脸热了。
张国焘因为秦邦宪在中山大学斗争中偏向米夫一边,很是不满,他想给他一点颜色看,让他领教一下他的厉害。
尽管局面尴尬,年轻的秦邦宪不去计较,仍旧谦卑地说:“国焘同志,克全同志表现这么出众,我想介绍他加入党的组织,您看他够不够条件?”
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张国焘今天不想让秦邦宪下不了台,毕竟党的事业需要年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年轻人,秦邦宪毕竟在帮助自己的同乡何克全,于是说:“既然对何克全感兴趣,你就当他的介绍人吧。”
秦邦宪很是乐意地说:“国焘同志,从今开始,我将根据您的指示,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他早日加入先锋队组织,眼下我党就缺少何克全这样的笔杆子啊。”
在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上,瞿秋白、邓中夏始终坚持原则,跟米夫、王明的斗争依旧毫不妥协地进行着。一九三○年春,米夫通过共产国际这个总后台,终于击垮了瞿秋白。那天,米夫以胜利者的姿态,把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叫到他办公室,宣读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完全站在米夫、王明小宗派的立场上。这样,瞿秋白被迫撤销了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职务,让后来转向米夫的张国焘接替。
瞿秋白、邓中夏、余飞于一九三○年八月回国。
瞿秋白回国之前,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代表团与共产国际关系,曾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做米夫的工作。但在既成事实面前,迫于“老子党”的压力,周恩来也无力回天。
这场历时三年之久的斗争,使多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卷入其中,为接下来的党内斗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一九三○年夏天,何克全在中山大学毕业,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即将回国的学生赴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进行军事训练。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也就是蒋经国曾经就读的大学。
训练结束时,一九二九年三月跟王明一起回国的秦邦宪给中山大学米夫写信,推荐何克全进莫斯科少共国际学校,接受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培训。
米夫对何克全作了安排。
进入少共国际学校不到三个月,何克全肺病发作,大口吐血,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九、意恐迟归
日子就像水车上的龙骨,转过一轮又一轮。
三伏天里,每当孙氏和金氏挽着衣袖和裤筒,双手作揖一样通过水车叶片把水挽进稻田里时,孙氏经常抬起头,往大路上望去。她希望看见何克全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接过她手中的车拐,叫她到一边歇息去。
过日子,女人不能没有男人。
男人是堵墙,可以为女人遮风挡雨。男人是棵树,可以让女人扶着站立。男人是张床,可以让累了的女人躺下来歇息。读书人说,男人的男字是由田字和力字组成。在孙氏看来,造字人真是琢磨透了女人的心,田里的事不能缺少男人啊。
日子就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不断地穿过三百六十五条经线,将人生的纬线无情地织进了它的中间去。每当听到秋叶飘落地面发出声响的时候,孙氏的脑海里总会出现何克全的身影,而且情不自禁问:“你在哪里?”“你可加衣服了?”好几回,因产生幻觉,深更半夜的孙氏竟要去给何克全送棉衣,好在金氏时时关注,才没让她走出家门。
“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
每当大女儿何明清、小女儿何淑英问孙氏时,她只能找理由,哄她们说:“爸爸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给爷爷、奶奶赚钱去了。”
何明清、何淑英问:“爸爸赚了那么久的钱,买了那么久的东西,怎么还不回来?”
她说:“爸爸赚的钱太多太多了,一个人背不动,他在外面等你们长大,等着你们长大后去帮他背回家来呢。”
夜深人静,哄得两个女儿不哭不闹之后,孙氏形只影单地躺下,时时抱着枕头嘤嘤地哭泣。她不怪丈夫不给她体贴,不怪丈夫不回家看望他的女儿,不怪丈夫不给家里寄钱寄物,因她知道,丈夫在外不是赚钱,而是造反,造那些靠收别人租子的人的反,造那些欺压穷苦人的人的反。造反的人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好多人连命都赔了进去。不久前,老关街上杀过一次人。那些被杀的人,脑袋被按在砧板上,一刀一颗,装满两谷箩。后来由保安团挑着去萍乡交差。保安团的人说:“这些被杀的人全是‘黑杀党’。他们经常夜里出山,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孙氏听说的“黑杀党”,就是被国民党赶上山去的共产党和红军,他们经常趁夜深人静时下山,专杀土豪劣绅,把没收的钱粮分给穷人,少部分带走自己用。有人告诉她,何克全就是“黑杀党”的头头。她知道,一个靠晚上出来生活的人,不可能回家看她。她不希望丈夫冒死回来,只希望丈夫给她写封信,报个平安就行。可丈夫一九二六年走后,杳无音信,就像石头沉进了大海。
一九三○年的冬夜,从来不进儿媳卧房的公公何秋美,拖着一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双腿,走进儿媳妇的卧房。
何秋美对孙氏说:“克全家的,你出门吧,何家亏待你了。”
“出门”一词在赣西,是改嫁的意思。
孙氏知道,“出门”的话要从公公嘴里说出来,那是他对何克全已经完全绝望的表示。公公是个要面子的人,儿子如果还有一线希望回来,他是不会让儿媳妇出门的。
金氏也跟进来,劝说道:“儿媳啊,你还年轻,既贤惠,又勤快,还可以找个好人家,过上舒坦的日子。你走吧,我们不怪罪你。清清、英英你想带走就带走,不想带走就留下。你到何家七年了,我跟你爸不能让你跟着我们受一辈子的苦啊。”
面对把自己当女儿看待的公公、婆婆,孙氏眼泪像涌泉般流下。她问公公婆婆说:“克全真的回不来了吗?”
何秋美爱恨交加地说:“肯定死了,回不来了!”
孙氏说:“爸,我不相信,我们乡下人对失去音讯的人,不是常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吗?没听到克全不在人世了,我们就不能说克全回不来了。”
何秋美说:“傻孩子,别管他回不回来。你守了他七年,他就是回得来,你出了何家门,我谅他也不敢在你面前说一句责怪的话!”
金氏说:“是啊,孩子,一个不顾家的男人,就该让他一生打单身去!”
孙氏和何克全,尽管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孙氏从和何克全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感觉何克全还是承认她这个妻子的。新婚之夜,何克全剪开她的包脚带,让她把双脚解放出来,她就知道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心里是疼爱女人的,她打心眼里感激他。七年前,何克全把她塞进口袋的银元重新还到她的手里,她就知道,在何克全这个身无分文的男人的眼里,是有她这个女人家的。男人,其实不要说很多话,不要给很多的笑,只要从他的一两个举止中,就知道他对人的好恶。孙氏坚信,何克全一定会回来,即使不回来,有何克全给她的上述的几个举动,她就没有理由离开何家。为此,她对公公婆婆说:“爸妈,我该给菩萨敬香了。有菩萨保佑,克全会回来的。”
何秋美再一次劝导:“孩子,那家伙不值得你守,你出门吧。”
孙氏不再搭理何秋美,独自走出卧室,去厅堂的香案上取香,当香取出后,她将桐油灯盏点燃,将香倒着伸向桐油灯火。慢慢点燃后,她双手握着,对着山墙上挂着的何克全祖父祖母的画像,作了三个揖,在心中祈祷祖父祖母的在天之灵保佑何克全平安。
闻着厅堂慢慢散发出的檀香味,望着如此倔犟的儿媳,金氏失声哭了。
何秋美也被感动得眼泪直流。良久,他长叹一声骂道:“何克全,你这家伙作什么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