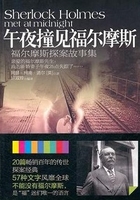艾滋病基金会志愿者培训课程的第一天,我们被教导不要将被感染者称为病人,而是客户。我们懂得了无论我们在他们的生活与护理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无论我们成为他们多么亲近的朋友,只要有家属介入并与我们意见相左,我们都要尊重他们。
我们明确了漂白剂和乳胶手套的重要性,它们在后来每天处理各种日常琐事的过程中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令人困惑的是,我们究竟是在保护那些免疫系统已受损的客户免受有害细菌的侵袭,还是说我们在确保自身健康而不触碰到任何他们碰过的东西。到处都是风声鹤唳,但只是源于对于这种疾病知识的匮乏。我们讨论该如何帮助那些感染者,没有人——尤其是医学界——知道这种病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
我感觉似乎其余所有的新志愿者们都是男同性恋。当问起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自告奋勇地加入这个人员寥寥无几,在凶险的危机前挺身而出的群体时,他们都会谈起一个朋友、爱人、亲人、熟人,或其他人,这些人或已被确诊或因某种疾病和感染而死亡,这种感染后来被归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又或许,他们本身已被感染了,只是想要时刻保持在新消息的最前线。那时候,1983年的年中,致病原因正在研究中,但还没有发布任何官方声明。
我在男同性恋群体中感到十分自在;事实上,那是我最初的舒适地带。我的儿子,加里,早就察觉到了。这些年,他一直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爱人们,以及旧金山同性恋男子合唱团1。我每年假期去探望期间,他通常都会被邀请到朋友们的家里共享圣诞晚餐,我一同被邀请也完全没问题。我喜欢和他、他的朋友们以及任何来到我生活中的同性恋们在一起。他们都张开双臂欢迎我,我也很开心地回应他们。无论我身处何方,那种感觉爱屋及乌扩展到所有同性恋人群,尤其是男性。于是当我和我的新朋友一起坐在培训课堂上时,我对于自己前来加入的决定没有一丝疑虑。在最初的几天,尽管还有其他的女性志愿者负责其他的事务,我相信自己是这个完全自愿的军团里唯一的一位母亲。
每个参加培训的人都收到了一只小泰迪熊作为感谢的礼物和纪念品。没有刻意偷看,每个人都从一个大的纸质购物袋中掏出自己的熊,而我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得到了唯一的一只白色的熊——重要的是那只白色的正是我想要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因缘。由于在教授安全性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泰迪熊成为了艾滋病教育项目的象征。
我们做了一些角色扮演的练习,在心理和情绪上准备好处理一切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场的人之前都素不相识,尽管我有些忧心忡忡,那种担忧很快就被驱散了,我意识到我们都在一起,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要开拓进取。在一个练习中,我们两人一组,被要求互相对视三分钟不讲话。我和我的搭档大卫的情感变得异常强烈,那三分钟似乎成为了永恒。我,强忍住眼泪,无法再控制自己。大卫感受到了那势不可挡的情感,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双双泪流满面。那是一种意义非常深远的心灵契合,一开始我们曾经质疑,但在结束时已默默懂得了。当不久之后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照顾我们遇到的人们时,学会不依靠对话而感知到别人的痛苦或情感成为一笔重要而有价值的财富。他们很可能被一台呼吸机所束缚,也可能患有痴呆症。有时,他们也许太虚弱以至于无法交流,但会明白有一个默默不语的看望者只是简单地陪他们在一起的重要性,这令他们重拾信心。
我们轮流表演着医院里或是家访的一幕幕,在那里志愿者和病人们以前从未见过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即兴的对话很难轻而易举地开展。在摸索中我唯一的慰藉是那里的每个人都感受着同样的不安。我们尽了全力,没人指责我们不够灵活应变,也没人批评我们糟糕的演技。事实上,在现实生活的场景中运用这些技巧要更加容易一些。那些话都是很自然的——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但我相信听到的人们会感知到我们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安慰他们。
如果我们花时间出去进行社交活动了:诸如共进晚餐、看电影或参加派对,有些志愿者会感到内疚。我们是健康的,应当去照顾病人和奄奄一息的人。特德作为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周组织志愿者会议。他打消了我们的疑虑,我们完全不必为耽于日常的活动而感到内疚。他深刻的话语令我永生难忘。
“如果你一心多用心力交瘁,对谁都没有好处。”
特德是一位治疗师。他能说到点子上。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每周的志愿者会议有8到10个人坐在一座银行大楼内一间捐赠的空房间里。我们互相交换着从其他那些突然陷入困境中的人们那里所了解的有限信息。我们开通了一部艾滋病热线电话,用于回复那些提出私密问题并希望得到保密答案的呼叫者。在这个由一人控制的电话银行中,值班者的一项任务是将所有来电登录到一本有日期的日志上,简单描述一下来电内容。这帮助我们收集到关于这种疾病侵袭人体的许多不同方面的资料。我对于志愿在热线值班感到很惶惑,主要是害怕不能够给那些惊慌失措打来电话的人们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这让我感到自己准备不足,无法处理问题。
一个年轻的男同性恋,比我勇敢得多,讲述了一个难忘的故事。他在一天晚上接到了一个发疯似的办公室主管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刚刚发现有一个员工居然是个同性恋!我们要怎么处理办公室里所有的文件呢?”
那位志愿者笑着对我们说:“我差点告诉她说把它们都烧了吧。”
1983
***
1旧金山同性恋男子合唱团: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男子合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