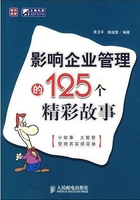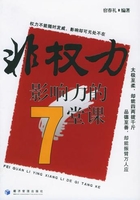随着我们小圈子里的六个人的知识逐渐增长,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和处理一些关于生和死、今生和来世的秘密。我们都是在善良诚实、自尊自爱的父母抚养下,在一个或另一个教派的影响下长大的。在匹兹堡长老派牧师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都加入了她丈夫的教区。(1912年7月16日,当我在奥特纳加荒野的别墅中读到这段时,我刚刚收到八十岁的麦克米伦夫人从伦敦寄来的短笺。她的两个女儿上周都在伦敦嫁给了大学教授,一位会留在英国,另一位已经收到了来自波士顿的聘书,两位都是卓越的男士。这样,我们两个说英语的民族结合起来。)麦克米伦先生是个善良而严厉的加尔文教的守旧派,他迷人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轻人的领袖。我们都喜欢待在她家里,那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自在,这导致我们偶尔也会去参加教会。
米勒听到了一次很有说服力的关于宿命论的布道,于是把这个宗教话题带给我们讨论。米勒先生的教徒都是坚定的循道宗信徒,而汤姆对教条则一无所知。宿命论的教义,包括婴儿诅咒理论——一些人生来光荣,其他人则相反,使他感到震惊。令我惊讶的是,有一次在麦克米伦先生布道结束后,谈到这个问题时,汤姆在结束时脱口而出:
“麦克米伦先生,如果你说的是正确的,你的上帝一定是个十足的魔鬼。”然后就留下惊讶万分的牧师离开了。
这成为我们好几周周日下午会议的话题,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汤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将不再受到麦克米伦夫人的欢迎了吗?我们也许可以不去接触牧师,但是我们没有人愿意放弃去他家聚会的机会,这点十分清楚。
卡莱尔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应该跟随他的解决方法:“如果这是不可信的,就以上帝的名义让它不可信吧。”只有真相才能使我们自在,而我们应该追寻所有的真相。
当然,一旦提到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一条条的教义,被我们看作是尚未开化的人们的错误思想,而加以否决和摈弃了。我忘记了是谁先提出的第二条公理。我们曾仔细研究过:“一位宽宏大量的神,是人类最高贵的作品”。我们认为,可以证明的是,文明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创造出自己的神,随着人类的提升,他们对未知的概念也越来越清晰。之后,我们都变得不太相信神学,但是我肯定我们都更加虔诚。我们度过了这次危机,很开心我们没有被麦克米伦夫人赶出聚会。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决定支持米勒的陈述,即使其中包含了放逐和更糟糕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对神学不怎么尊重,但对于宗教却更加虔诚了。
我们圈子里第一位去世的是约翰·菲普斯,他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这对我们大家都是沉重的打击,但我记得我这么安慰自己:“约翰他只是回英国去了,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不久后我们都会跟随他的脚步回去,永远在一起。”当时我没有任何怀疑。在我心中,这不是我给自己的希望,而是一个事实。那些在痛苦之中的人,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后会变得开心。我们所有人都该听从柏拉图的意见,永远不要放弃对持续的希望的追求,“让自己充满快乐,因为希望是高贵的,回报是丰富的。”没错,能够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和自己最亲的人永远在一起,这是一个奇迹,而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和亲爱的人共度此生,更加是一个奇迹。对于有限的生命来说,这两者都很难理解。那就让我们用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正如柏拉图说的,“让自己快乐”,绝不要忘记,我们在世都有一定的责任,天堂就在我们心中。他还说过,那些声称没有来世的人和那些声称有来世的人一样愚蠢,因为没有人知道答案,尽管可能所有人都希望有来世。同时,我们的座右铭是“家是我们的天堂”,而不是“天堂是我们的家”。
在那几年,我们家的财产一直在稳步提升。我的工资也从每月35美元涨到了40美元,是斯科特先生主动为我加的工资。每月给员工发工资也是我的职责之一,我们用的是银行支票,而我总是领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艺术品。
在家庭会议上,我们决定冒险买下一块地和上面的两所小房子。一所房子我们自己住,另外一所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原来一直是我的霍根姨父和姨妈住的,但那时他们已经搬去了别的地方。全靠艾特肯姨妈的帮忙,我们才能一直住在织布店楼上的小房子里。现在轮到我们请她搬回她的老房子来住了。在我们买下那所四个房间的房子后不久,霍根姨父去世了,我们又要搬去阿尔图纳,于是便同样的,把霍根姨妈接回她的老房子住。
我们付了一百美元买下这房产,而我记得总价是七百美元。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并且尽可能多存下些钱付本金。不久后,我们就还清了债务,成为了产权人。然而在未还清款之前,我们家经历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我父亲在1855年10月2日去世了。但是,对于家里剩下的三个成员来说,还得承担生活的重任。悲伤和责任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工作,必须存钱还清父亲的医药费,而当时我们没有多少存款。
此时,在我早期美国生活中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史威登堡教会的首要成员是大卫·麦坎德利斯,他注意过我的父母,但是除了周日在教堂时说过几句话,我不记得他们曾经有过密切的联系。然而,他和艾特肯姨妈很熟,因此他让她带来口信,如果我们在这个悲伤的时刻需要任何金钱的援助,他很乐意提供。他曾听说过我母亲很多英雄事迹,而这些就足够了。
当一个人不再需要帮助,或是处在一个可以回报帮助的地位时,往往会收到很多人好心提供的帮助。所以,能记录下这样一件纯粹的非功利性的善举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当时,一个贫穷的苏格兰妇女刚刚失去了丈夫,大儿子才刚开始工作,小儿子才刚十几岁。这些不幸打动了这个男人,他慷慨的姿态给了我们一丝慰藉,尽管我的母亲拒绝了他的好意,但是不用说,麦坎德利斯先生在我们心中占据了一个神圣的地位。我坚信,如果一个人在人生的关键时期需要必要的帮助,通常他们都能得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他们不但愿意,而且迫切地向那些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相应的,那些乐于帮助他人的人,自己也不会担心得不到他人的帮助。
父亲过世后,我要处理比以前更多的事务。母亲继续做鞋,汤姆还是继续上公立学校,我继续跟着斯科特先生在铁路公司工作。就在这时,幸运之神来敲门了,斯科特先生问我是否有500美元,如果有,他希望帮我做一项投资。说我的资产有500美分还差不多,我当时连50美元都没有,但是我不想错过这个和我的上司以及偶像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于是我大胆地说,我认为我能凑到这笔钱。于是他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堡站的代理人——雷诺兹先生那里买到十股亚当斯快车的股票。晚上,我把这件事汇报给母亲,她很快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她什么时候失败过呢?我们当时刚刚在房产上花了500美元,她认为这可以作为一笔贷款的抵押。
第二天早晨,我母亲坐着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她回来了,带着她从她兄弟那里借来的钱。他是那个小镇的治安法官,十分有名望,手头有很多农民要投资的钱。把房子抵押后,母亲带回了500美元。我把钱交给了斯科特先生,他很快就帮我把期待的十股股票拿回来了。出乎意料的是,还需要100美元的保证金,但是斯科特先生好心地说,我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付,这样就容易多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以前那些美好的日子里,每月红利比现在要多。而亚当斯快车正是每月分红。一天早晨,我桌子上躺着一个白色信封,上面是大大的手写的“致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先生”这个词让还是个孩子的我十分开心,在信封一角可以看见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我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张纽约黄金交易银行的十美元的支票。我永远都记得这张支票和那个亲笔签名的“出纳员J.C.巴布科克”。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收入——我没有付出汗水和劳动就得到的收入。“找到了!”我大喊道,“我发现了下金蛋的鸡。”
我们小圈子的惯例是,星期天下午在小树林里聚会。我们在树林里我们最喜爱的树下坐下后,我把我带着的第一张支票展示给他们看。我的伙伴们反应很强烈,没有人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我们决定攒钱,等待下一个投资机会。我们一起分享,然后几年后平分红利,就像合伙人一样一起赚钱。
到那时为止,我的社交圈子还没有扩大很多。我们的货运代理人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斯夫人十分友好,曾在某些场合邀请我去她在匹兹堡的房子做客。她常常提起我第一次按响第三街上那所房子的门铃,为斯科特先生传个口信的情景。她请我进来,我害羞地拒绝了,她靠着哄骗,才让我克服了羞涩。
这些年来,她从来没有成功地邀请到我去她们家用餐。我一直很害怕去其他人家里做客,直到后来才有所改善。但是斯科特先生偶尔会坚持要我去他的旅馆,和他一起吃饭。而那些场合对我来说很重要。没有记错的话,除了在阿尔图纳时,我去过罗姆贝特先生家外,弗朗西斯卡斯先生家算是我踏进的第一所很不错的房子。在我眼里,任何主要街道上的房子都十分时髦,只要它们有一个大厅。
我从来没有在陌生的房子里过夜。直到宾夕法尼亚铁路的首席法律顾问、格林斯堡的斯托克斯先生邀请我去他的乡间别墅共度周末。像斯托克斯先生这样睿智、有教养的人会对我产生兴趣,邀请我去他家,这可是件怪事。其实,能收到这个邀请的原因是我在《匹兹堡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通讯。早在我十几岁时,我就算是新闻界的一个三流作家。成为一名编辑曾经是我的目标之一。贺瑞斯·格里利和《论坛报》是我理想中的成功典范。奇怪的是,当有一天我本可以买下《论坛报》时,昔日的珍珠失去了光泽。当日后我们有机会得到空中楼阁时,它也就失去了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整个城市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态度,这篇文章是匿名投稿的。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它被刊登在《匹兹堡日报》专栏里一个十分显着的位置,编辑是罗伯特·M.瑞德。作为操作员,我收到了一份斯托克斯先生发给斯科特先生的电报,请他询问瑞德先生,谁是这篇通讯的作者。我知道瑞德先生不知道作者是谁,所以他不会说。但同时,我又害怕如果斯科特先生去找他,他会把手稿交给他。这样斯科特先生必定能一眼认出我的笔迹。
因此,我向斯科特先生坦白,我就是作者。他看上去有点怀疑,他说他早上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并还在猜测作者是谁。他怀疑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眼睛。钢笔逐渐成为我的武器。随后,斯托克斯先生就邀请我去与他共度周末,这次做客是我一生的亮点之一。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斯托克斯先生的家富丽堂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图书馆里的大理石壁炉架使其他东西都黯然失色。在架子中间的大理石上刻着一本摊开的书,上面刻着: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不愿思考的人是顽固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隶!
这些高尚的语句震撼了我。我对自己说,“某一天,某一天我也会有自己的图书馆(这是个前瞻),而这些话语会使壁炉架更雅致,就像这里一样。”如今,在纽约和斯基沃,这个想法都实现了。
几年后,我在他家度过的另一个周日也值得一提。当时我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匹兹堡分部的主管。南方各州宣布独立,我当时充满了战斗的热情。斯托克斯先生是民主党的领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统一,他表达了他的看法,这导致我失去自制地大喊道:
“斯托克斯先生,我们在不到六个礼拜内就会绞死你们这种人”。
写到这里,我又仿佛听见了他的笑声,他对着隔壁房间里的妻子喊道:
“南希,南希,听听这个年轻的苏格兰小鬼的话。他说他们在不到六个礼拜内就会绞死我这种人。”
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一些怪事。不久之后,同一个斯托克斯先生在华盛顿请我帮助他申请志愿部队的陆军少校的职位,我那时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个委任,从此成为斯托克斯陆军少校。这样,那个曾经质疑过北方是否有权力靠武力统一的男人,为了高尚的目标,也拿起了手中的武器。人们开始争论和制定理论来修改宪法权利。当国旗被烧毁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一瞬间,所有东西都燃烧起来,包括宪法。祖国统一和昔日的荣耀!这才是人们所关心的,但已经足够了。宪法的目的是确保只有一面旗帜,正如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允许有两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