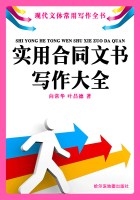沙场秋点兵。
燕山深处,铁甲轰鸣,烟尘滚滚。坦克第二训练学校教练团正在燕山深处组织越南、坦桑尼亚、巴基斯坦等外军留学人员进行实车实弹战术合成演练。
十几辆坦克挟风滚雷般驶过去,外军驾驶员娴熟地拉动操纵杆,顺利地通过弹坑、断崖、壕沟、秃岭、车辙桥、弯道路等障碍路段,向着预定地点突击。
穿过障碍路段的十几辆坦克,听见进攻的命令,快速形成三角作战队形,对着左前方移动的几个移动目标万炮齐发。
轰,轰,轰——三分之二的目标被摧毁。
节骨眼上,108号坦克在短暂停顿中没停住,担任一炮手的外军留学生连忙射击,几发曳光弹,拖着一团火光,朝快速移动的目标射击。
五发炮弹只中了一个目标。
坐在外军留学生中间的年轻教官阎铁民冲着远处生气地吼道:
“笨蛋,有这么停车的吗?”其他几十名等待考核的外军留学生有点害怕地望这个严厉的黑脸教官。
一辆越野吉普驶进训练场。车门打开后,从车上跳下来一个花蝴蝶一样的姑娘。姑娘眉清目秀,鸭蛋脸,柳叶眉,一双好看的眼睛扑闪着睿智的光泽,秀挺的高鼻梁微微翘起,显得机灵而调皮。姑娘走过来,为硝烟弥漫的训练场带来一道靓丽的风景。
身穿军装的青春男儿一齐将焦渴的目光投过去。
姑娘似乎没有看懂大家目光里的含义,打开120照相机,越过警戒线,对着行进的坦克不停地照相。
正在气头上的阎铁民看见等待考核的外军留学生和教练团的士兵,像呆头鹅一样傻乎乎盯着照相的姑娘看,厉声道:“坐好!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一个来自拉丁美洲的外军留学生听见呵斥,吐了吐舌头,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姑娘听见教官的厉声呵斥,回眸一看,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
阎铁民见了,心里窝着火,走过去,大声呵斥道:“哎,干什么的?
退回去,退到警戒线外面去,没看见正在组织实车实弹射击吗?”
姑娘仿佛没有听见,继续照她的相。
“哎,说你呢,没听见吗?哪个单位的?”
“我有名字,不叫‘哎’!”姑娘继续给行进的坦克拍照。
“警卫班——”阎铁民怒吼道,“把她给我拖出去!”
负责保障的警卫连走出几名人高马大的战士,就要将摄影的女记者架走。
正站在指挥塔高处摄影的教练团政治处宣传干事见状,惊叫一声连忙跑下指挥塔,向年轻的教官解释道:“阎教官,她是报社记者舒蕾同志,专门来报道我们坦克二校培养外军留学生的经验。”
因为外军留学生在实弹射击考核中没有打出好成绩,心里窝火的阎铁民没好气地说:“你只管自己照相,女记者的安全出了问题谁负责?”宣传干事跑过去,对着女记者劝说了一会儿,美丽的女记者回头望了阎铁民一眼,继续坚持在原地拍了几张照片,才退回到警戒线外。
舒蕾来到坐成一排排的外国留学生中间进行采访,请他们谈在军校学习的收获和体会。
采访中,那些外军留学生谈的最多的还是射击教官阎铁民,说他军事技术精湛,理论水平高超,待人热情。在外军学兵喋喋不休争先恐后的回答中,阎铁民俨然成了他们热爱的师长,崇拜的偶像,当代中国军人的杰出代表。
一个军人,一个普通的教官如何能成为外军学员崇拜的偶像?他的身上有什么魅力,成了舒蕾要揭开的谜底。
一辆教练坦克从射击场开回来。
4个外军坦克乘员土贼一样从车里钻出来,舒蕾看见刚才训斥她超越警戒线的年轻军官,亲切地喊:“阎教官,阎教官……”
教官黑着脸,训斥钻出驾驶室的学兵姆卡帕:“姆卡帕,你是怎么驾驶的?坦克短停对射击的重要性不知道?”
“我离合没踩好……”黑如煤炭的姆卡帕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
阎铁民又回过头斥责担任一炮手的巴基斯坦留学生穆亚拉夫:
“穆亚拉夫,你是怎么掌握射击要领的,不是告诉过你,要等坦克停稳的瞬间击发吗?你急着抢孝帽去?”巴基斯坦留学生用生硬的中国话不解地问:“教官,什么是抢孝帽?”阎铁民感到自己失言了,随意支吾道:“就是吃东西!”正在学习汉语的穆亚拉夫不停地小声嘟囔道:“抢孝帽,抢孝帽……”阎铁民哭笑不得地批评老挝学员:“你身为车长,是怎么指挥的?考这样的成绩你不感到羞愧吗?”老挝学员两手一摊,耸耸肩,做了一个鬼脸。
“你在中国坦克第二训练学校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舒蕾拉住越南留学生阮籍学问。
“我有一个好教官,阎教官教会我如何组织坦克三大专业的基础训练,教会我坦克师团在现代战争中超越纵深作战的战术原则。我回到越南,一定按照在中国学到的军事技术,组建属于越南人民的坦克部队!”
“你在中国学习军事,最崇拜的人是谁?”
“阎铁民!不仅是我一个人崇拜,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外国留学生都崇拜他!”“阎铁民是中国最棒的军人!”有个拉丁美洲学员翘起大拇指说。
“对!阎铁民是最棒的!”有个非洲学员随声附和道。
舒蕾仔细打量起这个凶巴巴的黑脸军人。他瘦削挺拔,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个头有1.80米,最多26岁,线条分明的黑脸上,眉毛又黑又长,一双冷峻的眼睛,闪烁着军人特有的坚毅和刚强。这么年轻的军人,竟然让外军留学生如此着迷,这里面究竟有什么蹊跷?
“阎铁民同志,我是创创报记者舒蕾,我想对你个人进行一个专访。”舒蕾大方地走过去伸出手自我介绍道。
“你没看我正在组织留学生研究射击难题吗?”阎铁民回头冷漠地看了一眼这个美丽的姑娘。
舒蕾白皙的脸蛋上,飞起两团红晕,伸出的手尴尬地僵在那里。
“停不稳,就打不准,射击中的驾驶,短暂停顿很重要,拉操纵杆、踩离合一定要快、稳、准……”阎铁民耐心地纠正外军学员的合成战术动作。
几个外军留学生头点得像鸡啄米。
“如果你现在忙,等训练完毕,我去采访你可以吗?”碰了一鼻子灰的舒蕾并没有气馁,她又一次向这个黑脸大汉发出邀请。
“外国留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回国,战术训练课目还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我哪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阎铁民冷冰冰地说。
“等你有时间,我到坦克二校去采访?”
“我们学校是军事禁区,保密单位,记者不能随便进来采访!”阎铁民感到这个女记者像缠藤的菟丝草一样难缠,想三言两语将她打发走。
“我是创创报记者,有权利在任何军事保密单位进行采访!”女记者固执地说。
“那你去找军训处吧!”阎铁民话没说完,跑过去,一个漂亮的三步蹬车,钻进坦克炮塔里,满载着3名外军留学生的坦克挟风滚雷般向靶场驶去。
舒蕾隐隐感到阎铁民的事迹材料一定是个“大鱼”,记者的敏感性告诉她,这个黑脸教官的事迹绝对不是大路货,有新、鲜、活三个特点,如果因为自己受了委屈而不去采访,一定是个重大损失。倔强的唐山姑娘,望着坦克开动卷起的烟尘,用银白的牙齿咬着醉人的下唇,心想,你现在高高在上,对我不理不睬,有朝一日,你一定会来向我道歉。
我要采访的对象,没有采访不成的!
午饭的军号响过之后,官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洪亮的口号走向饭堂。
饭前一支歌。
上百名身穿绿色军装的外军留学生整齐地站在饭堂门口。冰冷如铁的阎铁民做了指挥的手势,队伍“唰”地跨立。“向前,向前,向前——预备——唱!”随着年轻军官强有力的指挥,来自亚非拉三大洲的外军留学生以排山倒海之势,用生硬的汉语唱道:“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猪肉白菜炖粉条端出来。
已经习惯军旅抢饭生活的外军留学生端着饭盆一拥而上,不顾阎铁民的呵斥,抢起行军锅里的大烩菜来。巴基斯坦留学生穆亚拉夫高举着饭盆喊道:“我要抢孝帽,我要抢孝帽……”
饭堂里的中国坦克兵听见他的话,“轰”地一声全笑起来。
一个吃了一大口粉条的坦克驾驶员,听到穆亚拉夫的话乐了,“噗”地将粉条喷了出来。一个教官笑得从椅子上仰跌到地。一个正吃馒头的炮手笑得噎住了,瞪眼哽脖子咽不下去,连忙端起碗喝了口汤,一个车长哈哈笑出了眼泪。
穆亚拉夫看见大家哄堂大笑,瞪着眼睛,用生硬的汉语诧异地问:
“你们笑什么?我说错了吗?”阎铁民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大了,笑着摇头过去,帮着穆亚拉夫打了一盆猪肉白菜炖粉条,抓了两个雪白的馒头递给他说:“穆亚拉夫,以后这样的话不能在饭堂里说。”
“教官,抢孝帽是吃东西,不在饭堂里说,在哪里说?难道要去W畅C说吗?”穆亚拉夫一本正经地问。阎铁民觉得由于自己的随意,伤害了外国留学生,道歉道:“穆亚拉夫,对不起,我当时在气头上,随口说出这三个字,在中国这是骂人的话,以后不要轻易乱说!”
“骂人的话?”
“嗯。”
“阎教官,你为什么要骂人?”
“因为你们在训练场上表现不好。”
“如果我们考核获得了优秀呢?”
“那我就说好话表扬你们!”
穆亚拉夫点了点头,端着饭盆来到外军留学生吃饭的餐桌上坐下吃饭。
阎铁民自己也打了一盆烩菜,抓了两个馒头,坐下,吃着馒头,吸溜起猪肉炖粉条来。他三口两口就吃完一个馒头,半盆烩菜也吃了一半。
“报告——”
“进来!”
“报告校长,军训处教官阎铁民向你报到!”阎铁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道。
学校政委杨国良望了这个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院校的小伙子一眼,微笑道:“铁民,来,先坐下。”阎铁民刚要坐下,校长将军帽“啪”地一掼,厉声道:“谁让你坐下了?一边给我站着!”
阎铁民吓得赶紧立正。
“校长,我到底犯了哪条军规?就是送我上军事法庭,也得让我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大错?”
“犯了哪条军规你不知道?苏联伏龙芝军事院校留过学就了不得了?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谁都敢骂了?不扳掉你身上的骨儿刺,你披着被子上天,张狂地没领了!”
“校长,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创创报社的记者你都敢骂?你小子是不是想翻天?”
“校长,你搞错了吧,我什么时候骂过记者?是谁给你打小报告说我骂过记者?有政委作证,你把他叫来,咱们来个当面锣对面鼓,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阎铁民辩白道。
“你是背着牛头不认赃!人家报社领导把电话都打到政委那里告状,你还给我说假话抵赖?”
“小阎,前几天在战术合成考核中,你是不是骂过一个女记者?”杨国良笑道。
阎铁民早把那档子事忘到爪哇国了,他摇头坚决予以否认。
杨政委又问:“人家要采访你,被你断然拒绝,有没有这些事?”阎铁民恍然大悟道:“是那个脖子上挂照相机的丫头片子?”
“什么丫头片子?你明天提上水果给人家道歉去。”
“什么?我去给她道歉?校长,你还是处分我吧。”
“这是命令!要么年底转业,要么给人家姑娘道歉,两条路你自己选择!”
“校长,没那么严重吧?为一个会照相的姑娘,您就忍心让我卸甲归田?”阎铁民吃惊道。
“你试试看!”老校长一点玩笑的意思都没有。
“小阎,”政委笑着拍着阎铁民的肩膀道,“我们坦克二校在宣传方面一直比较弱,为什么?缺乏笔杆子,搞军事的人才很多,没有一个能把我们的典型事迹宣扬出去的,好不容易来一个党报记者,又让你轰走了,这事要在新闻界传开了,以后谁还来我们学校做宣传?”
“好吧,那我就死乞赖皮地去一次,成不成我可不打保票。”阎铁民吭哧半天道。
“你少给我念经,女记者一次不来,你跑一次,两次不来,跑两次,什么时候人家愿意来了,算你把任务完成,否则当心我剥了你皮!”校长沉着脸道。
第一次去道歉,人家女记者外出采访,阎铁民沮丧地回来复命。
“今天没找见,明天接着去,找到人家记者赔礼道歉,直到人家满意为止。”老校长冷冰冰地说。
“我不去!”阎铁民梗起脖子。
“你敢?”
“全报社的人都以为我是找那姑娘谈对象!”
“报社就是把你当成上门女婿你也得去!人家记者一次不来,你请一次,10次不来,你请10次!”
阎铁民又一次硬着头皮去了报社。今天运气好,女记者舒蕾没有外出采访任务。阎铁民鼓足勇气敲了门。
“请进!”房门坐着一个50岁左右胖胖的男人,已经谢顶,稀疏的头发盖不住宽阔的额头,看见一身军装的阎铁民进来,和蔼地问:“解放军同志,你找谁?”
阎铁民真像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仿佛让人看穿了心事,脸一红,不安地说:“请问舒蕾同志在吗?”男人抬起头,隔着一个办公桌问道:
“小吴,舒蕾呢?”戴眼镜的姑娘冲着里面的办公桌喊:“舒蕾,有个解放军找你。”正在里面打电话的舒蕾回道:“帮我招呼一下,我马上就说完。”
戴眼镜的小吴姑娘以为阎铁民是舒蕾刚谈的男朋友,看见他窘迫的样子,指着旁边一把空椅子,捂着嘴吃吃地笑着说:“您……您请坐。”
阎铁民不知道这个姑娘笑什么,本来就紧张的他显得更紧张了,双手不停地搓着军裤,不知道说什么好。舒蕾从里间走出来,看见阎铁民窘迫地坐在那里就想笑,想起在训练场受到的奚落,小心眼的姑娘故意绷着脸大声道:“阎大教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舒蕾同志,那天实在对不起,是我态度不好,请你原谅!”阎铁民的脸更红了。
“我哪儿敢记恨你?”舒蕾冷笑道。
阎铁民一张黑脸更加黑红了,他将水果朝桌子上一放,尴尬道:
“雷校长委托我给你带些水果,我走了……”话没说完,一溜烟似的跑下楼去。
“哎——,你等等——”舒蕾提着水果追到门口,阎铁民已经跑得没影了。
舒蕾返回办公室,几个男女记者“呼啦”一声全围拢过来。
戴眼镜的姑娘指着舒蕾笑道:“舒蕾,不够意思吧?背着姐妹偷偷谈一大军官,老实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舒蕾,你太残忍了,粉碎了我的爱情梦想,我太伤心了,我悲痛欲绝啊……”一个男记者夸大地说。
“德行!”舒蕾啐道。
“上帝啊,采编室要发生地震了……”同舒蕾一样大的女记者林佳感叹道。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舒蕾笑道。
“不是男朋友,他为什么要给你送水果?不是男朋友,他为什么一进我们采编室,脸红得像高粱,跟毛脚女婿见丈母娘一样?”戴眼镜的姑娘不依不饶。
“瞧他那做贼心虚的样子,傻子都能看出来不是来办公事的。”男记者起哄道。
“瞧你们这一出一出的,好像我快要嫁人了,同志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该干嘛干嘛去!”
谢顶的男人用手指笃笃地敲着桌子嚷道:“姑娘小伙子们,别嚼舌根了,该干活了!”一群男女记者陆续回到自己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