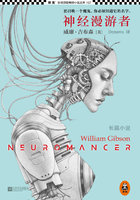“时常揭你短的,不一定是恶意,时常说你好的,不一定是善心。”
马老五搔着后脑勺,嘿嘿笑道:“活佛,马某是个粗人,只知道杀人放火,捅共产党的疼处,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我不会说话。”白菊花见缝插针:“打断骨头筋连着筋,天下救国军是一家人。”马老五踢了宗咯喇嘛一脚:“失去良心的人,比豺狼还要狠毒,这个内奸才是一匹可恶的恶狼!”一个小班弟向巴赞喇嘛请示道:“活佛,如何处置这个披着羊皮的狼?”
扑倒在地昏过去的宗咯喇嘛,被马老五踢醒了,他动了动胳臂,摇了摇疼痛的头颅,顽强地站了起来。
两个小班弟连忙将他从两边架住,不让其动弹。
“共产党是雪山上的太阳,它的光芒将照耀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弃暗投明吧,就你们这点人马好比蚂蚁撼大树,扭转不了乾坤,若再杀人害命,将永远坠入十八层地狱不得超生!”宗咯活佛大义凛然地说。
“宗咯,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巴赞喇嘛冷笑道。
“魔鬼张牙舞爪,众生水深火热,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好!我成全你!押下去,剥了他的人皮做鼓,放在佛祖的法座前,我要让转轮寺所有的法台、僧官、提经、班弟都知道,给共产党通风报信的下场!”
两个小班弟押着宗咯往外走,走到经堂门口,宗咯哈哈笑道:“你们害命杀生,造下无边罪孽,罪盈恶满,必有地狱之灾、阿鼻之难!”
“慢着!”白菊花朝门外喊道。
两个小班弟一愣。
“白菊花,我的少校参谋,你到底搞什么鬼?”马老五生气地问。
白菊花瞪了他一眼,对巴赞喇嘛说:“活佛,不要杀他!”
“为什么?”
“狼不吃野狐子,都是跑山的,因为他也是个喇嘛!”马老五嘲弄着白菊花。
“兔子硬要仿照狮子跳雪山,一定会跳到深谷里摔死!你错了,我并不是因为他是喇嘛才让活佛饶他一命,他对我们有用!”白菊花冷冷地说。
“一个叛徒,对我们有什么用?”
“毛绳子越拉越长,闲球话越说越多,干脆剥了他的人皮做鼓得了!”马老五玩弄着他的手枪不耐烦地说。
“我们设在骆驼山转轮寺的救国军司令部已经暴露,商云汉就是彭德怀专门派来剿灭我们的狼群,我估计这是一场恶战,鹿死谁手尚难以预料,如果我们战败了,留着宗咯喇嘛做人质,我们就可以和商云汉讨价还价,逼他们退出骆驼山,如果我们获胜了,就招集方圆七百里的善男信女,当众剜眼、砍手、断足,剥下他的人皮做法器!”
“丫头说的有道理,但这个牦牛犊子出卖了我们,不给他一点血的教训佛爷会降罪。”巴赞从法座下面抽出一把尖刀,冷酷地说,“不用戴石帽了,马老五,挑了他的两个眼珠子!”
马老五接过巴赞的尖刀,像吃了大烟土一样兴奋,愉快地吹着口哨,一步步地走向宗咯喇嘛。
宗咯喇嘛呵呵冷笑着盯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一声惨叫,两个沾血的眼珠子滚到地上,疼到肺腑的宗咯喇嘛跪在地上,双手捂住眼睛大喊大叫,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里流出来……放会的钟敲响了108下,巴赞喇嘛在一群法台、僧官、提经、班弟等僧侣的簇拥下,念着“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生……”的口诀出了经堂。
肥头大耳的巴赞身着一身藏红色的袈裟,摇着从印度灵山进口的紫檀木法轮,脚蹬一双黑底勾花蒙靴,满面微笑地穿过僧房附近的甬道,来到转轮寺正殿,向两米高的释加牟尼金像敬献酥油花,并念起供品加持咒。身后年轻的小僧侣们已经正襟危坐,正殿里响起此起彼伏的诵经声。
僧众在领诵师嘎宗巴的带领下。音调一致地诵经,大殿里响起一片婉转祥和的诵经声。在释迦牟尼佛的注视下,僧人们颂念起五部祈愿经,殿内佛声、罄声、海螺声不绝于耳。
“活佛放会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拥挤到正殿前广场的数千名善男信女一起流着泪呼唤起来:“佛爷——佛爷——”
在大法螺、唢呐、刚洞、筒钦等乐器演奏的法乐声中,巴赞喇嘛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有几十个善男信女跳起了法舞枟钦木枠。舞者带上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面具,在法乐的节拍下跳起演示佛教教义的舞蹈。迷信的人群拥挤得更厉害了。
“好哇,莲花湖的珍宝,愿我功德圆满,与佛融合,众生平等,解脱苦难,大慈大悲,大彻大悟,光明自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唵——嘛——呢——叭——咪——吽——叭咪吽——南无慈力主佛,南无慈藏佛,南无智慧胜佛,南无弥勒仙光佛,南无日月光佛……”巴赞用洪钟一样的声音领头念诵。
所有在场的法台、僧官、提经、班弟等僧侣低头念诵道:
“如是等一切世界诸佛世尊,常住在世,诸世尊当慈念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从无始生死以来所做众罪孽,若自做,若教他做,见作随喜若塔若僧若四方僧物。若自取若叫他取,见取随喜,五无问罪,若自作,若叫他作,见作随喜,十不善道。若若自作,若叫他作,见作随喜,所作罪障或有覆藏,或不覆藏,应坠阿鼻饿鬼畜生,今众生皆忏悔……”
念经完毕,巴赞喇嘛开始摸顶赐福。上万善男信女,有老人,有孩子,有妇女,有猎人,自动排好队,虔诚地接受巴赞喇嘛的摸顶赐福,巴赞每摸一个人的头顶,都要嘟囔一句“唵嘛呢叭咪吽”。光摸顶赐福就进行了一个上午。
几个小班弟端来数箩筐红枣。
巴赞喇嘛抓起一把又一把红枣撒向等待的人群。人们疯了一样拥挤着去抢夺祛病纳福延年益寿的临泽红枣。当第9筐红枣快撒完的时候,山外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响。
“活佛——”一个满脸血污的土匪探哨从飞驰的马背上跳下来,跌跌撞撞地跑上山,扑倒在巴赞喇嘛的脚下放声痛哭:“我们在拦羊镇伏击商云汉骑兵大队,寡不敌众,800叉子枪骑兵全军覆灭……”
“什么?全军覆灭?”巴赞喇嘛愤怒地揪着土匪的衣领,“我的八百护法没了?”
“骑兵大队有机枪、迫击炮,我们的斧头和叉子枪根本不是对手,商云汉的人马穷追不舍,已经来到沟外……”
正在接受红枣的人群有了骚动,大家小声议论着,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血头污脸。
“一群酒囊饭袋!”巴赞抬腿一脚将满脸血污的土匪踹倒。
为了蒙蔽群众,巴赞喇嘛使了个眼色,一个红衣小班弟将土匪扶到佛堂后面的耳房。
“佛爷的儿女们——”巴赞喇嘛开始了挑唆和煽动,“共产党派出骑兵几万人,对祁连山北麓的尧呼儿、黄番、华来番动手了,刚才这个藏胞兄弟就是从共产党骑兵的枪口下逃出来的,这次屠杀是大规模的,蒙古、回回、尧呼儿,他们一个也不放过,佛爷的孩子,你们遇见恶魔了,你们要遭难了……”巴赞说着,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他的一番煽动果然奏效,善男信女异口同声道:“誓死保护活佛!”
巴赞喇嘛站在经幡下大声道:“共产党解放军在大西北不慈不悲,不仁不义,瞒心昧己,对我西域诸族大肆杀伐,害命杀生,不能一视同仁,他们已经造下无边罪孽,那些骑兵大队罪盈恶满,定有地狱之灾、阿鼻之难,今天,我们救国军前来拯救佛爷的子民,我们必将让那些前来杀害我们少数民族同胞的骑兵大队以身还债,将肉饲人,永坠阿鼻,不得超生!”
前来放生会朝圣的信徒被煽惑得热血沸腾,挥动着手里的腰刀翻身上马,跟着马老五、白菊花、巴赞喇嘛一行“嗷嗷”叫着冲下山,潮水一样向红柳沟东北方向奔去。
红柳沟。
两支武装在大雨中对峙。
商云汉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吃惊道:“这么多土匪?”
“多数是无辜的少数民族群众,只有少量土匪武装。”戴着眼镜的政委段立人说。
“强攻显然不行,这样会伤害到无辜群众,通知部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大队长,我看只有靠政治攻势了!”段立人打了一个喷嚏。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段政委,宣传群众、瓦解敌人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段立人喊道:“通信员——”一个背着长枪的小个子战士喊了声“到”,来到政委面前。“把喊话的喇叭取出来!”不一会,通信员取来一个喊话的喇叭。
“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前来红柳沟剿灭马老五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杀害无辜干部群众,炸毁铁路桥梁,暴力冲击政府,制造恐怖事件,破坏西北人民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希望大家不要听信坏人的挑唆,赶快回家去……”
人群里有人愤怒地质问:“你们剿灭土匪跑到我们红柳沟干什么?
难道红柳沟里窝藏着土匪?”有人骂道:“失去良心的人比豺狼还要狠毒,你们共产党解放军是来剿灭我们的魔鬼!”
“全国都已经解放了,难道大家还不相信解放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我们咋可能去向自己的父老乡亲开枪?我们是来搜寻从青海流窜到河西的土匪马老五的,请大家不要相信土匪的谣言,相信自己的政府,相信党,相信人民的子弟兵!”段立人用喇叭解释道。
“既然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带着迫击炮、机枪到红柳沟来干什么?”
“滚出去!牧区里只有活佛,没有土匪!”
“乡亲们,你们听信了坏人的谣言,土匪头子马老五就藏在骆驼山上的转轮寺,他杀了多少无辜的群众,你们知道吗?这个马步芳的残渣余孽,欠下西北人民多少血债?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捉拿归案!”
“保护活佛,同解放军拼了!”混在群众队伍里的土匪开始给骑兵大队扔石头和装了汽油的燃烧瓶。骑兵队伍里不断有人受伤。段立人不为所动,继续他的政治攻势:“乡亲们,请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坏人就在你们身后,你们每前进一步,我们就多一份危险!”
巴赞喇嘛、马老五和白菊花站在人群后面的一处高地上,几个小班弟扯着一张黄色的油毡布为他们遮风挡雨。
“那个戴眼镜喊话的人是谁?”马老五不耐烦地问。巴赞喇嘛道:
“听我们的人说,骑兵大队的政委段立人戴着眼镜,在苏联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这个喊话的该不是他吧?”
“这个喊话的眼镜一定是骑兵大队的一个大官,我知道共产党部队作战的纪律,遇见危险,当官的都站在最前面。他能冒着石头和汽油瓶的危险继续喊话,一定不是个小人物!”白菊花冷笑道。马老五掏出盒子枪吼道:“我带人去砍了他!”巴赞喇嘛拦道:“杀一只羊羔子用得着这么费力?菊花,看你的了!”一身青衣的土匪递给白菊花一杆26式中正步枪。
白菊花接过钢枪,娴熟地拉开枪栓,推子弹上膛,尽管大雨天的光线有点暗淡,但这个在南京政府受过专门射击训练的军统特务,轻松地举枪瞄准,眼睛,准星,枪口三点成一线,眼看用喇叭喊话的段立人就要成为这个女人的枪下猎物。突然,有个人影在段立人面前一晃,白菊花叹了口气,缓缓地将枪放下。
警卫员见雨越下越大,连忙给段政委撑开一把油布伞。白菊花又一次将枪举起,瞄准了段立人的头颅。
“啪——”混乱中一块石头飞来,砸在段立人的额头上,顿时血涌了出来。
“卫生员,快,政委受伤了!”卫生员快速上前,用绷带给政委包扎头上的伤口。
白菊花恼道:“他娘的,猎一头熊也没有这么复杂!”
血流满面的段立人眼看群众要冲过来,一把推开卫生员,继续用喇叭喊话:“乡亲们,不要上土匪的当,不要给土匪做挡箭牌,请你们尽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土匪手里有武器……”
白菊花又一次举枪瞄准。
“啪——”
随着一声枪响,白菊花26式中正步枪的子弹,在政委段立人的右眼上方穿了个眼,他身子一挺,瞪着眼睛,保持着用喇叭喊话的宣传姿势,向后仰面直直地倒在雨水射溅的泥泞里……政委白皙的面皮比平时显得更苍白了,脸上并没有很多的血污,只有纳鞋绳子粗细的一股红,从右眼上方的枪眼里流出来,像一条粗蚯蚓一样蠕动着,慢慢地爬进右边的耳朵里,不等灌满耳朵,血就不流了。营养了段立人政委35年的鲜血,从脑袋后边一个茶盅大小的窟窿里喷了出去,顺着肆虐的雨水慢慢流了出来。
“政委——”警卫员大声哭喊。
“政委——”大队长商云汉跳下马背,在雨水泥泞中抱起段立人,拼命摇晃着已经牺牲的战友,试图把他唤醒,然而,段立人再也睁不开他眼镜后面一双黑白分明的丹凤眼了。
侦察排长高战元拔出双枪,愤怒地高喊:“妈拉个巴子,跟他们拼了!”义愤填膺的战士群起响应。
白菊花潇洒地抬起冒烟的枪口。
“射中了?”巴赞喇嘛吃惊地问。
白菊花笑而不答。
“这么远的距离,你隔山能打着野兔?”马老五有点不相信。
白菊花抽出一根烟点燃,醉人的红唇一嘬,吐出一个烟圈,慢悠悠地回答道:“看看那边,已经乱了!”
骑兵大队的副大队长张景涛、副政委陶广智、参谋长叶锐、政治处主任黄凤鸣等人围过来,喊着,摇着,乱成一团。各连连长、指导员、副连长、排长、党员、班长等骨干都打马冲在前面,用自己的血肉身躯组成一道人墙,挡住飞来的石头、棍棒和燃烧瓶,不断有人受伤。
“大队长,下命令吧,我们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打吧,大队长,为政委报仇!”
“为段政委报仇!”
商云汉放下段政委的遗体,铁青着脸站起来,望着越来越逼近的群众,腮帮子可怕地抖动,他低声怒吼道:“马老五,血债要用血来还!
我一定要砍下你的头颅祭奠政委的在天之灵!”高战元噙着眼泪道:
“大队长,你就下命令吧,不活捉马老五,我誓不为人!”商云汉悲愤地吼道“回去!后退三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违令者军法从事!”
“大队长——”
“执行命令!”商云汉挥拳将段立人政委的坐骑打了个趔趄。
“哈哈,解放军不敢开枪,活佛,你这招果然奏效,你看,有那些愚蠢的信徒走在前面,骑兵大队的人开始向后撤退了,不敢动刀动枪!”
马老五伸出大拇指夸赞道。
“对付共产党,活佛早就胸有成竹!”白菊花优雅地吐着烟圈。
“菊花这一枪打得好!打死了共产党的头羊,头马不慌,马群不乱,头马死了,马群肯定会乱!老五,招集你的敢死队,挥动月牙斧头,趁着混乱从侧翼冲到共产党骑兵前沿,能砍死几个算几个!”
“活佛,您就放心吧,精明的头羊会把羊群领到好草场,敢死队,集合!”马老五哈哈笑道。
马耀清带着100多人的月牙斧头敢死队集合。
马老五交代一番,头戴白帽的敢死队员每人握一把宽刃月牙斧头,在马耀清的率领下,冒雨翻身上马,闪电一样大喊大叫着从侧翼向前冲去。
骑兵大队立足未稳,站在前面的连长、排长、班长等部队骨干,有的被土匪的月牙斧头削掉了头颅,有的被拦腰砍翻。有的头颅还连带着一条血肉模糊的胳膊,解放军官兵伤亡的情景惨不忍睹。
因为商云汉下了不开枪的命令,解放军官兵只喊着“打,打,打……”但没有一个人敢真正开枪,因为大家谁也弄不清楚这些头戴白帽子的汉子到底是土匪还是群众。
土匪们砍杀一阵后,耀武扬威地打马回营。
骑兵大队的阵前横陈了上百具骑兵大队骨干党员和干部残缺的尸体。鲜血顺着雨水流进了红柳沟里的季节河。
见到连长、排长和班长被无辜砍掉头颅,很多士兵伤心地大哭起来。
一个人高马大的山东兵提着一杆步枪,抹着眼泪大步流星地走到大队长商云汉面前。
山东兵“哗啦”一声将子弹推进枪膛,“扑通”一声跪在泥水地里,双手将步枪递过头顶。
“鲁奇同志,你干什么?”商云汉惊讶地问。
“大队长,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不想这么窝囊活着,与其让土匪的月牙斧头砍死,不如让你打死痛快……”鲁奇孩子一样“哇”地一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