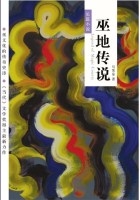13.莫名其妙的恐惧
每当晚霞染红天际的时候,瓦尔德·朱力便喜欢推开房间的窗子,吹着新鲜的晚风,看那只倦归的鹈鹕落在窗外那株茂密的菩提树上。酡红的夕阳沿着破碎的云絮渐渐西坠,火烧云将蓝得炫目的天空烧成了暗红色。落日的红光,将菩提树雪白的塔状花穗和碧绿的阔叶涂抹得一派辉煌。
鹈鹕哀叫着抖动双翅奋飞的姿态,常常让他浮想万千。每当这时候,罪恶便在心灵的荒原沉睡,所有腐败腥秽的思想和战争气息,便随着清爽的晚风飘散了。这时,瓦尔德·朱力那张冰冷的脸,便有了淡淡的暖意。灵魂的冰毒正被人性本真的阳光融化,那双深嵌的灰褐色眼睛里就有了月光一样温柔的东西。这种巨大的原始的自然力量,给他一种返璞归真的呼唤。它用淡淡的云,微微的风,蓝蓝的天和缀着绿色阔叶的菩提树笼罩他,包围他,使他感觉自己的渺小、屈辱、孤独和无助,感觉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自己的生命同样像别的生命一样,如一粒微尘,一粒沙子,随时都能灰飞烟灭,化为虚无。
瓦尔德·朱力的房间非常宽大。地板上铺着一块席子般大小绣着神话中欧罗巴公主骑着神牛形象的阿拉伯金丝绒地毯。天蓝色的墙壁上画着两把交叉的纳粹军刀。军刀与军刀交叉处,托起一个令人恐怖的白色骷髅,这是瓦尔德·朱力自己的杰作。靠墙有一张宽阔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架手摇式电话和一沓厚厚的文本卷宗。桌上还悬有一面德意志的星条旗。办公桌的对面,摆放着一排深红色的长沙发和几张深红色的椅子,窗帘是用黄色丝绸做成的,非常考究。办公室里有一个漂亮、宽敞的套间,没有朱力的命令,谁也不敢进去,包括党卫队官兵和德国本土来的女监工。
自从撞见母亲和农场主通奸的场面,瓦尔德·朱力便陷入一种巨大的孤独之中。尽管母亲是为了自己和儿子的生存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但瓦尔德·朱力心中的仇恨与屈辱却怎么也解不开。他常常对着黑夜的月光悄然低语,又长长地吁气,并努力让自己挣脱回忆的束缚获得自由与新生的气息。他多想把生命播散在黑暗的夜气里,和缓缓飘泊的云,积雪皑皑的山,透明的湖水融为一体。这种来自潜意识的寂寞,让瓦尔德·朱力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他对所有的女性产生了仇恨与厌恶。上完中学后,他离开了汉堡的农村,离开了让他尴尬而羞愧的母亲。大学4年,多少漂亮的日耳曼女孩暗恋着他,想找机会对他诉说相思之苦,都被这个冷漠的年轻人拒之门外。在瓦尔德·朱力的潜意识里,婚姻、爱情、性交都是丑陋和肮脏的,是一种上帝无法饶恕的罪孽,一旦背负上这种罪孽,灵魂将永远在地狱里无法超生。在这种不断扭曲的变态心理的支配下,瓦尔德·朱力选择了纳粹,选择了党卫队,决心为第三帝国的崛起奉献自己的全部生命。
然而,在党卫队司令总部工作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妻子克拉尔的背叛,又给他的内心留下了沉重的伤害。
自从成为一名党卫队军官,他就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念头,那就是借助元首发动的这场战争,消灭这人世间残留的罪孽与丑恶,他奉仰的是古罗马人的格言:“紧握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
副旗队长威廉·达拉第少校皮球一样肥胖的身体从门外挤了进来,他手里拎着一个大约公元前450年前制作的古代双耳黑色陶罐。
瓦尔德·朱力从窗户前收回身子,眼睛逐渐冰冷起来,冷冰冰地问:
“那是什么?”威廉·达拉第咧着厚肥的嘴唇一笑,说:“前线将士收缴的,我知道您喜欢考古,特意送给您。”瓦尔德·朱力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
这是一件真品。在将近两个世纪里,欧洲的陶器制造艺术以黑色绘画为主。这的确是古代的绘画风格,人像呆板,几乎都是侧面像,坐姿生硬,面部没有表情。这只双耳陶罐的图像表现的是一个神话故事,传说中的埃涅阿斯和阿喀琉斯在掷骰子。陶土的天然颜色使整只陶罐的底色呈深红色,而人的侧影则填满黑色,细部和边线用石头做成的尖头工具刻划,使粘土的颜色明显突出。
瓦尔德·朱力一边仔细观察着陶罐上图像的线条走势和颜色,一边赞扬威廉·达拉第:“达拉第,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这确实是古代的黑色陶罐,我如果没看错的话,它应该是公元前450年的东西。”威廉·达拉第头点得像鸡啄米,一张粗糙的胖脸放着兴奋的红光,随声附和道:“大概是吧,反正我看不懂。”瓦尔德·朱力嗅着陶罐的气味说:“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他大力推行著名诗人梭伦的立法改革,把贵族的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为了繁荣城邦经济,大力提倡制陶业。在庇西特拉图任雅典僭主的时期,手工作坊主发明了一种新的焙烧技术,让红色人像陶罐取代了比较简单的黑色人像陶罐。不过这是公元前560年以后的事情了。”威廉·达拉第对历史知识和古代制陶技术一窍不通,只有傻笑着点头。顿了顿,瓦尔德·朱力问:“那些女战俘的尸体怎么处理?”威廉·达拉第“啪”来了个立正,行了个军礼说:“报告上校,挖坑埋了。”
“那衣服和鞋子呢?”
“有一部分衣服和鞋子还在第三囚室。”
“糊涂!”瓦尔德·朱力突然咆哮起来,“国际战俘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怎么办?立即派人,不,你亲自去,立即把英美联军残留的衣物鞋子统统用火烧掉!”
“是,上校!”
“战争不是消遣,我们必须为元首的总体战略负责,仅仅依靠冒险和赌注的娱乐心态是不行的。它不是随心所欲、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目的而采取的严肃手段。”
“我知道,军人必须服从政治。”
“你知道什么?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在这个集中营每天要死多少犹太人和战俘,仅仅靠挖坑掩埋是不行的,一定要在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军视察之前建好集中营的第一座焚尸楼,记住,要质量上乘,规模宏大!再有半点差错,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肥胖的威廉·达拉第敬了个军礼,屁颠屁颠地跑了。瓦尔德·朱力又拿出放大镜,仔细赏玩着古代的黑色双耳陶罐,陶土的底色以及人物侧影的黑色线条让他如痴如醉。大约把玩了半个小时,他才小心翼翼地将那只双耳陶罐放置在他办公室的博古架上。占去半边侧墙的博古架琳琅满目,有克罗马农人的石斧,尼安德特人的抛矛器,刻满线形文字的迈锡尼石板,武士双耳爵和几何陶罐等。这都是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战争让这些稀世珍品从各个德军占领国的考古博物馆落在了瓦尔德·朱力这个冷面打手的手里。
威廉·达拉第离开后,瓦尔德·朱力的房间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平静。瓦尔德·朱力仔细地端详着办公桌上那块削刻了一半的根雕,他拿过刻刀,精心地削刻着鹰的翼翅。他构思雕琢的这个根雕艺术品,是一个收敛双翼凝目雄视的鹰,这个纳粹党卫队的旗队长正用这块丑陋的树根表现着自己,目极八荒、主宰生杀、不可一世的狂傲心态。在他聚精会神的雕琢下,鹰的双翼渐渐有了轮廓,他一刀一刀仔细地刻划,平面的翼翅有了羽毛的涡纹,有了翼的质感,黑色、黄色的木屑飞落在他的身上、办公桌上。瓦尔德·朱力一点也不在乎,他沉浸在一种追求艺术的喜悦里,满脸是细密的汗水。
在夕阳透过窗户斜射而入的余晖里,金色的光影淡淡地涂抹着,瓦尔德·朱力的神情是那样专注,似乎蕴含着一种热爱艺术的圣洁。
这一刻,对美与力的艺术神往,完全占据了他原本冰冷的思维空间,沉浸在雕刻的世界里,完全忘记了血腥现实的存在。
这时候,套间虚掩的房门“吱”一声自己洞开。瓦尔德·朱力抬起头,他看见一个挂在墙上赤身裸体的年轻女人,正冲着他嘿嘿冷笑,似乎那白森森锋利的牙齿,沾着一点腥红的血一样的东西。一阵黄昏的山风,“呼啦”一声从开着的窗户灌了进来,黄色的丝绸窗帘便“噼噼啪啪”随风飘动。他打了一个寒颤,心里涌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14.醉人的康乃馨
依尔斯·卜莉歪歪斜斜地靠在瓦尔德·朱力的办公桌一侧,痴痴地看着朱力上校正在雕刻日耳曼人的祖先力量之神曼努斯的圣像。
那只鹰的根雕已经完工,就置在办公桌的一侧。这是一只猛禽,它收敛双翅,深藏利爪,傲视群雄,完全是一副冷眼看风云的模样。瓦尔德·朱力上校此时此刻正沉浸在雕刻艺术的愉悦之中,那块巴掌大的美国黑核桃树根在瓦尔德·朱力上校的手中像变魔法似的飞快地发生着变化。依尔斯·卜莉为什么不站得正一点呢?也许是她想借此故意吸引这个集中营党卫队旗队长的视线,以便让他爱上自己至少是喜欢自己;也许是因为身不由己,就像雪人在熊熊烈火面前禁不住要融化倾斜一样。
这个女人像是变幻莫测的6月天,忽儿乌云遮蔽晦暗一片,忽儿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在她不喜欢的男人面前,她的脸上像太阳被乌云遮蔽一样消沉,而在她喜欢的男人面前,她的脸上像晴空万里的阳光一样灿烂。当初,当党卫队副旗队长“肥蝎子”威廉·达拉第以重金把她从金蛇夜总会赎出来,并让她去波兰任集中营女监工时,这个年轻的脱衣舞娘曾感激地流下了泪水,并发誓要给这个肥胖的党卫队军官做一辈子情人。很快,依尔斯·卜莉便对这个肚子像啤酒桶一样,仗着舅舅冈瑟吕特晏斯是海军上将混到党卫队副旗队长位置的男人产生了厌倦,这家伙除了一顿能吃一只烤鸭喝10瓶黑啤酒外,再没有别的能耐。同党卫队的其他纳粹军官相比,威廉·达拉第显得太没层次,太没魅力了,不仅仅是因为他长相丑陋,主要是因为威廉·达拉第见了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人总是色迷迷走不动的样子。依尔斯·卜莉难以忍受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个肥胖的家伙缺少纳粹军人应有的铁血气质和文化修养。现在,依尔斯·卜莉站在瓦尔德·朱力面前,两只又细又长的眼睛,闪烁着幽幽的狐狸般的光芒,两颊鲜艳如玫瑰,醉人的红唇显得非常性感。她几乎是贴着瓦尔德·朱力,仿佛是要倒在他怀里,却又怕他拒绝,便用了最后一点女人自尊的理性力量,支撑着自己软弱无力的情欲。
她故意将她的一只白晳的、半握的手放在瓦尔德·朱力上校的面前,那么近,近到他稍稍一动便会碰到它,那只手柔软白嫩,像一团蚌肉。那是她情欲世界里发出的第一颗信号弹,是试探也是期待,五根手指微微颤栗。它分明是要上校去握、去吻,去紧紧地拥抱那激动喜悦、温软香柔的异性身体。
然而,瓦尔德·朱力上校正沉浸在雕刻艺术给他带来的愉悦之中,眼前似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艺术之神维纳斯。其实,瓦尔德·朱力早就注意到这个来自柏林金蛇夜总会的女人了。她的两只乳房鼓胀像两座坟包,两只乳头像母山羊的犄角,将黑色的皮夹克顶得老高,两只浑圆的臀部高高翘起,非常丰满。双腿丰满修长,腰部有旖旎动人的优美弧度。然而,由于瓦尔德·朱力对所有的女人都有一种仇视的心理,越是窈窕的女人,他越厌恶。瓦尔德·朱力讨厌这个女人的挑逗,他多少已经耳闻这个从金蛇夜总会招来的女人和副旗队长威廉·达拉第之间黏黏糊糊的异性关系,他甚至听站岗的哨兵说,这个女人还曾在夜晚衣衫不整地从党卫队军医汉斯·科赫的房间跑出,出来时竟然光着两条白腿,连鞋也没穿。看见这种挑逗,他就会想起依尔斯·卜莉漂亮背后的轻浮。作为纳粹军人,他非常厌恶这种轻浮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