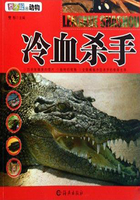依尔斯·卜莉之所以不敢贸然向瓦尔德·朱力示爱,主要是因为上次在军医汉斯·科赫那里碰了钉子。依尔斯·卜莉之所以要三番两次地挑逗党卫队的军官,是因为这个女人过惯了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在夜总会里,她喜欢同不同的男人享受床笫之欢,但这个男人必须有气质、有吸引力,令她心醉,让她痴迷。她在与不同男人的做爱过程中,体验到了什么是肉体的风雷闪电,什么是精神的最高愉悦,什么是生命的激情澎湃。与威廉·达拉第有过两次野合之后,依尔斯·卜莉便失去了对他的肉体渴求。在她的眼里,这个肥胖的家伙像一堆风干的牛粪一样,稀稀松松的残渣下没有任何象征生命激情的东西,尽管这个男人曾让她脱离了夜总会,给了她一个富有政治前途的职业,然而在依尔斯·卜莉眼里,两情相悦的性爱比空荡荡的政治狂热更重要、更实在、更具体。
依尔斯·卜莉说:“朱力上校,在集中营所有的军官当中,你是最博学的。”
瓦尔德·朱力正沉浸在雕刻艺术的狂热与激动之中,头也不抬地说:“是吗?那是你的偏见。”
见瓦尔德·朱力开口说了话,依尔斯·卜莉两只细而长的眼睛放出幽幽的光亮,进一步说:“不管是不是偏见,你的渊博的考古、绘画知识,以及在刑法上的独特见解,是日耳曼帝国的骄傲,你能否给我详细讲讲提香的酒神节油画。”
瓦尔德·朱力说:“今天恐怕不行。”
“有什么不行,今天战俘营没有什么重要任务,你尽管讲好了。”
瓦尔德·朱力连连摇头:“不行,我今天要让日耳曼人的祖先力量之神曼努斯复活。”
“大神曼努斯?”
“是的,他的勇敢和智慧孕育了日耳曼民族。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民族分为3个支派——因加旺人、赫米侬人和伊斯塔旺人。”
“那么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居住在什么地方?”
“卡蒂人居住在现在的黑森地区,弗里斯人分布于莱茵河与埃姆斯河流域,卡乌其人生活在威悉河的河口附近,而聚集在其南面的则是阿米尼乌斯所属部族的切鲁西人。”
“上校,你真博学。”
“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所以我们要不惜用武力消灭劣等民族,把日耳曼文化推广到全世界。”
依尔斯·卜莉得寸进尺,她几乎把脸贴在瓦尔德·朱力的脸上,嗲声嗲气地说:“所以,我们对这些劣等民族的反抗者绝对不能心慈手软。”瓦尔德·朱力没有吱声,继续专注于他的雕刻。
“上校,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
瓦尔德·朱力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停下手中的雕刻。
依尔斯·卜莉以为男人已经对她动心,趁势半推半就地坐在上校的腿上。女性特有的肉体温热和头发上的法兰西香水味,让瓦尔德·朱力有点莫名其妙的晕眩。
女人两只细而长的眼睛,幽幽地放射出一种勾魂摄魄的醉人魅力。两片性感的红唇,像两瓣不堪风雨的桃花,微微吸张着,在颤栗中显现出一种鲜艳的诱惑。瓦尔德·朱力的心情异常复杂,对依尔斯·卜莉说不出是欣赏还是厌恶,是需要还是拒绝。
依尔斯·卜莉此时此刻却完全意醉神迷了。她手拈一枝红得醉人的康乃馨,用细密的柔软花瓣轻轻地摩挲着瓦尔德·朱力那张英俊、冰冷的脸。
在康乃馨花瓣轻轻的摩挲下,瓦尔德·朱力也有些微微的醉了。
他感到汉堡原野上的清风轻轻地吻着额头,棉花一样纯白的云朵在他的身下缓缓移动,太阳暖融融的手指轻轻地捧着他那颗冰冷而坚硬的心。那只铁青色的苍鹰,突然划动翅膀,飞向飘泊着朵朵白云的高空,残阳如血,鹰的全身几乎涂上了一层炉火一样的光泽在空中盘旋。它原本想做一个勇敢的俯冲,却寂然地落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好似一块树根。这个汉堡天空的灵物,曾经驮着朝霞飞掠在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之上,呼啸着从高空俯冲下来抓住过田野里疾驰的野兔,又从高空将失神落魄的野兔摔死在地面的岩石上。曾经在大风中搏击过流云,斜穿过突如其来的猛烈暴雨,要让它做人的俘虏,那无疑是要它的命!尽管它钢勾似的利爪,搏击风云的黑色羽翼,曾经傲视群雄、锋利如刃,但受伤了,被俘了,一切都会无济于事。想到这里,瓦尔德·朱力的鼻尖有些发酸,一颗大大的泪珠从他那双灰褐色眼睛里滚落下来。这滴泪珠里有对故乡、对母亲的回忆,也有对所有异性的仇视。
“你怎么啦?上校。”依尔斯·卜莉第一次看见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旗队长目光像兔子一样迷离,他的脑海闪烁着被遗留在故乡千里之外的童年。“没有什么。”他冷冰冰地说,“卜莉,你真的需要爱情吗?”依尔斯·卜莉不知道瓦尔德·朱力上校的用意,还以为她的万种风情已经生效。她俯下自己那双颊娇艳、热气腾腾的脸,用潮湿的雨中花瓣一样的嘴唇吻着上校的脸、耳朵和头发,并低声嘟囔道:“是的,上校,在战俘营,我是一个寂寞的女人没有人能真正和我心灵相通。我需要你……”这时候,一位刚刚清洗完党卫队司令部浴池的犹太女人,从窗前经过,瓦尔德·朱力突然两眼放光,像深山里的猎人看见了一只野兔。他推开依尔斯·卜莉,抓起桌上的手枪,“砰”那个正专心走路的女人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从她的嘴和鼻子里慢慢溢出。枪响的同时,依尔斯·卜莉瞪着惊惧的眼睛尖叫了一声。瓦尔德·朱力冷笑了两声,吹了吹枪口还没有完全散尽的硝烟,说:“这才是爱情!
人与武器的爱情,它可以使人的肉体和精神产生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这种震撼对于我来说,比与任何女人上床更快乐。”
依尔斯·卜莉吓得扔下那枝红得醉人的康乃馨落荒而逃。
15.新婚之夜的尴尬
望着依尔斯·卜莉逃去的背影,瓦尔德·朱力从鼻孔挤出一声冷笑。自从妻子背叛他以后,女人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诱惑力了。
在他的眼里,女人完全是一种肮脏的雌性动物。那美丽容貌的背后,掩藏着罪孽和自私的丑陋情欲。
自从汉诺威参加党卫队后,瓦尔德·朱力在仕途可谓一路顺风。
他的学识和才干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被推荐到柏林党卫队司令部工作。在司令部,瓦尔德·朱力担任全国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将军的法律顾问。海FA·希姆莱同样对瓦尔德·朱力的才干很欣赏。
1934年6月,希姆莱同他一起参加了希特勒亲自逮捕罗姆及其褐衫队的行动。在慕尼黑,瓦尔德·朱力的表现非常出色,几年功夫他由少尉提升为少校。希姆莱决定重点培养他,并把自己的表妹克拉尔介绍给瓦尔德·朱力。在瓦尔德·朱力的眼里,令人闻风丧胆的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一位冷酷狡猾的人。他身材中等,一张平庸的脸略微显得有些浮肿。短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的下巴给人一种性格上软弱的错觉。而那双透过夹鼻眼镜不时向四周扫视的青灰色眼睛,却又暗示出非常坚强的意志力。他的一双胖手白白嫩嫩的,像女人的手一样。希姆莱将阿道夫·希特勒枟我的奋斗枠奉为经典,并将其反犹太主义的专著牢记心间。希姆莱全盘接受了种族论的观点,并在党卫队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人生性俭朴,过日子精打细算,从不乱花钱。有时候没烟抽,就跑到瓦尔德·朱力的办公室借一支雪茄。希姆莱给党卫队定了一条铁的纪律:“对偷钱的人,即使一个分尼,也要处以死刑。党卫队队员决没有任何权利贪污一块手表、一个马克、一支香烟或其他物品。”
瓦尔德·朱力最后离开党卫队总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满口仁义道德的希姆莱,实际上是一个卑鄙的色狼。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同妻子玛加丽特的感情破裂后,曾跟一家酒馆的舞女犹太姑娘英格·巴尔科私通,使这位犹太姑娘被父母赶出家门。在搞大了巴尔科的肚子以后,他又缠上了酒馆女主人的女儿,遭到姑娘的严词拒绝后,转而钟情于他过去的女秘书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对于这个色狼介绍的姑娘,瓦尔德·朱力的心里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他又不敢公开提出拒绝,他害怕希姆莱手里主宰生杀的权力。
克拉尔,那个热情奔放的日耳曼姑娘,完全为瓦尔德·朱力的气质所吸引,深深爱上了这个英俊而冷漠的小伙子。
然而,新婚之夜却非常尴尬。
克拉尔拉灭了屋里的灯。淡淡的月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夜风轻轻地吹着,院子里花的暗香随着夜风送进屋里。克拉尔从背后抱住了瓦尔德·朱力,她的潮湿的染着口红的嘴唇吻着丈夫的脸、耳朵、头发,并低声呢喃:“朱力,亲爱的,你是我的,我唯一的爱人……”在克拉尔的亲切爱抚下,瓦尔德·朱力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感到一种压抑,一种不习惯的痛苦压抑。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家里的卧室只有一张双人床,床上只有一床被子,却放着两个睡枕。多么奇怪,仿佛是一瞬间,就跑来一个女人。
克拉尔抱着瓦尔德·朱力温存了一会儿,见他无动于衷,以为他在操办婚礼中累了,便爬上床,熟练地摊开被子,说:“你洗洗吧,早点休息。”这个女人今夜竟要睡在我的旁边?瓦尔德·朱力在胡思乱想中点着了一支雪茄。
“你不是不抽烟吗?怎么这会儿还抽烟?”克拉尔的语气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
“还不想睡。”瓦尔德·朱力抽了一口,抱歉地向克拉尔笑笑说,“我很兴奋,今夜的月色真美啊,院子里的苹果花开了。”
克拉尔也笑了,但躺在被窝里没有作声。
“克拉尔,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瓦尔德·朱力坐在床沿上,问她。
克拉尔一双迷人的蓝眼睛看着卧室饰有古代骑士图案的屋顶,沉默了片刻,调皮地反问:“那么,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是因为希姆莱将军吗?”
克拉尔生硬地笑了一下:“哦,难道我们走近结婚礼堂是表哥用权力强迫的?”
“当然不是。我是想说我是清贫的,我一直想着一个人生活……”
瓦尔德·朱力喃喃地说。
“我寻找伴侣,不是去淘金,只要这个人可以依靠,我便爱他一辈子,至死不悔。”
“你觉得我可以依靠吗?我想你该找一个比我有出息的男人,至少要比我有钱……”
“睡吧,睡吧。”克拉尔温和地表示了不耐烦:“你胡思乱想这些干什么?既然已经结婚了,就想着以后怎么过好日子。”
“怎么过日子呢?”瓦尔德·朱力讪讪地问,一边慢慢地脱衣服。
任何人的性格形成都和他小时候某种刻骨铭心的经历有某种关联。
瓦尔德·朱力永远忘不了母亲和农场主之间发生的奸情,在他少年的记忆里,小伙伴们在上学的路上或者在学校里做游戏的时候骂母亲是“荡妇”,骂他是“野种”的声音,至今在屈辱的记忆中回响。还有那赤裸裸的淫荡和丑恶仿佛灼红的烙铁,让他的心永远吱吱地冒烟……直到今夜,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伤痕累累。
“来吧。”克拉尔说。
瓦尔德·朱力撩开被子,看见了和母亲一样雪白的女性身体……在最后一刻,少年时的记忆突然复活了:他看见了母亲不堪入目的裸体,还看见了在母亲身上像尺蠖一样蠕动的农场主……所有耻辱的记忆纷至沓来。
瓦尔德·朱力跪在床上,用双手猛地捂住眼睛哭了。
他越哭声音越大,最后变为失声恸哭。克拉尔后来如何穿起衣服,又如何安慰他,又怎样一个人孤独离开,他都不知道……后来的日子里,瓦尔德·朱力试了几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每次他都像被人在背上抽了一鞭子似的……“你是不是有毛病?”克拉尔轻轻地推开他,叹息了一声。
“我,我不知道……”瓦尔德·朱力揉着剧烈跳动的太阳穴,嗫嚅地说:“过去……我不知道……只是……”母亲的丑事,他实在羞于启齿。
“算了,以后我们分开睡。”克拉尔冷冷地说。妻子的郁郁寡欢,不自然的笑容和藏在温顺与体贴下的怜悯,让瓦尔德·朱力无地自容。
他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肉体与灵魂要分离了,做为男人的年轻的瓦尔德·朱力少校在这场灵与肉的搏斗中失败了,像罗马斗兽场败下阵来的一头公牛。
平静的日子过了几个月,不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甘寂寞的克拉尔背着他和一个文静瘦弱的男人在家里偷情。而这个和克拉尔偷情的男人正是全国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