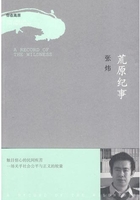江峰环顾四周,小声道:“你到内堂去告诉他,我等他,不然你就替他送葬吧。”
正在这时,堂内走出一行黑衣人,簇拥着往茶馆外走去。
江峰凝视着这一行人,人群中有一个人的缎面长袍若隐若现,江峰将礼帽飞了出去,一个箭步向前跨去。
茶倌叫喊着:“五爷快跑。”
黑衣人铸起一座人墙,蜂拥而至,与江峰厮打起来。突然面前一道劲风袭来,江峰一个侧身躲了过去,一根手臂一样粗的长棍落空。
黑衣人手里拎着棍子。
川剧锣鼓此刻停止了,戏子一溜烟儿跑得不见了。茶客们见此番情景纷纷夺路而逃,他们显然不想惹祸上身。
“砰!”江峰的拳头狠狠地打在了来人的肩膀上,一阵骨裂的声音传出,被打中的人抱着胳膊倒在地上不停地叫着。旁边的几个黑衣人拎着棍子就向江峰打来。
细雨后的山城被薄雾笼罩着,歌乐山显得巍峨而又朦胧,与尘世的喧嚣相比,显得静谧且悠远。山谷中隆起一处台地,长青的白松簇拥着一所白色的别墅,这所别墅便是有名的“香山别墅”,因为主人姓白,所以大家也习惯称它为“白公馆”。
提起“白公馆”,也许在你的脑海里依然浮现着《红岩》中那所惨绝人寰,关押着众多的革命先烈和政治犯的监狱。其实,自1930年修建之日起到1939年的9年的时间,白公馆只是一个私人公馆。只是在1939年10月28日,国民党军统局用30两黄金将其买下后才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在这之前这座公馆的主人叫白行之,大家都尊称他为白老爷。
白老爷有个军阀哥哥,是重庆鼎鼎有名的袍哥舵爷。在重庆帮会中,势力最大的就是袍哥,袍哥按仁、义、礼、智、信五堂排名,单公口就有300多道,人数达十万之众。水码头是滋生重庆袍哥的温床,旧时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重庆码头。城中九开八闭十七门,除通远门唯通陆路外,其余各门均面临两江。于是,重庆城因码头而兴,因商贸而盛,各具特色的行帮码头便应运而生。自然,哪个码头生意兴旺一些,占据这个码头的帮会就强势一些。白老爷掌握着重庆最大的水码头——朝天门,再加上他凌厉强势的作风,自然地赢得了在袍哥中的坚实地位。
杀手
白公馆颇具西洋风格,主体建筑为中西合璧式二层楼房,青砖灰墙。在云雾缭绕的青山绿水之中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
公馆门口,仆人用长杆将一个一个红色的灯笼有序地挂在屋檐上和宅院四周。
白行之和坤叔都已年过半百,都是教父式人物。白行之霸气、睿智、果断。表面上儒雅斯文的坤叔却是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白行之从堂口走了过来,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他环视一下,顿觉思绪万千,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记忆伤痕的年代。
这时,云雾多变的天空将一丝霞光隐没。
“老爷,你……”阿坤不解地看着白行之。
白行之内心复杂地望着晚秋的天空,黯然地想说什么。
这时,突然“砰”的一声,一把黑伞撑了过来,遮挡住他们整个身躯。
白行之面不改色地叹道:“阿坤啊,我们俩能够平静地站在这里欣赏落日,不容易啊。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阿坤不解地看着白老爷。
白行之和坤叔是结拜兄弟,他们之所以今天能站在这里享受白府的荣华与富贵,都是血与火的斗争中用生命换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真不愧是强者的乐园,弱者的地狱——灯红酒绿的三不管地带,充满着血腥和残酷,砍砍杀杀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卧虎藏龙的险恶江湖,动荡不安的社会时局,辛酸无奈的市井苍凉,一群充满热血的袍哥们,随时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江湖神话与喋血传奇。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盲目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里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袍哥们经历着炼狱,又祈盼着飞向天堂……
在重庆龙蛇混杂的袍哥帮会的打打杀杀中出了不少乱世枭雄。几大帮派在利益的驱使下互相残杀,已经没有了人性。
白行之最怕人家叫他老大,因为他觉得在江湖中随时都在出现神话,袍哥随时都可能杀掉老大,政府也在打黑盯着老大,敲诈勒索无处不在,为了利益无中生有的罪名让你瞬间人间蒸发……
但是在阿坤的心目中,他一直认为老大太过谦虚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该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白行之回过神来,朝空中一拍手,宅院四周火红的灯笼都点亮了:好一派张灯结彩的景象。
管家坤叔一脸的憨厚,猫着腰说:“老爷,您看行吗?”
红色的光映在了白行之的脸上。“好,不错。”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道,“我只有逸芸这一个女儿,明天的……什么舞会来着?”
坤叔回答:“老爷,是化装舞会。”
白行之笑了笑又摇了摇头,一脸慈祥的感叹:“对,对,化装舞会,尽是些新鲜玩意儿,阿坤,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啊,袍哥的各大舵把子,各大堂口的管事都会来。”
“老爷,那湖广会馆呢?”坤叔问道。
“再说吧!”白行之警觉地看着阿坤说,“对了,他去了吗?”
坤叔点了点头应声道:“去了。”
“做得干净点。”白行之笑了笑道,“我不想添任何麻烦。”
坤叔点了点头回道:“我明白!”
白行之拍了拍坤叔的肩膀说:“兄弟,这些年辛苦你了!”
听到这样的话,坤叔打心眼里生出一种幸福感,他抬起头来看着白行之,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中:我们生死走来,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况且在我们袍哥中,也得有一个在明处主持正义的吧……
心里的话音刚落,白行之摆着手,久久地看着阿坤。他心里十分明白,能坐到今天的位子上,成为袍哥的舵爷,在重庆码头上呼风唤雨,受人尊重,没有阿坤是永远办不到的。
朝天门码头,雾霭沉沉,一片苍茫。
朝天门,一座神奇厚重的雄性之门,立于两江交汇之处:一条是奔流不止的嘉陵江,一条是横贯苍茫大地的长江。重庆水码头上舟舸穿梭,举帆落帆,扬桨收桨,一片繁忙的景象。
吊脚楼下的青石板小道上,身着青衫,头缠青布头帕,腰围黑丝带的“袍哥大爷”从茶馆堂口里进进出出。
一群浑身赤裸,逆江而行的纤夫豪唱着:“天府国水码头要数重庆,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朝天门大码头迎宫接圣,太平门吃的是海味山珍;储奇门卖药材医人病症,千斯门鲜包子雪白如银……”
码头上的洪崖茶馆,一片热闹非凡的气象。小小的舞台上,川剧刚刚开场,锣鼓齐天,喧闹不断。再大的噪音似乎也无法阻止茶客们摆龙门阵的兴头。茶客喝着茶、磕瓜子儿,风风火火地聊着码头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此刻,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头戴织贡呢礼帽,身穿白绸衣衫的人矫健并急速地走进了洪崖茶馆。他叫江峰,他的职业充满了血腥——杀手。进门后,他挑了一张没有人的茶桌,在桌子右边坐了下来。
茶馆虽小,但也是江湖人士聚集的地方,来来往往都是袍哥人家。所以,茶倌除了会添茶倒水,更要学会看人。
茶倌小二提着炊壶走了过来:“这位大爷,您喝什么茶?”
“叙府毛尖。”说完江峰冷冷地看了茶倌一眼。
茶倌一边转身拿茶碗,一边打量着江峰,吼道:“哎——,毛尖一碗,多放几片叶子。”茶倌给江峰端上茶小声问道:“您是白老爷的人?”
江峰有些吃惊。他的脸上和身体上并没有印着白公馆的标记,为何一个小小的茶倌都能洞察自己的来历?他很清楚,作为一个杀手他不能出卖了自己的主子,他更不能因为一个茶倌而乱了手脚,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他眼光中透露着一股杀气,狠狠地看着茶倌的眼睛。
茶倌惊觉着正要离去。
“我要见你们管事的洪五爷。”江峰站在他面前道。
“五爷不在。”茶馆知道来者不善,故作镇静地回答。
江峰环顾四周,小声道:“你到内堂去告诉他,我等他,不然你就替他送葬吧。”
正在这时,内堂走出一行黑衣人,簇拥着往茶馆外走去。
江峰凝视着这一行人,人群中有一个人的缎面长袍若隐若现,江峰将礼帽飞了出去,一个箭步向前跨去。
茶倌叫喊着:“五爷快跑。”
黑衣人铸起一座人墙,蜂拥而至,与江峰厮打起来。突然面前一道劲风袭来,江峰一个侧身躲了过去,一根手臂一样粗的长棍落空。
黑衣人手里拎着棍子。
川剧锣鼓此刻停止了,戏子一溜烟儿跑得不见了。茶客们见此番情景纷纷夺路而逃,他们显然不想惹祸上身。
“砰!”江峰的拳头狠狠地打在来人的肩膀上,一阵骨裂的声音传出,被打中的人抱着胳膊倒在地上不停的叫着。旁边的几个黑衣人拎着棍子就向江峰打来。
“啪!”的一声,江峰硬生生地接住了对方的棍子,一脚狠狠踹在对方的肚子上。几根棍子一起袭来,江峰一把接住将棍子顺势一横,架在头上,挡住了想要打过来的棍子,然后一个侧踢把另几个冲上来的人踢退了几步。剩下的一人握着棍子的一头,江峰微微地笑了笑,握住棍子的另一头使劲地向上撅着。对方开始的时候一只手,后来实在承受不住,两只手一起上,但是丝毫顶不住江峰一只手的力量。棍子的一头还在升高,黑衣人实在抵抗不住,一把松开棍子退了出去。江峰拿住棍子狠狠地向对方的腿上砸去,“砰”的一声,所有人都倒在了地上。
重逢
江岸边,一个身影婀娜多姿的女人迈着一双修长的腿来回走动着,她叫燕珍。
燕珍穿着旗袍,头上裹着头巾,她凝视着并不平静的江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江中一艘小船向岸边驶来,夏人杰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个皮箱,望着这并不是太熟悉的城市。
燕珍嘴角微微上扬,她要等的人终于来了。
夏人杰和燕珍走在古镇青石板的小道上。夏人杰英俊潇洒,深沉而清高、重感情、武艺高强。燕珍天生丽质、爱憎分明、聪慧过人。重逢的两人没有往日儿时的话语,他们默默地走着,彼此之间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相视、回避,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夏人杰低头看着燕珍的高跟鞋,裸露的脚踝光滑而洁白。他收回了目光,似乎还不太敢看燕珍,看着远方说:“你还好吗?”
燕珍依然裹着头巾,恬静地点了点头。
这时,洪五爷狼狈地落荒而逃,一下撞在了燕珍的身上,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前奔跑着。
“他怎么如此地慌张?”夏人杰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洪五爷。
“这里不安全,你快离开这里。”燕珍不时回头张望着。
夏人杰有些惊讶地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快走,别多问。”燕珍递给夏人杰一张纸条说,“到这个地方去找我。”
“那你也小心一点。”夏人杰心中还是充满了疑惑。
“拿着。”燕珍从皮包里摸出一把手枪递给夏人杰小声道,“在这里拳头不是万能的。”她打量了一下四周,转身离去。
夏人杰不安地看着她,点了点头。
燕珍迅速钻进了一条小道,消失在了尽头。
夏人杰回过头,满脸是汗珠的江峰站在了他的身后。夏人杰背着身,机警地斜视着对方。
江峰满怀敌意地看着夏人杰。他心里非常明白,此人来者不善,必须脱身,正要向前跑去。夏人杰移动着步伐堵住了他的去路。
“你是什么人?”江峰怒斥道,“为什么挡住我的去路?”
夏人杰点了一支烟,喷着烟雾:“这叫路见不平……”
江峰问道:“你想干什么?”
“你说呢?”夏人杰盯着他,说道。
江峰将拳头拎了起来,发出用力的骨节声:“好,那我就成全你。”说完冲了上去……
两人交起了手,在激烈的打斗中双方不分上下。
几个回合后,江峰转身向前跑去。
夏人杰看着江峰离去的背影,陷入了沉思。他到重庆,不,应该说他回到重庆,为的是解开一个让他痛苦了二十年的谜团。
层峦叠嶂的山前是吊脚楼。洪五爷奔跑在吊脚楼前,江峰在后面紧追不舍。
洪五爷跑进一个木结构的民居里,江峰跟了进去。民居里四通八达,有无数的过道。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江峰掏出了枪,凝视四周的一切,他闭着眼睛似乎在凝听着什么。他的耳朵随着风的律动在舞蹈,在安静得几乎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空气中,俘获到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江峰下意识地举起了枪,他一睁眼,一个小男孩稚嫩的脸出现在江峰面前,枪口正对着小男孩的头,小男孩惊恐的双眼中闪烁着泪花,双腿颤抖着,裤脚湿了一片。江峰扣在扳机上的食指慢慢放松了下来。
透过残破的窗户,江峰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在屋梁上晃动着。
“站住!”江峰越过窗户,跨到了横梁上。
洪五爷喘息着在屋顶的砖瓦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着。
江峰举着枪对着洪五爷的脚边开了一枪,子弹将瓦片击碎飞溅了起来。
“别杀我、别杀我……”洪五爷顺势从吊脚楼的屋顶滚落到了一角,他蜷缩着身体。
江峰冷酷的脸上基本没有表情,说道:“你知道我只是一个执行者。”
洪五爷惊慌失措地回答:“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白行之给你什么,我双倍给你,五倍给你,十倍给你,求你不要杀我。”
江峰正准备扣动扳机,洪五爷从裤腿里摸出一把枪朝江峰开枪,江峰一个侧身,子弹射进了他的手臂里,洪五爷爬起来拔腿就跳到了另一个吊脚楼的房顶上,继续死命地奔跑着。
江峰举起了枪,子弹拽着风呼啸在空中,昂头挺进,发出凄厉的撕扯声,它把风扯出一道口子。“砰”的一声,正中洪五爷的胸膛。洪五爷的身体缓缓坠落,江峰的眼神透着坚毅和自信,手臂上的鲜血正顺着指尖一滴滴地滴在了青色的砖瓦之上。
也许是枪声的惊动,一群鸽子飞向了天空。夕阳快要西下,在余晖之中,白鸽排着纵队翱翔在天际。江峰靠在房顶,凝视着远处,他其实也渴望像白鸽一样,在属于他的世界里自由的飞翔……
他点燃了一支烟,内心十分茫然。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戒烟好久了,可是从前天开始,总是有种再次点燃香烟的冲动。即使没有真正去抽它,但是心里已经吸了好几根了。恍然间才明白,原来自己已经在替人消灾,杀人赚钱。这时他感觉冷汗突然冒了出来。他痛苦地将手抬了起来,鲜血染红的手让他恐惧了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雾蔓延覆盖着他此刻充满仇恨的脸庞……
白公馆戒备森严,阿坤心神不定地张望着。作为管家,他对自己的职责非常清楚:保证公馆里的安全。
他走进了白行之的书房,只见白老爷沉醉在墨与神之间。他没敢惊扰白行之,静静地在一旁坐了下来。只见墙上的大钟“滴滴答答”地转动着,发出了心跳般的急促声。坤叔憨憨地看着老爷,这时他的内心很不平静,他急于告诉老爷眼前发生的事情,但始终没有动。白行之心领神会,不动声色地闭上了双眼游离在笔画之外……
白行之放下了手中的笔,问道:“阿坤你来多时了?”
阿坤起身憨憨地笑了笑回道:“老爷真是神来之笔呀……”
白行之没让阿坤把话说完。“以防后患,斩草除根。”指了指书桌上的字画,说道。
“神来之笔呀,神来之笔呀……”阿坤连声道,然后坚定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去。
客厅里,白行之的儿子白浩坐在沙发上,佣人们穿梭着做着各自的事情,房间里充满了寂寞的味道。他看着书房里父亲和坤叔在说话,嘴一直在动,却猜不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他渴望父亲能够重用他,可是他越想要得到的,父亲却永远让他得不到,他猜不透父亲的想法。突然间,他感觉自己在这个白公馆里越加地微不足道,渺小,小得几乎不需要半个位置的空间。他有些生气地点燃了香烟,深深地吸入、又重重地吐出,吸进的似乎不是团团烟雾,而是缭绕在周围的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