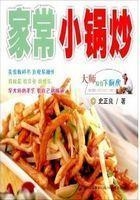这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的一天。
南京莫愁湖畔,杨柳依依、春意盎然。
作为明朝的陪都,此时的南京依旧是一派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气象。寓居此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正倚在临湖的窗边长吁短叹:那些寻欢作乐、醉生梦死之人,何曾想过国家的兴衰存亡啊!
侯方域,字朝宗,原籍河南商丘,出身于名门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朝廷做过大官,备受时人称赞。受其父亲影响,侯方域年少时便加入了复社——一个由继承东林传统的南北文士所组成的民间团体。
侯方域早年的诗文富丽华美,风格接近班固和宋玉;稍后又追求浩瀚之气,十分崇拜韩愈和苏轼。商丘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名城,居住在这里的侯方域得地利之便,曾时常在此呼朋唤友,饮酒作赋,尽展才华。
去年(1642),侯方域踌躇满志地来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名落孙山的结果。再加上战争频仍,南北阻隔,已有很长时间没能收到家中的来信。每每想到这些,一股惆怅之情便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
不知不觉,又到了每年的仲春时节。侯方域举目远眺,碧草连天,一望无际。可是战争还未结束,到处都是逃难的灾民,连一个可以结伴还乡的人都找不到。
“不要愁,不要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侯方域自言自语,企图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只是面对现实境遇,他往往身不由己。幸好,还有陈定生、吴应箕这两位复社好友,就住在相离不远的地方。他们时常互相走访,高谈阔论,抒发心中烦闷。如此一来,侯方域心中的寂寞才稍稍得以排解。
侯方域今日早起,是要和朋友前去城西的天宫道观共赏梅花。彼时,陈定生与吴应箕已在道观附近等候。
“兄弟,你知道最近有关起义军的消息吗?”陈定生问道。
“昨日听闻,起义军打败了官兵,节节胜利,快要攻入京城了”,吴应箕随即转向陈定生,悄声说:“左良玉将军把军队撤到了襄阳,现在中原已没有可以掌控局面的人。哎,此等国家大事,不宜过问,我们还是只管欣赏这春日美景吧!”
说话间,侯方域也来到了两人面前,连忙问好:“二位仁兄,果然比我来得早啊,让您们久等了!”
“没关系,我们也是刚到没多久!”吴应箕笑着说道。
“我已经派人去打扫道院了,并预备下了好酒,到时候咱们边赏梅边饮酒,岂不潇洒自在!”陈定生话音刚落,家童过来传话:“公子,今日赏花的人太多了,咱们来得迟了,还是回去吧。”
“怎么来迟了?”陈定生十分诧异。
家童道:“是这样,魏国公徐家的公子今日也在此请客赏梅,道院早已被客人占满了,我们找不到一块好地方了。”
听罢此言,侯方域在一旁提议:“既然如此,咱们何不去秦淮河边,一访佳人?想必也一定十分有趣!”
吴应箕接言:“依我看,咱们不必跑那么远。不知道侯兄是否知道柳敬亭,此人说书绝妙至极,曾被许多名士赏识。我听说他现今就住在附近,咱们何不前去听他说书,以消减春日愁绪呢?”
陈定生表示赞同,可是侯方域却怒气冲冲地讲道:“不就是那个柳麻子嘛,他最近做了奸诈小人阮胡子的门客,听这样的人说书,我看还是算了吧!”
“侯兄有所不知”,吴应箕笑了笑,然后说道,“阮胡子现在是苟且偷生,但心还不死,等待时机,以便兴风作浪。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揭发他的罪行。很多门客认清他的真面目后,都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这柳麻子就是其中的一位,也是十分可敬之人呢!”
“原来如此!”侯方域吃惊道,“想不到还有柳敬亭这样的豪杰,我们的确应该去会一会他。”
于是,三个人边说边行,朝着柳敬亭的住所走去,全然不顾道观里飘出的丝竹管弦之声。让别人去热闹吧,他们自有心向神往的趣事。
不一会儿,陈定生、吴应箕、侯方域三人就来到了柳敬亭的门前。家童前去敲门,大声喊道:“柳麻子在家吗?”陈定生连忙喝止了他:“柳敬亭是江湖上的名人,你应该称他为柳相公才比较合适。”家童随即改了口,再次敲门。只见一位胡须花白、头戴青帽、一袭深蓝色长袍的老者开门相迎,此人便是说书人柳敬亭。
见是他们,柳敬亭连忙施礼:“原来是陈相公和吴相公啊,有失远迎!”并用眼光打量着侯方域,问道:“不知这位公子是何人,老夫怎么不曾相见?”
陈、吴两位因与柳敬亭早已熟识,便特意把侯方域介绍给了柳敬亭。彼此客套一番后,柳敬亭将客人带进室内,请他们入座品茶。
弄清三人的来意后,柳敬亭说道:“三位公子都是谦谦君子,应该好好读《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圣贤书,不该跑到我这里,听这些俚语俗谈的。既然你们肯赏光来寒舍,老夫也万不能推脱。只是怕说的话太俗套,辱没了各位雅士的耳朵。这样吧,我权且把大家常读的《论语》说上一段吧。”
“您要给我们说《论语》,我很好奇,《论语》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吗?”
看着侯方域一脸疑惑不解的样子,柳敬亭不禁开怀大笑:“各位公子可以谈《论语》,难道老夫我就不能说《论语》吗?今天我偏要装装斯文,献丑说它一回。”说罢,就走向说书的位子,敲了一下鼓板,清了清嗓子,振振有声地念道: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原来,他引用的是李白《山中问答》的诗,意思是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住在碧山上,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闲适自乐。山上的桃花随着溪水悠悠地向远方流去,这里就像别有天地的桃花源一样,不是凡尘世界所能比拟的。这样一个精妙的开场白,使得陈、吴、侯三人啧啧称奇,兴致陡增。
接着柳敬亭拿醒木用力一拍,说道:“在座各位,今日我所要讲的不是别的,就是那《论语》里‘太师挚适齐’的内容。春秋时期,鲁国世道衰微,人心浮动,三家有权势的公侯欺负君主,擅自采用国君的礼乐。孔子听闻此事后,星夜驰骋,急忙从卫国返回鲁国。由于他的不懈努力,鲁国的礼乐又走上正途。曾为那些倒行逆施的权势们服务的乐官这才恍然大悟,悔恨交集,呜呼而散。一度热闹异常的戏场,顷刻间变得冷冷清清。你们评评,这孔圣人的手段厉害不厉害?
神妙不神妙?”
柳敬亭敲了下鼓板,改念白为唱词:“自古圣人手段多,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见那些乱臣贼子犯上无礼,随便用个小计谋,就让他们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走狗奴才见风使舵,见势不妙,便另投明主,反而成了高风亮节的大英雄,你说可笑不可笑?”
柳敬亭如此这般,在醒木和鼓板的交替起落中,一会儿娓娓诉说,一会儿朗朗唱诵。本是烂熟于心的故事,竟让陈定生、吴应箕、侯方域三个听得如痴如醉,难以自拔。
大约过了一小时,柳敬亭激越的话语戛然而止,收了道具,向他们拱手施礼道:“献丑,献丑了!”
这三人还意犹未尽,一边回味着刚才的故事,一边还礼。
“您过谦了!您刚才所说之书真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陈定生忍不住称赞,并接着说:“现如今,大家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写的文章,大都穿凿附会,枯燥乏味。哪能像您这样畅快淋漓,兴趣盎然呢?真不愧是绝技啊!”
“敬亭才离开阮家,不肯投靠别人,所以才借此故事明志。”吴应箕补充说道。
侯方域也连忙附和:“我看敬亭人品高洁,胸襟洒脱,和我们是同路之人。说书只不过是他闲暇时,拿来消遣的技艺而已。”
“过奖,过奖!”柳敬亭连忙摆手。
稍过片刻,侯方域又问道:“当时和你一起离开阮家的,还有其他熟识的朋友吗?”
“都已经四散而去了,只有苏昆生一人,尚且住在附近。”柳敬亭如是告知。
“苏昆生的大名,我也有所耳闻,一定是要拜访的。到时候还希望您能一同前往,也十分期待能得到您更多的指教。”侯方域谦恭地说道。
“指教不敢当。拜见苏昆生同样是我的心愿,自然是要去的。”
柳敬亭爽快地接受了邀约。
又互相寒暄了一番后,陈定生、吴应箕、侯方域三人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