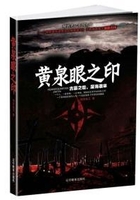成都有两个城,据说是有来历的。《名胜记》有言曰:
初,张仪张若筑成都,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出于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所掘处成大池,龟伏其中,故曰龟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秦张仪又于大城之西墉,别筑子城,《蜀都赋》所谓亚以少城,接乎其西也。王右军法帖曰:往在成都,见诸葛禺,曾问蜀事;云:成都城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具示,为广异闻。李石诗序曰:张仪司马错所筑大城,自秦惠王乙巳岁,至宋绍兴壬午,一千四百八十七年,虽颓圮,所存如断壁峭立,亦奇观也。范成大诗注曰:少城,张仪所筑子城也,土甚坚,横木皆朽,有穿眼,土相著不解。然则,秦城至宋犹存矣。隋,蜀王秀附张仪旧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广十里,亦曰少城。唐乾符六年,高骈于子城外增筑,周二十五里,曰罗城,亦曰太元城。后唐天成二年,孟知祥于罗城外增筑,周四十余里,曰羊马城。今城周二十二里,非其故矣。后蜀孟昶僭拟宫苑,城上尽种芙蓉,曰芙蓉城,又曰锦城。
可见大城少城,在前原是两个城,直到宋朝犹然。明朝改筑,便合而为一。当时城池甚大,据故书所载,张献忠初入成都时,城郭周长四十余里,光是水井,有三万多口。其后,他先生实施斩尽杀绝主义后,人是杀完了,城池是踏平了,只剩下蜀王宫——即是他先生的皇宫——三道宫门,同一段宫墙,三道横跨御河的石桥,以及一道长二十余丈高四丈余的王宫照壁。——至今名为红照壁,但照壁已在民国十四年,被四川当政的人抵押给成都商会,着商会将它拆卖了。——中间有十八年,不见人烟,而为虎狼所踞。直至清康熙初,才由官吏捐资,修筑土城,便把城垣缩小到周长二十二里,将以前的十八门,减少到四门。直至满洲八旗兵开来驻防,也在大城偏西画出一大片地方,缭以短垣,专驻满人,大家遂叫这地方为满城。现在大城满城又合而为一了,大概在民国五六年以后的成都人,虽然还知道少城这个名词,——民国建元以来,满城之名便废,复称少城。——可是已不复能指其形式,已不知道现在繁华的东城根街,即是以前满城的城垣。这里且说一说:
满城在成都之西,画大城一角。清康熙五十七年建筑,城垣周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门五:北门通大城守经街,大东门通大城羊市街,小东门通大城西御街,南门通大城君平街,以及大城之两门。各门皆有敌楼三间。每一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每一步甲,占地五十方丈,马甲,占地六十方丈。
到底地旷人稀,隙土甚多,树木甚众,房屋甚疏,街道甚阔。又因为驻防满人只准吃粮当兵,以防汉人,不许兼营他业。因此,在弓马之余,生活很是清闲自在,消遣之方,全在栽花饲鸟,植树钓鱼。以此,满城之内,不但到处古木参天,花树扶疏,抑且到处鸟声繁碎,积潦成池。也因为口粮有限,生活费用逐年增涨,人哩,又都养得懒懒的,没一点生产能力,所以十分之九的满人,都很穷,到处都显出土垣半圮,矮屋欹斜,没有余力培修。在大城人烟稠密处住久了的人,往往一进满城,就觉得到了另一世界,是那么的静寂!是那么的荒凉!偶尔遇见几个男子,不是拿着钓竿,就是掌着鸟笼,偶尔遇见几个妇女,都是搽脂抹粉的打扮着,并靸着半截鞋子,吧着长叶子烟竿,又都是那么的逍遥自在!但这绝不是乡野之趣,而是有诗的趣,有画的意。
不过在前满汉之界甚严,你们但从各城门上俱建有敌楼的用意上,就可看得出了。满人是可以到大城来,而汉人却不能随便进去,不是不准,是满人的气焰难受;就是一个小孩,他也有权力可以无原无故的打你的耳光,唾你的口水,扯你的发辫,叫你做奴才,而估逼你尊称他们的男女为老爷,为太太。更不必说要调戏妇女,要估吃霸赊了。
直到庚子以后,满人一天一天更其不行,穷的越穷,不能振作的越不能振作,气焰也就大不如昔。跟着排满的声浪传来,他们虽然还有所恃,却也不能不略有所恐了。于是稍有资产的子弟,竟有不遵祖训,跑到大城各学堂来读书的了,穷妇女们也有偷偷溜到大城,给汉人当仆妇,当临时姨太太的了,汉人也有侵进去做叫卖生意的了。后来提倡满汉通婚,想把二百余年来两个民族的仇恨,借男女的性器来调和冲淡,自然是个转机,可是汉人又不肯起来;把女嫁给他,讨厌他那臭架子受不得,娶他们的女,又讨厌她但能吃好,但能懒做。
宣统年间,放来一个将军,——专门管理满人的,非满人不能作,官阶与总督同为一品。——叫做玉昆的。此人比起一般满人要算明白得多。知道驻防满人已经走入末途,再照老规矩办下去,若不改弦更张,则全部满人,就不被汉人排斥杀尽,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一来就提倡招佃汉人到满城内去杂住和做生意,以增进满人的生资。后来又特意把那从小东门进去不远,关帝庙旁,一片广大的野树丛生,杂花满地的隙地,和一片大荷花池,开辟出来,改为公园;马马虎虎修造几所假洋楼,以及一些亭榭,招了几家餐馆茶铺,出卖门票,每人当十铜元二枚。
这是自有成都以来,破天荒的一个大公园,虽然屋宇修得太不好,毕竟树木还多,地方还大,又有池塘,又有金河,因此,公园一开,生意登时就兴隆起来。玉昆先生便一举两得,既有门票收入的利,又博了个颇颇开通的名。
从五月起,天气渐热,少城公园的游人也加多了。荷花池一带,更有佳趣,隔池便是丈多宽的流水的金河。金河边,与关帝庙的水榭相对,生生用砖石砌了一只洋船,居然有桅樯,有烟筒,楼头匾额,也居然题了“乘风破浪”四个大字,想来定是玉昆先生的得意之作。当时很引起了许多游人的讥笑,说满巴儿到底是俗物。却不知他还是临摹那拉氏颐和园的石船哩,俗物的责任,他真代负得冤枉!
这也是卖茶卖酒的地方。
下午五点过钟,蝉声噪得正厉害。淡淡的太阳,从阵雨后的湿云隙中漏出,照着池里碧绿的荷叶,静观楼周遭苍翠的柏树,从这“乘风破浪”的楼栏边望去,确不是大城里和田野间找得出的。只是相距不远处一排卖茶的水榭,临河撑出的参差篾篷,很为碍眼。这种总有缺憾的地方,倒是中国园林的特点,我们姑且置而不论,我们只须拿眼去看那楼栏边,那里不是有一张小桌子,不是有三个年轻人在那桌上小酌吗?你看,他们一面观赏斜阳里的景致,一面举着酒杯,一口一口的抿着,意态萧然,不是很像能与自然接近的三个幽人?
否否,不然!这三个人,并非什么幽人,而是我们已经认识过的楚子材,王文炳,罗鸡公,是也。
此日是他们学堂里试验完毕,正式放暑假的头一天。平日各人只管随便听课,用心也好,不用心也好,然而一到年暑假试验,大家都非临时抱抱佛脚不可。有志气的便不睡觉的温习课本,没志气的也不睡觉的抄写挟带,名字叫抄汞子。不过话也难说,罗鸡公是专门抄汞子的,能于一寸见方的纸上,抄十六个代数公式,两年以来,在同学中,已得了个矿务大臣的徽号;然而罗鸡公却抱负甚大,每每谈到天下国家大事,未尝不激昂慷慨,颇有经纶满腹,舍我其谁的样子,如此能说他没意气吗?楚子材怎的平庸小胆,并未打算过自己将来有多大作为,偏是个温习课本的人,希望分数及格,又不敢挟带,自然惟有“三更灯火五更鸡,”把不懂的硬记下来。王文炳则既不温课文,又不抄挟带,他的本事顶大,就是专门写别人的;比如上午试验数学,他先举眼一看,知道姓胡的数学向有心得,一上讲堂,他就坐在姓胡的身边,——那时学堂试验是不编坐次的——待姓胡的草稿做好,便不客气的拿过来先抄写。以他平日的威望,同学们自不便不受他的驱使,即监堂的监学与稍差一点的教习们,似乎也未尝想到要得罪他。所以每逢试验,他一直是逍遥自在的,而一直也未考在总平均八十五分以下。不过到底辛苦了,试验完毕,总要检平日彼此说得拢的,邀约几个,到小酒馆里,结结实实的慰劳一番。
王文炳当下用筷子挟了一块卤鸡,一面吃着,一面问楚子材:“你今年还是要回去吗?”
“我很近,通共只有一天的路程,回去转来,都方便,你呢?”
“大概不回去了,明天就搬到会府南街同乡处去。罗鸡公新婚远别,一定不能留在省里的了。”
罗鸡公笑了笑,又把大曲酒呷了一口,悠然望着天上的云花,似乎他的心早已越山渡水,飞回泸州去了。
王文炳笑道:“呃!我问你,讨了老婆,到底有啥子味儿?我想,不过睡觉时两个人挤在一堆,有点好处而已。其实是绊脚索,是消磨志气的东西,所以古人才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罗鸡公就是一个好例,从今年开学以来,一天到黑,迷迷胡胡,去年的那种豪气,一点都没有了。我劝你,罗鸡公,得看开点,婆娘是到处都有的。”
楚子材插嘴道:“我想鸡母一定生得好看,说不定还是一个美人哩,所以鸡公才念念不忘的。”
王文炳呵呵大笑道:“此一说也,姑存之!”
罗鸡公仍微笑道:“你们都是些鄙人,女人一定要生得好看,才可爱吗?等你们到有了与女人接近的机会,才晓得女人自有她可爱的地方,自有她使人留恋的地方,好看不好看,那不过是表面上的事!”
王文炳道:“好好!我明白了!俗话说的,中看的不中吃,中吃的不中看,大概罗鸡母是中吃的了。这也像朱云石的李小姐一样,在我的眼睛里,真就看不出李小姐的好看地方在那里,然而我们这位名士却颠之倒之,闹得满城风雨。若不是如罗鸡公的一样见解,就是所谓的色重一点了。”
说时把他的折扇递给罗鸡公道:“这是上星期我请他挥写的。这首诗,就是他去秋草堂情诗十四首之一,正把李小姐迷恋得神魂不定的时候做的。”
楚子材也偏过头去共看那诗:
短束征衣过草堂,马蹄零落乱秋香;
小栏画阁人何处?一树孤花对夕阳!
楚子材呷了一口酒道:“听说朱山出省了。那天演说时,激烈得很,硬把一根指头砍断了,可是真的?”
王文炳笑道:“你是从《同志会报告》上看见的吗?你不晓得,那是邓慕鲁撰稿时,故意跟他渲染的,其实,那里是这样一回事哩!那天是我亲眼看见的,他演说的时候,倒也激烈得很,大概说得高兴了,一拳打下去,刚好就打在面前的茶碗上,碗打破了,手也划破了,果然出了一些血。接着邓慕鲁就登台报告,借题发挥了一长篇,说朱志士不惜断指沥血来反对卖国贼,大家若果都有朱志士的气概,岂止盛宣怀不敢卖国,就是朝廷中一般少不更事的亲贵,也有所顾忌而不敢乱搞了。登时朱云石的志士之名大著,场内场外的人无一个不恭维他。第二天,就由会中派他往川东一带去讲演,并一路去鼓吹成立同志分会,同志支会,拿日子算来,该到重庆了。”
楚子材笑道:“如此看来,历史教习刘先生的话真不错!他说,历史根本就不可信,且不说后人与旁边人的记载,有入主出奴的偏见,就是自己记自己的事时,也没有逼真的。我们看朱云石这件事,刘先生的话真不错!”
罗鸡公道:“这回事体,想不到一般老酸倒跳得这们有劲。平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回却不同了。光看同志会成立那天,罗梓青那们一哭,把几百人都引动了,我向来不哭的,都不知不觉流下泪来。那时,只要他喊一声造反,我相信立刻就可暴动起来。”
楚子材道:“那天你也去了吗?我咋个没有看见你呢?”
“你在那一排凳上?我坐在顶前头的。”
“我挤进来时,你们都哭过了,只听见罗先生喊大家一致反对。跟着有人叫写名字,跟着就挤了出来。”
王文炳道:“罗梓青果然会哭,果然哭得动人,但是据我看来,会哭的先生还很多哩!比如王又新王先生,他自从二十九那天,同彭兰棻聂丕承几个人担任了讲演部的事情以来,无一次不是开口就哭,闭口也哭。以前,啥子人说过,宋太祖的天下是哭得来的,我看清朝的天下,恐怕会着我们四川几个老酸哭下台的。”
罗鸡公眼睛忽然几眨道:“老王,你是常在同志会跑的,我问你,那会里掌大权的是那个?”
“骨子里是蒲伯英,但他并不露水面,在表面上指挥一切的,自是罗梓青,他们倒很扣手,还有张表方,也是主动的一个人。文牍部长邓慕鲁,也有实权。像王又新等人,那是打旗旗的了,无足道也。你问他们做啥?”
罗鸡公端起酒杯道:“问一问,没啥子。再喝一杯好了!”
太阳更西下了,湿云散尽,满天碧澄澄的。一阵清风,带过一派荷叶的清香,吹在微醺的发烧的脸上,很是沁脾。酒已差不多了,楚子材拿出纸烟来,与王文炳各咂燃一支,刚回身向栏杆上一靠,忽听见河边上一个人在高声的招呼他。
他也打着回声道:“啊!吴管带……在柏树边静观楼上吗?……好,好!我就来!”
罗鸡公道:“你的朋友吗?”
“新近才认识的,是舍亲的老朋友,曾经在川边当过管带,才丢了差事出来。”
王文炳道:“那你就去罢,我们也快走了,只是你吃饱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