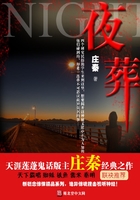当初宋家和杨家住在相邻的两个村子里,有一条从西山崖流出的泉水汇成的小河从两村之间横穿而过向东流去成了这两个村子的界河。宋家在河南叫南村,杨家的村子在河北,是北村。杨忠奎的父亲眼看着自己渐渐衰老,过一天没一天的;老婆早早死了,小儿子也大了,在城里上学回来家里也没有个人照应,就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弹,给儿子成了亲,好了却自己的这桩心事。他托人排生辰算八字说了几家,但儿子都没同意,硬说人家这些姑娘像地窝里的老鼠,土眉土眼的,自己看不上眼。老人家骂了几天以后,只好去让儿子自己找,说只要你看上不论谁家的姑娘,我就托人去说媒,就把她给你娶过来。说来也巧,那一天,杨忠奎从学校出来回家过礼拜天。他刚走到自己的村口,就看见河对岸有一姑娘在那里洗衣服。这姑娘身材长势非常好看,白皙的手臂露在水面上,一条粗粗的大辫子盘在脑后形成了一个环型的髻。杨忠奎愣愣地看了半天,心想这是谁家的女子,我咋从来没有见过呢?由于那姑娘是蹲着,蓝围裙把下身遮了个严实,所以看不清她是大脚还是小脚……这女子长相咋样?杨忠奎想看个究竟。他本想找个石头打过去,让溅起的水花迫使姑娘抬起头来,可就在这时,那姑娘正把涮洗的花布提出水面,仰起脸来,迎着阳光仔细地审视着,看自己到底洗干净了没有……这一下可把杨忠奎给看呆了。那净白的脸蛋,在被洗得褪成暗红底色粗棉布面过滤后的阳光映照下,鲜艳明丽。也不知是人映在布面上还是人布化为一体,杨忠奎仿佛真实地看到了一幅绝妙的西施浣纱图,生动无比。那女子就是宋二巧。这时,那女子觉察到有人就在跟前,就从布料后面侧过脸来剜了河对岸的小伙子一眼。尽管是慎怪的一瞥,但也温顺自然,这就使得杨忠奎从心底里一阵欢呼,这就是我要找的女人!她就是我的老婆!
他飞奔回家把自己的发现和决定告诉了父亲,接下来的事情异常顺利。宋家穷,一大堆女孩子。当家的又软弱没出息,仅靠三四亩崖沟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常年给人扛长工也没攒下点家底,所以也没有要多少彩礼就把二姑娘给嫁了过来。杨家的父兄们也拗不过自己这个尽管有辱门楣但也不管不顾的子弟,只好由着他的心思去办……
初婚岁月是幸福的,两人如胶似漆。尽管杨忠奎还在城里上学,但是天天往回跑。他把自己还很不成熟的青春蛮力毫无节制地倾泄到这个洁白柔顺的躯体上。他尽情地占有着,享受着……他嫌二巧这个名字太土气,在自己的同学们面前说不出口,就给她重新取了个名字叫淑卿。一来是取贞淑温良之意,二来呢是纪念他们初次相识是在那条小河的旁边,正好印证了“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句古诗。这个名字以后就成了宋二巧的正式名字,一直陪伴了她一生。新婚的宋淑卿就和一只小兔子一样任凭自己也还是一个大孩子一般的丈夫揉弄压迫撕撞。起初她还感到害怕,后来也就听之任之,尽量满足丈夫的那怕是无所顾忌的要求。她对夫妻间的性生活由羞耻害怕,很快就变成了麻木顺从。她从不主动迎合丈夫。每当她看到杨忠奎疯狂地折腾自己的时候,她总觉得不可思议,她想不明白男人们到底图了啥?后来,她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丈夫那气喘吁吁的面孔时,她明白了,这是男人们的事,女人们就像一口缸,生来就只是接受罢了。对此她终生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她把这个态度一直带到了部队家属营、半坡东街,也一直带到了她的晚年,以至于后来影响了杨忠奎对她的感情……也可能她也还是一个未发育成熟的小女孩的缘故吧,尽管他们如此做爱,她也还是多年未能怀胎生子,直到三十多岁随军后她才生了女儿杨秋华,又过了十五年才生了小儿子杨克华。单就这一点,丈夫也逐渐冷落了她。时间一长,杨忠奎就感到宋淑卿除了只能给自己缝补洗涮外,就是麻木顺从地应付自己旺盛的性欲了,毫无热情可言;而且两人的谈活也越来越少。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妻子毕竟是个村姑乡妇,是那样缺少见识和眼光,而又太多的婆婆妈妈,杨忠奎那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的热望仿佛碰到了一面不吐不纳冰冷的橡皮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美貌和娇躯失去了魅力。他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就连急需缝补换洗的衣裤鞋袜也是托人捎回来后再捎回到学校里去。思想上的差异,导致了感情上的裂缝,而且这个裂缝在他们今后的一生中都没有真正地弥合起来。要不是在他三十多岁那年,由于好事的朋友们的力劝,他才把这个苦苦等了他十几年的结发妻子接到部队驻地,否则,他很可能会让宋淑卿一人老死在老家那两间黑房子里的……就在对妻子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却和另外一个女人不期相遇了,而且也是一见钟情。不过这一回他和这个女人爱得却是那样深,那样缠棉久远,那样刻骨铭心,而且又那样历久弥新,但是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爱情给他们各自的命运带来的是那么不堪回首的痛苦。这种痛苦一直伴随了他们整整的一生,同时也随着他们一起走到了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今天,而且还影响着他们此时此刻的命运。
原来杨忠奎在县立师范,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同学,叫周武翔。两人岁数相当。周武翔长得比杨忠奎低,方头方脸,高鼻梁高颧骨,皮肤也比杨忠奎白些。眉毛却稀淡,在远处几乎看不见。说话声音不高,尾音有些颤,说完每句话之后声调都要发颤,显得好象十分激动。他酷爱打篮球,这一点和杨忠奎倒十分投机,也许就是在蓝球场上两个人结成好朋友的吧。那时周武翔还没有结婚,家里有一个后妈,没人管他。杨忠奎就把自己的和周武翔的破鞋烂袜子拿回去让宋淑卿给缝补洗涮,每星期一次。这样他俩的关系就日见紧密,简直形影不离。他们俩的这种关系当时在学校里十分引人注目。然而毕竟人各有各的志趣和理想。杨忠奎和周武翔各自为自己的打算和安排就很不相同。杨忠奎学习成绩各科都比较好,尤以数学见长,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当个科学家工程师之类的人,好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做点贡献;如若不成,好歹也要当个医生,争取做个名医,一生受人抬举,吃喝不愁。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成名成家、光宗耀祖。杨忠奎怎么也理解不了他的这个好朋友那些前所未闻却又令人目瞪口呆的言论和近乎天方夜谭般的理想。他总认为周武翔不是在做梦就是在说梦话,而周武翔当时的一切言行举止也确实与众多的乡绅才子格格不入。他不知从那里找来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和陈独秀等人的文章,每天废寝忘食地捧读。这一点就连杨忠奎也始终没有弄明白。周武翔骂自己的家庭是“吸血鬼”,他看见破衣烂衫、饥肠辘辘的种田人就流眼泪。他非常同情女人,他说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人把女人当作人看过,就是有钱人家的女人也很可怜,但是她们却是必须要铲除掉的那类寄生虫。他对当时的蒋冯阎混战义愤填膺,咒骂那是一头驴操两只牛屁股的事。他一提到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官僚派系林立明争暗夺,他那发颤的喉结就只能将每个音节单个弹出口腔,然后再连结成需要再补充一句才能完整的意思……他每每说完这些话后,总是让他的听众听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象绵羊一样的牲口,没有啥指望。中国的现实就是几只狼养着一群每天要吃掉的羊,而搞阶级斗争就等于是反了过来,要让羊吃狼!他对自己的老师也很不恭敬,说他们从来没有替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讲过话,都是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骗子……对于他的这些言论杨忠奎从来没有反驳过,只是以笑声回报。其实杨忠奎对他的这些高深莫测的理论根本就不知其所云。但他俩居然还能够相处如常,一直保持着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这在当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咄咄怪事了。相比之下,沉默寡言的杨忠奎的理想要简单得多。
就在杨忠奎结婚后的第二年,他们俩成了县立国民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确定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了。杨忠奎的哥哥们早就对继续供养这个小兄弟念书不耐烦了,威胁说将不再提供学费,并且给他指出两条出路:一是随兄弟们经商做个买卖人;一是做乡村教师养家糊口。杨忠奎从骨子里厌恶这两种职业。他哭诉力争,才和他的赡养者们达成“上学可以,但每年不能超出四十元学费”的协议。无奈,他只好放弃当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理想,因为培养这些人的学校都是要自己掏那昂贵的学费的,而去投考他从没想过又十分陌生不过却是政府出资培养军事人才的军校。尽管内心非常痛苦,即使受到“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嘲笑,他也硬着头皮顶着,坚信只要能出人头地就行。
周武翔尽管家境富有,可以提供他想上任何学校的费用,但是依据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志向,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院校,按当时的情况就是考省立国民师范。就在他们徒步去太原投考的那一天,杨忠奎见到了一个女子。然而就是这一相识改变了这两个好朋友的关系,导致了他们俩人几十年的爱恨情仇。这个女子就是周武翔的妹妹周武兰。
周家是长治一带有名的大户,到武翔兄妹这一辈已是四代靠放田吃租过生活了。这对兄妹的母亲原本是一个书香门弟家的小姐,生下武兰五年后便郁抑而死。随后他们的父亲又买了一个丫头续弦填房。父亲只顾新欢,新欢也还只是个小丫头。周武翔兄妹俩就是在这种放任无束和各种各样的奇思异想中长大的。
上路的那天天空湛蓝湛蓝的。晚上刚刚来过一场暴雨,温湿的泥土味和刺鼻的大麻味不时袭来。贫瘠荒凉的山地和田野绿色散乱地间隔着,就如同一个穿着绿格子衣裳半遮半裸的疯野村姑。庄稼还没熟透,心事重重但脚步轻快的杨忠奎顾不上看这初秋的原野,只顾闷头匆匆赶路。周家在城边,是他们去太原的必经之路。到了周家院子外,杨忠奎踌躇了一会儿。他向大门里望去。这是一座三进的四合大院,前院住长工和存放农具杂物;武翔住中院的西房,对面是粮库。武兰和父母就住在里头的院子里。
杨忠奎进院时,正是周武翔向家人辞行的当口,杨忠奎就径直走到了里院。杨忠奎对周氏父子的告别并没有太在意,但一个一边听别人谈话一边摆弄花枝的女子却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院子中间是个花池,池子中央种着一颗梅花树。周武翔曾说过这是他妈妈生前的爱物,一入冬就开白花。他妈妈特别喜爱白色,以至于把这个癖好也遗传给了她的这一双儿女。用砖和条石砌成的花墙上摆了几盆花。那女子一头的黑发正凑在一枝刚刚开放不久嫩生生白灵灵的菊花上侧。一件绢白的薄纱绸小领长衫紧紧地裹在身上。一眼看去,渐至发育成熟的肉体就是在娴静的状态下也微微地颤动,使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如同突突跳跃的火苗。这火焰把惆怅寂寞的杨忠奎内心烤得烘热难耐,欲火直舔喉管。姑娘衫子的下摆随着身体的屈伸深深地嵌进了那发育得极柔软细腻的体股缝里,仿佛整个身子都被分成了极为诱人的两个部分。那是一条巨大的能满足人最基本最强烈最疯狂欲望而又是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肉缝。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生死祸福,适时顺逆;它给人带来虚妄的满足,也给人带来罪恶,甚至是终身都无法摆脱的罪恶。这一点对此刻年轻的象种马一般强壮的杨忠奎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杨忠奎忘乎所以的看着,心底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恶意,这股仇恨的恶意渐渐使他失去了清醒的意识……此时,还是周武翔首先发现了自己的同伴,他的惊叫使院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位不速之客。杨忠奎眼中的一团黑发突然间变成了又一朵白色的菊花。这一印象使他从内心深处永久地抛弃了宋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