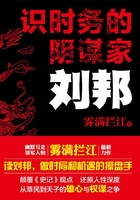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三岁失父爱。五岁失爷爷。
但我又是一个幸运者,
有二叔、三叔的培养和呵护。
叔侄亲情,永铭肺腑。
——林海水
林海水的家乡在福建省安溪县。安溪古称清溪、蓝溪,其境内多崇山峻岭,幽谷深壑,溪水大都穿行其间,最后汇入晋江入海。因山多田少,自古以来,安溪人也大多顺流而东,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对林海水这位离乡三十多年的游子来说,故乡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只有在月圆人静的时候,迢迢故乡水才会在迷蒙的梦中奔涌而来。
一、幸福的家庭
林海水1930年8月22日生于福建省安溪县蓬莱乡大墘下洋村一户侨眷家庭,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其父林景亚是马来亚的华侨。他高挑个儿,中等身材,浓眉方脸,身子骨虽不强壮,却也神采奕奕。林景亚生于1906年,孩童时曾在本村读过几年私塾,1925年,他刚满20岁,为了创建属于自己的事业,征得父母的同意,就只身出洋到马来亚吉隆坡去。先在其四叔家落脚,接着就在吉隆坡茨街经营炒面生意,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很快就站稳了脚跟。1927年,在其父林石泉的再三催促下,他返乡与邻村茂林村一位聪明贤达的姑娘刘爱结了婚。婚后不久,由于生意放不下手,他依据祖训,长子务必等弟弟、妹妹全部长大成人之后,方能分家立业,于是,他把妻子留在老家,与父母弟妹同甘共苦,又匆匆赶到吉隆坡去。当时,到东南亚去谋生,办理出入境手续非常简单,只是坐船渡海,往返要近一个月。因此,林景亚每隔两年才返乡探亲一次。其妻刘爱为人贤惠,开朗豁达,遵循传统教诲,尊敬公婆,体贴叔姑,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林海水的祖父林石泉是大墘下洋村远近闻名的人物。他精明能干,年轻时,曾学过一些拳脚,每逢正月初九,清水祖师“割火”,大墘下洋村组织了一套“八仙打”的节目,参与蓬莱乡的故事阵取乐。林石泉是“八仙打”的好把势。他学过武术,碰伤、摔伤是家常便饭。因此,他跟人学过医学的“铜人”,颇识“铜人”要领,懂得一些采摘中草药对症下药的方法,可说是药到病除。他除了种田外,还兼营贩卖鳖兔的小生意。俗语说“龟鳖蛇是兄弟”。他到溪里去捉鳖,经常会碰到蛇,有时还会被咬伤。于是他又学会了采蛇草,被毒蛇咬了,经他的草药一敷也就痊愈了。蓬莱的百姓,自古以来都把蛇视为小龙,是吉祥物,几乎很少人会加害于它,更没人敢随意捕杀,乃至吃它。有时农人们偶尔触犯了它,被咬了,总是来找林石泉要些蛇草药。久而久之,村里人凡是跌伤、撞伤或被蛇咬伤,无不前来求他采药,他都有求必应,颇受村人的好评。
林石泉共有兄弟四人,他位居老大,他们个个精明能干。其四弟早年就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是个木匠,技艺精湛,颇受当地人欢迎,生意兴隆昌盛,就在马来亚吉隆坡安家落户。从此,四弟的住所,成了故乡亲人南来北往的落脚点。林景亚、林梧桐初到马来亚吉隆坡时,都在其四叔家落脚。林石泉从小读了几年私塾,除了精心务农之外兼做鳖兔等小生意,以补家用。因此家庭经济虽不宽裕,却也不寒酸,时常还可以接济一些穷困的乡亲。林石泉膝下有三男四女,长子景亚,次子梧桐,三子景坤。那时候,教育极不发达,许多农家子弟都无缘进学堂,林石泉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十分重视儿子的文化教育。他的儿子们,每到读书年龄都送到私塾就读。他算是下洋村颇有远见的人士,凭着一把锄头一根扁担,肩负起一家人的生活和儿子们读书的重担。林景亚南渡吉隆坡谋生立足之后,有了一定的侨汇收入,他长期以来肩负的重担才得以分担。1929年冬,林景亚返乡探亲,看到社会动荡,匪患猖獗,他劝父亲不要再到漳平永春等内地去当小贩了,保命才是最重要的,家庭费用与弟弟读书的学费,他会大力支持的。林石泉也就暂时收起贩鳖兔的扁担,专心在家务农,打发时光。
1930年晚秋,马来亚吉隆坡的天气依然很炎热。在炒面店里忙了大半天的林景亚,眼见过路的行人稀少,店里的食客已离散。门口的一株橡胶树,比拳头还大的橡胶果在炽热的阳光暴晒下,发出哔哔啵啵的爆裂声,一颗颗小金橘般滚圆的橡胶籽掉落在锌板屋顶上,叮叮当当地顺着屋顶的斜坡滚落到门口的水泥汀上。林景亚觉得有点倦意,他解下围巾,拉开一把躺椅,准备歇午。“林景亚有信!”突然听到有人喊,他一骨碌从躺椅上翻起身来,接过信,打开一看,是父亲的来信,得知自己喜得一子,并要他取名,很是高兴。晚上打烊后,他特意炒了几样小菜,打了一壶酒,让店里的伙计分享他喜获麟子之乐。
夜已深了,往日做完了一天的工,洗漱完毕,躺倒便睡,今晚他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孩子应取什么名字才好呢?为此,景亚颇费心思。他觉得,儿子应该是心胸阔大、襟怀坦荡的君子,比祖辈强,比父辈壮。他曾数次乘船渡海,眼望浩瀚无边、碧波万顷的大海,时而温柔沉静,时而超绝威严,既神秘又有容,既虚怀又广博,他为大海包容并蓄宏大气魄所折服,故为儿子取名为“海水”。按故乡的辈分,“海水”是“致”字辈,故其字为“致德”。他想妥后,立即写信告诉父亲。林石泉收到儿子的来信之后,也为这个名字感到相当满意。但农村命名有个习惯,总要请相命先生摆一摆生辰八字,测测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之类。相命先生看了八字后说,孩子的命属火,而火有盛火,有弱火;弱火者,宜用木、火之类扶持;盛火者,宜用冰雪沼泽潭或江河湖海洋等化之。这孩子命属盛火,以“海水”名之甚当。景亚为孩子取名,与相命先生的说法相吻合。石泉听了,颇为满意。
二、从小康坠入穷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山高林密、交通很不发达的安溪农村,依然保持着十分典型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安溪县蓬莱乡,地处蓝溪中游,在四周高山耸立的一片相对平坦的盆地里,一条长约五公里的小溪,由西向东沿着峡谷,注入蓝溪。这里的人口,比较周边山地相对稠密一些。有十几个姓氏的宗族分布在这片盆地中的不同地域,所以全乡又分成三个庵堂,即上庵堂、中庵堂和下庵堂。
林海水的出生地大墘下洋村属于中庵堂。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分地时,蓬莱乡三庵堂人均耕地面积约一亩,中庵堂人口较多一些,人均只约七八分地而已,在二三十年代,中庵堂人口还要少些,大约人均近一亩。在那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年代,各家各户的柴、米、油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需要购买的商品就是穿、盖以及土油(煤油)、番仔火(火柴)、盐等。而衣物一般农家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的衣物,则是大的退下来给小的穿这样地延续着,所以并非要年年添加新衣服。至于盖的棉被,许多较穷困的农民,他们一生一世只在结婚时打一床被褥,生儿育女,待孩子长大就与爷爷奶奶睡,自己老了,也是如此,这样世代相续。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费用,就得靠养猪、鸡、鸭、鹅、兔等副业,卖了换钱,再买衣被,买油盐。那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到东南亚一带开辟市场,兴办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农户便纷纷南渡,到东南亚去做工或做小生意,赚了钱,便汇回家乡。于是,家里有侨汇的,日常生活的开支,便可以用侨汇支付。家里耕种的田地,饲养的家畜,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日子就过得好一些。那些没有侨汇收入的,全靠副业买卖维持生活的,日子就比较艰辛。为了摆脱窘困的生活,那些有劳动力的人家就纷纷把自己的儿女,送出国去谋生。这样靠乡亲的互帮互助,越来越多的人到南洋去落地生根。因此,蓬莱乡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家有侨汇。出去的人,有的赚多一点,成了富侨,有的赚少一点成了穷侨,但有侨总比没侨强,富侨总比穷侨好,这就是当年安溪蓬莱乡民们的实际情况。
林海水的父亲虽非富侨,却也是中等的工商业者,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谓小康人家。那时农民最怕的是两大灾祸:病与匪。那时整个农村缺医少药,从医疗条件来说,一个蓬莱乡只有三个道士在彭墟上开的三家诊所,给人看病。他们倡导的是传统的养生固本,精神慰藉,医治一些常见的疾病,遇到疑难病特别是突发病,就束手无策了。那时,华侨们带回来的药,如“斧头标”驱风油、胡文虎制造的“虎牌”万金油,算是很受欢迎的好药。华侨归来,送一罐这药,人们无不把它藏入十八层荷包里,偶尔才拿出来一用。倘若不幸得了大病,那就只好求神拜佛了,请开诊所的道士,巫医并治,一面驱鬼赶邪,稳定病人的精神,一面开些中草药治疗。许多人都因无医无药耽误了治病的良机,听天由命。
匪患,也是那时十分令人恐惧的事。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之事时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初,蓬莱刘姓的一户华侨,遭土匪抢劫,17岁女儿也被掳了去当压寨夫人,这户华侨不得不全部搬到南洋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行剿匪运动,消灭了匪首,她才获得了解放。因此,病与匪,就像两砘无形的大磨盘,平民百姓们就在这两砘大磨盘间讨生活,时刻提心吊胆,担心病灾匪祸落到自己的头上。稍有资财的人家,不得不出巨资建造高大的“炮楼”,以防匪祸。鉴于如此,1929年,林景亚从马来亚归来时,就劝其父林石泉不要再到外县跑买卖,以防不测。
林家虽是比较宽裕的侨眷家庭,但在旧社会“病与匪”的双重威胁下,生活很快从小康坠入了穷困,林海水在祖母和母亲的抚养下度过了艰辛的童年。1932年,林景亚从马来亚归来,那时林海水仅3岁,在父亲的怀抱中享受爱抚,一家人如同过节般快乐与幸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正当林景亚打点行装,准备南渡之时,突然腹痛难忍,一家人都慌了,不知所措,林景亚忍着病痛,安慰家人:“不要紧,肚子痛忍一忍就好了。”他交代父母向邻居讨点鸦片膏,服了以后略为轻松些。但其父母还是放心不下,跑到彭墟上请办诊所的道士来诊治,道士甩着拂麈,念着咒语,在病房里挥舞了一阵,画了符箓贴在床头,又开了一些药方煎服,惘然无效。当鸦片膏麻醉药效消退,林景亚的腹痛加剧,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病痛的折磨下,凄惨地走完他年仅27岁的短暂人生,留下了一个仅3岁的儿子林海水和一个尚未出世的女儿。林景亚的遽然去世,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家庭的一根顶梁柱突然折断,一家老少全都陷入无限哀伤的痛苦中。
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依然要继续为生存奔波。林海水的祖父林石泉不得不拾起那根已搁置多年的扁担,重操旧业,走村串巷,四处奔波。林海水的二叔梧桐,年仅15岁,只好辍学回家,协助祖父操持农务。往年是雇工整治农活,而今都得全盘揽在身上,犁田、耙田、插秧、除草,上山割芼,下地种菜,所有农活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学,渐渐地成为家庭的好帮手。
全家人逐渐从悲痛的阴影中走出来。1934年的一天,林石泉从永春返回家乡的半路上,与三个同乡被土匪绑架了,其中一个被放回家报信,并开出了一个数目不小的赎单,要求其家人在短时间内拿钱赎人,约定时日一过就要撕票。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使全家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家里倾尽所有,也没有多少钱,林海水的祖母、母亲、二叔等人跑断了腿,把从所有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钱汇集起来,仍与土匪的要价相距甚远。听回来的人说,土匪很凶蛮,他们说:“谷壳要榨出汁,瘦狗也要榨出四两油!没钱休想来赎人!”
面对这样凶残的土匪,村里没有一个人敢带着少许的钱去匪窝向土匪求情。林梧桐在情急之下,想亲临匪窟赎回家父,却被其母死死拉住。“难道我们眼睁睁地等待父亲被他们害死?当儿子的怎能忍心?”林梧桐无可奈何地说,其母开导他说:“如果土匪尚有人性的话,逼不出钱来,最终是会放人的;如果是一群野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点点钱,他照收不误,又白白多搭一条性命。”听了祖母的话,大家认为有道理,再等几天看看动静,听听风声再说。多日之后,众乡亲经过四处打探,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时日一到,林石泉及另一个同乡已被杀害。至于被掩埋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剿匪时,捕获一个曾经参与害死林石泉等人的匪徒,在审讯中,才获悉具体掩埋地点,林族宗亲派人从该地取回两具骸骨,依据林梧桐的意见,把它们分别葬在大墘村后山上,以供先人安息,后人祭扫凭吊。)当得知父亲已被害死的消息,林梧桐悲痛万分,同时也佩服母亲的睿智善断,这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凡事都要通盘周密地考虑,不可鲁莽,意气用事,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满盘皆输。母亲的话语,他铭记于心,成了他日后成就事业的座右铭。
林石泉被害之后,17岁的林梧桐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他在务农的同时也兼做一点花生糖,挑到集上或走村串户地叫卖。他对大哥的独苗林海水倍加关爱、呵护,不让他受到一点委屈。每次外出去卖花生糖,他总是留两包给海水吃,自己肚子即使再饿也舍不得吃。那时,社会仍然动荡不安,土匪经常入村洗劫。全村约好,如果土匪来了,下洋村的人就往码头溪树林里跑,这里人口较多,便于防卫。在林海水的记忆中,曾经好几次深更半夜里,听到有人大喊:“土匪来了!”林梧桐立即唤醒弟弟景坤,背了海水迅速往码头溪树林里跑。
在那多灾多难的岁月里,蓬莱乡经济停滞,文教落后,土匪猖獗肆虐,民不聊生。林梧桐深深感到,在故乡这片贫瘠落后的土地上,无论如何勤奋刻苦经营,发家致富都很难,白白浪费时间和青春。他萌生了到海外谋生的想法。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母亲提出,心里还担心这一家老小的生计如何安排,不料母亲不但不阻止,反而鼎力支持。她说:“孩子,你放心去吧!家里的事,我自会安排。”林梧桐整理好行装,拜别了母亲和家里的人,临行前他交代说:“妈妈,海水已快到读书的年龄了,你要教他好好读书,今后做一个于社会有用的人,我会尽力帮助的。”他像当年哥哥出洋那样,到蓬莱彭亭坐上驶往泉州的木船,踏上了南渡之路。那年正是1937年。
林梧桐出国以后,家里只剩下几个老小,如何维持好这个家?林海水祖母深感担子的沉重。海水兄妹两人,尚需有人呵护;家务虽然由她主持,尚缺欠劳力。考虑到儿子景亚已过世多年,儿媳妇尚年轻,需要重新组成一个家,她征求儿媳妇的同意之后,把景地招赘到这个家来,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担负起家中的一切农务,使景坤和海水能专心读书,同时也为林海水增添了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墘下洋村林石泉派下,又枝叶繁茂,兴旺发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