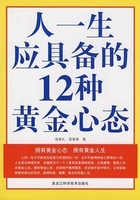这是我听来的故事,很美。
世纪60年代的一个冬天,天下着雪,一位逃难到深山的作家迷了路。夜幕降临,四望白色茫茫,作家又渴又饿又冷,又听见狼嗥。他怕得要命,隐隐约约看见远方有房子,就不顾一切奔过去,急叩门环,里面没有声息。他只得哀叫:“有人吗?有人吗?”回应他的依然是狼嗥,而且显然声在逼近。他绝望了,但他依然哀叫:“有人吗?有人吗?”他几乎就要倒地的时候,门开了。他一个趔趄闪进去,门立即又关上了。屋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仍然能听见狼嗥,但他不怕了。这时候,渴、饿、冷、累、瞌睡,都开始折磨他。他忍着,主人不吱声,他决心也不吱声。渐渐地,他看清了一个人影在晃动。眼前忽地出现了火苗,微弱的光使那个人影变得清晰,脸显然被黑布包裹着。他看见火在跟前燃烧起来,一碗热水也放到了他跟前。他立即端起碗,两手抱着,热热的水,味道真甜美呀!肚子暖和了,又闻见土豆烤熟了的香味。他从火灰里刨出一个土豆,连皮带灰囫囵着吃掉了。接连吃了十多个,吃饱了肚子,感觉好极了。那人影已经上炕躺下了。他想:“十之八九是个古怪的老头吧?这么冷的天,应该不反对我睡炕上。”顺势上了炕。炕上真暖和呀,却睡不着。狼还在嗥叫。他看见了露在被子外的脚的时候,他觉得那是女人的脚,可是他睡着了。醒来,天已大白,翻身坐起,窥视纸糊的窗外,洋洋洒洒的飞雪里,竟然立着一个妇人。一身黑的粗布衣服,掩盖不了优美的身姿。她正用雪擦脸,脸蛋立即红润了。那脸的确好看。她把洁白的雪往簸箕上掬,然后端起来。妇人走回屋时,作家立即倒下装睡。眯缝着眼看见妇人把一簸箕雪倒进锅里。奇怪的是她烧火的时候,给自己脸上又抹了把灰。作家下了炕,向妇人鞠了一躬,便朝门外走,那妇人撂过来话:“雪封山了!”妇人的声音非常甜润。他说:“谢谢!”心里头却想:“我没有打算走呀!”照着妇人刚才的动作,用雪“洗”了把脸。回屋看妇人忙活,妇人问:“会不会劈柴?”他就劈柴,妇人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他知道自己是个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对一个山村独居的年轻漂亮的妇人而言,像昨夜嗥叫不去的狼,很危险。好在他的为人他心里有底儿。所以一直坦然。共住了七天,妇人吃土豆,他吃土豆;女人做活儿,他也做活儿;妇人睡觉,他跟着睡觉。睡一个炕,不能说他纯洁得没有胡思乱想过。他事后说:“还好,我挺了过来!”七天后,妇人的丈夫回来了。原来他出山换粮,被雪阻在了山外。他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反而让媳妇做了碗面,炒了盘土豆,给作家送行。妇人向作家道歉说:“那晚我迟迟不敢开门,我怕又遇见坏人!”妇人的丈夫补充说:“两年前,我不在家,我媳妇接纳了一个投宿的人,结果……”作家抬起头,盯着妇人说:“你的脸不抹灰更美呀!”妇人立即跑出去,用雪“洗脸”,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作家把自己手腕上的表给了妇人的丈夫。那年月,对普通人来说,有一块手表已经很阔了。作家走时,那一对夫妇送了他很远。作家忽然有了冲动,很想把妇人抱一下。他当然没有。等看不见那对夫妇了,作家拥抱了路边一棵银装素裹的白杨树。四处望去,冰天雪地的深山真白、真美呀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如此呀!生活原本是洁白的,只可惜我们有些人没有好好把握自己,把本来洁白的生活给弄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