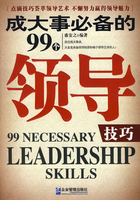我的房门坏了,母亲整日没完没了地唠叨。父亲是个怪脾气,你越唠叨,他越无动于衷,根本就没有去请木工来修缮的意思。房门坏了还不是坏了,我一教书匠,屋里除了有几本破书别无他物,我怎么也不把房门坏了看得很严重,所以也就没有理会母亲的唠叨。况且,到了晚上,坏门也能勉强关上。
过年了。二哥提了个很是漂亮很是精巧很是神气很是华贵的红里泛紫紫中带黑黑中有红的提包,从市里回来了。一进家门,父亲母亲喜不自禁。母亲高兴得把盐当成了糖,冲一杯咸得要命的盐水给二哥喝;父亲坐在火桶上,一个劲地说,回来好,回来好,回来了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好年。
我和二哥寒暄几句之后,躲进了自己的房间,随手拿起一本书,无聊地翻了起来。
吃过晚饭,二哥把他那个提包拎到我的房里。窸窸窣窣从包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一条中华烟,说是给我过年的。我执意不肯要,我说,这么昂贵的东西,我哪里消受得了。二哥笑了笑又不无调侃地说,不吃白不吃!于是,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收下了。
年过完了,二哥就要去上班。临行的头天晚上,他开始收拾行李物品。可是,任凭怎么找,那个派头十足的提包却怎样也找不到了。二哥很着急,家里人也很着急,而母亲似乎比二哥还要着急,屋里的大小角落,凡是可疑的地方,她老人家总不嫌麻烦,哪怕是爬到床铺底下,她也不嫌艰难。
二哥的包丢了,不啻于晴天霹雳,在大家庭中炸响。那几天,全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有几十号人吧,大家里里外外,进进出出,谁谁谁可疑性最大,谁谁谁可能性最小。反正,母亲的话语间,我属于可疑性最大者。我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我不猜忌其他人,我心中无愧。
小弟站出来说,过年期间,来拜年的客人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络绎不绝,说不定是哪个客人顺手牵羊给拎走了。于是乎,家人开始嘀咕哪个哪个客人的疑点,哪个哪个客人的行踪。但猜测归猜测,家人一头雾水,因为谁也没有亲见提包的去向。
第二天一早,二哥十分沮丧地离开了家。
二哥走后,此事也就渐趋平息。只是母亲,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那满脸的憔悴让人看着十分痛心。
开春了,杜鹃鸟啼催着农民该下地了。
这天,我正津津有味地跟学子们讲授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告诉学生,人生于世间,应该有点范老夫子心忧天下的情怀。正勃兴间,一位老师跑到我的教室门口,催促我去接一个长途电话,我满腹孤疑却不敢怠慢。
电话那头是一个男性严肃的声音:你是×××吗?你二哥现在在市拘留所,希望你的家人尽快来探望一下,劝告他务必配合政府的调查。
我,蒙了!来不及顾及教室里的学生,踏上自行车向家里驰去。
母亲听后,晕倒过去。
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陪母亲来到了市里。
公安人员的告知,让我们瞠目结舌。
过年期间,一个小偷趁我家的房门坏了,三更半夜偷走了二哥的提包。没想到这是一个惯偷,被公安逮着后,供出了二哥的包及包里的物件:身份证、现金、存折,等等,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摸”出了二哥这条受贿的大鱼……
我哑然了!
母亲则不停地抱恨,抱恨我坏了的房门,抱恨可恶的小偷,抱恨家人疏于防范,当然她不知道抱恨二哥,也不可能去抱恨二哥。
我很郁闷,也很纠结。坏门,提包,小偷,受贿,这一切的因果链条的诱因就是那扇坏了的门!可是,谁能坚守住自己的门不坏呢?能像范文正公那样的先贤又有几人呢?
似乎我不曾丢失什么,但我还得把门修好,修得严严实实的。
1991年5月初稿
2007年9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