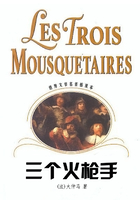医生和护士都赶过来……一看这情形,医生急了,忙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一百元递给护士:“处方在桌上,先拿药去!快!”接着,他想起什么,又走到办公桌前,又拿起笔在处方签上新开小花的用药……
大松惊叫的声音:“医生,瓶里的药怎么不滴了!”
小花的脑袋耷拉着,像睡着了,只是两滴眼泪还挂在脸上……医生的手伸过来,翻开她的眼皮……
医生的声音:“瞳孔已经放大……”
护士急匆匆拿药进来。医生的声音:“她已经用不着了。”她一愣,难过地走到小花床前,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小花的脸:“她还没来得及长大——”她“哇”的一声哭了……
这时,孩子们才明白:小花死了!抽泣声、呜咽声在急诊室回荡。
昏暗的灯光下,三屉桌一片狼藉。一个红色的某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翻开着,上贴着宋明的照片,有“外国文学系英文专业四年本科”的字样。烟灰缸里的烟头多得溢到桌子上。
一只手掐灭一个烟头,扔进烟头、烟灰四溢的烟灰缸。
另一只手拿起桌上的酒瓶。
宋明坐在桌前,双目紧盯小半瓶酒,傻笑。猛地将酒瓶对着嘴,一扬脖子,“咕嘟咕嘟”灌下去……底朝天了。
底朝天的空酒瓶。
宋明大声猛笑,将酒瓶砸向墙角,摇晃着站起身,一下跌倒在地。他仰面朝天。笑脸变成哭脸,泪水涌出,压抑的抽泣声后,失声狂哭,像野狼的干嚎……
一段黑片。
房间渐渐亮起来。静寂。宋明摊在地上,像个“大”字,睡得很沉很死。
“哒”一声轻敲门声。
宋明惊醒,警惕地坐起身,伸手抓起床下的弹簧刀。“哒、哒”两声轻敲声。
宋明依然不动,刀握得更紧,作随时起身状。
“哒、哒、哒”三声,伴着一声“咳”的轻咳。宋明丢下刀,不情愿地站起身,朝房门走去。
高打手闪身进屋,随手关上门,在一张方凳上坐下:“阿明,警方已注意到你了,老板让你南下,避避风头。”
宋明冷笑:“既然盯上了,避也无用。”
高打手冷酷地:“避不避是你个人的事,老板说不能让警方打开缺口。剁手、割耳那些事——冤有头,债有主,你站得拢,走得开;诈骗老外的事——那、那麻烦些,但警方很难拿到真凭实据,过了风头也就万事大吉。”他打开皮包,“这是你明晚南下的软卧票,这五千元你先凑合用着。这是老板重新给你办的身份证。”他一一放到桌上,一眼瞥见桌上的大学毕业文凭,拿起笑笑,“这个从此作废了。宋明这个人也从此消失在太空了。”干笑两声。
宋明一把抓过文凭,打燃火机,凑上那个自己曾苦熬苦读十六年得到的证明,烧着了。他冷冷地看着燃烧的文凭,脸上肌肉抽动了一下。
文凭燃烧着,或许是太厚,塑料封得太紧,它闷燃而冒不起火苗,浓浓的烟雾升腾……
浓浓升腾的烟,蹿得老高,蹿到天空中……
宜江市的火葬场。
活泼,清新的歌声起:
我家门口有条清清的小河
小河小河你在唱什么
你把欢乐的歌声
悄悄送进了我的心窝
……
火葬场建在一个山坡上。门前有一个很高的石级台阶。
丁丁、大松、豆豆、亮亮站在台阶上,仰望袅袅升腾的浓烟,所有的人心里空落落的,一声不吭……
浓烟很快没了,还有些许轻烟。之后,没烟了,只剩下蓝天和飘浮的白云。
丁丁自言自语地:“小花一下就没了!就像一片云,风一吹,就飘走了!”说完颓然坐到石级上。
大松呜呜哭起来。豆豆和亮亮也轻声抽泣。大家并排着坐成一排。
音乐继续,节奏徐缓……
我们急忙忙跳进小河
亮晶晶的浪花翻腾着
它像千万双小手
帮我们洗干净手脚
……
远处,是空茫茫起伏如波的远山。
排成“人”字的南归雁飞过,留下一串雁鸣。
亮亮望着雁阵,轻声说:“我想回家了。可能现在——我爸不打我妈了。”
豆豆忧郁地望着远山闷沉沉地说:“一到冬天,我爸的腰就要疼,我可以替他钻到车底下去修车……”
大松望着远处,眼里却没有东西。他竭力忍住不哭,也不说话。
沉默。
“大松!”丁丁憋不住了,“你必须回家!你们明天就走!”
大松望着丁丁,眼都没眨一下,泪水“哗”就滚落下来:“我们都走了,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怎么办……”
“没遇见你们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过啦?”丁丁突然扮出一脸的笑,“在江湖上,你们是混不出个人模狗样的!回去!回去!都回去!等大松大学毕业,到江湖上来找我,没准那会儿我已经操练成神,坐上龙头大哥的交椅了。”
“吹什么牛!”大松破涕为笑,“江湖险恶,不等你操练,不定早就被打死了。”然后很严肃地对丁丁说,“我回去后,找爸爸想办法,我妈肯定也赞成,把你送去上学。”
豆豆遗憾地:“丁丁要生在有钱人家就好了。”
丁丁自负地:“我才不依赖你爸妈哩!咦,金庸的书上怎么说的?‘富贵多纨绔,贫寒出状元。’我会管好我自己。”然后转身向火葬场鞠了一躬:“我们走啦,小花!一朵飘走的白云……”
大松、豆豆和亮亮也都鞠了一躬:“再见小花!我们会记住你!”
“我们会记住你!”的声音和歌声回荡在悠悠的白云间。
宜江火车站。
豆豆、亮亮神气地拿出票,检票员“咔”地剪完,两人进站了,然后快乐地回头跟站在门外的丁丁和大松挥手道再见。
丁丁和大松坐在车站的花坛上,沉默着。
大松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妈没问题。我尽量说服我爸,我会来找你的。”
“你上哪儿来找我?”丁丁调皮地,“我四海为家,明天我也许就广州混去了。”
“你就在宜江等我嘛!”大松固执地。
“不可能!”丁丁断然拒绝,“你一走我就离开宜江。哎,大钟都指着八点了,你快进站吧。”他拉起大松往车站的候车大厅走去。
检票口。大松递上票、检票、进站,走两步,他低头站住,少顷,猛一回头,泪流满面,望着丁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丁丁被大松的情谊感动,说话也有些哽咽,“快进去!”
“你先走!”大松说。
“你先走!”丁丁说。
“不,你走了我再走!”大松说。
丁丁咬咬牙,猛转身,说了句:“我们还会见面的!”头不回地挤开人群,瞬间就消失在人丛中。
送走完伙伴,丁丁没精打采地坐在花坛边。
来去匆匆,背包摞伞的旅客川流不息。
霓虹灯在夜空闪烁不定。爵士乐声时隐时亮,又是个不安定的夜。
丁丁懒懒地站起身,走向报亭。他捡起一张别人垫坐后扔下的报纸,蹲在报亭下,借着里面射出的灯光,细心阅读。
那是登有“寻人启事”找大松的报纸。
丁丁茫然地抬起头,报纸滑落,被一阵风吹起,翻卷着远了。
一个男人到报亭买报,趁售货员找补零钱的当口,男人叼了烟,背风打火,打火机那小火苗照亮了他的脸,他是宋明!
宋明没有了往日潇洒,一件劳动布夹克衫,一条旧牛仔裤,一双又旧又脏的旅游鞋,像个出差的工人!一顶旧遮檐帽,盖住了前额,看不见往日书生意气的脸。他拿起报纸刚转身,不小心踩了丁丁一脚。
丁丁“哎哟”一声仰起脸。
宋明“对不起”一声低下头。
双方都认出了对方。丁丁霍地站起身,十分高兴:“哥!”
宋明用一根食指竖在嘴唇上“嘘”一声,把丁丁拉到暗处,低声说:“我遇到了麻烦!”又从衣兜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丁丁,“帮我买两包‘红塔山’,在药房买一盒‘康泰克’,一盒‘交沙霉素’。我感冒了,正在发烧。”
丁丁转身欲走,宋明又拉住他:“记住药名了吗?”
丁丁笑说:“康泰克、交沙霉素。”
宋明拍拍丁丁的脑袋一下:“真聪明!”他退到黑暗深处,望了一眼车站房顶的时钟。
时间正指10点13分。
有个汉子上前借火:“哥们儿,上哪儿发财呀?”
宋明警惕地四顾,没有搭腔。发现左右两边似有人趋近,立即站起身,看看正面行人较多,便夺路欲跑。
“别动!”后面有人用刀子抵在他腰上。
汉子嘻嘻笑着:“兄弟我这几天手紧,先借俩钱使使,改日一定奉还!”
两人已经走近,四个人团团围住了他。表面上看,这五个人正在友好地聊天似的。
是抢小钱的蟊贼!宋明松了一口气:“出差人,所有的全在这儿!”他不屑地把提包丢给汉子。
“还有呢?”汉子并不看包,却用眼盯着他胸前的那些口袋。
“是些散碎银子!”宋明逐一搜出衣包里的钱,“就这些了!那包里有皮夹,你拿去吧,今天才借的出差费,两千!”
汉子伸手掏出皮夹:“够气魄!讲义气!”说着就往自己衣兜里装。
宋明喊声“慢着”,拉住汉子:“把里面的火车票给我!”
其他人劈头朝宋明打下来:“想拖延时间呀!黑灯瞎火的找什么火车票?”
汉子打量宋明:“还想出差?说明你身上还有钱!搜!”
几个人搜,确实没搜出什么。
汉子命令:“金戒指,手表全脱下来。”
宋明求饶地:“留点给我活命吧!”说完,甩开架势,左右开弓,“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你们太过分了!”
五个人打起来。都不敢吼喊,是一场沉默的肉搏。
丁丁拿着香烟,还端了一个盒饭急匆匆过来,老远看见几个黑影晃动,像是搏斗,便跑着赶来。
宋明已被掀翻在地,他的外衣被脱下来,皮带被一个人夺走,他正抓住皮带的另一头死死不放……另一个人朝他大腿就是一刀……
“警察来了!”丁丁急中生智,大喊着,“警察来了!”
几个人夺路而逃,丁丁放下饭盒,准备追赶,嘴里吼着:“逮强盗——”宋明一把捂住了丁丁的嘴。
宋明虚弱地:“警察来了,就更麻烦了。”他想站起来,腿伤了,一个趔趄又坐回地上。
“你受伤啦?”丁丁老练地撕下一块自己的衣衫,“快,脱开裤子!”他将布紧紧缠在宋明的腿上,“上医院去吧。”
“不行。”宋明勉强站起身,“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到我们窝棚去!”丁丁说,“绝对安全。”
江边的窝棚外。
深秋的太阳已没有了热度,整个河滩荒凉寂静,一派萧瑟。
河水退去,水流缓缓,两岸的树、庄稼都呈枯黄萎败状。
一件旧衣衫铺在地上,上面有一瓶酒精、消炎药粉、纱布、棉花、线和一根穿好线的针。
宋明坐在一块石头上,伸出右腿,小心地用刀子割破牛仔裤,露出受伤的大腿。
“我来!”丁丁轻轻解着昨晚替宋明包扎伤口的衣衫布,有些血已凝固,撕起来很艰难,丁丁张着嘴,像是自己疼似的“嗨,嗨”叫着。
一个大约五寸长的刀口,腿部肌肉翻裂,红呼呼张着大口,血还在往外沁出来。
宋明拿起酒精瓶,往伤口上倒酒精,冲洗伤口,之后用棉花擦干净,洒上消炎粉。“把针给我!”接过针,他提着线把针放进酒精瓶浸泡一下,“丁丁,手挤着我的腿,这样,让口子合严缝些。”
针锥进肉皮,拖出长长的线,宋明满头大汗,战战兢兢地缝合伤口。
丁丁难受地侧开自己的脸,不忍心看……
“丁丁,看着伤口!”宋明的声音严厉,“勇敢点!要像个男子汉!”
丁丁回头看一眼,难过地又侧开不看。
“丁丁,看着!”宋明更严厉的声音,“在江湖上,什么事都可能遇到,这几寸长的伤口算什么!王杰的歌怎么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宋明轻声唱着,唱着,“扑通”一声,他疼得昏死过去。
丁丁惊慌失措地站起来,不知该怎么办?伤口差一点才缝完,咬咬牙,帮哥缝,趁他现在不省人事,不知痛。于是,三下两下替宋明缝完了伤口。现在又该做什么?不行,得让哥醒过来。他可能是想起了电影里的方法,拿起一个破盆,飞杈杈跑到河边,舀来一盆水,全部淋到宋明的头上。
宋明慢慢睁开了眼睛,果然,这招真灵。
宋明坐起身,甩甩头上的水,用衣裤擦擦脸,低头一看,缝完了!他朝丁丁笑笑,把线打了个结。再洒上些消炎粉,用纱布裹上。看着坐在旁边直哆嗦的丁丁笑道:“人家兰博缝伤口的时候,前有敌人,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枪击。我幸运多了……”
崇拜之情已令丁丁饱含热泪,他情不自禁地喊道:“你是英雄!”
“英雄?”宋明自嘲地哈哈大笑,但是他愧对丁丁纯洁的目光,绝望地闭上眼睛,沉重地吐了长长一口气,“我是在案的逃犯。”
丁丁茫然失措地望着宋明。
少顷,宋明睁开眼睛,缓过气来,拍拍丁丁,换了个话题:“喂,昨天我看见你看报来着,你识字?”
“我上过小学二年级。”丁丁毕竟是孩子,说到高兴处,“我还有一本书。”钻进窝棚,拿出了《汤姆索亚历险记》,“是在金县的时候,一个老师送的。”
“呵,你还能看这种书。”宋明一扫沮丧,高兴地说,“你上过二年级?那好,你赶快去新华书店,把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语文算术全买回来。趁现在没事,我教你!”
“你教我?”丁丁瞪大了眼睛,“你读过小学?”
宋明像被戳到了痛处,冷冷地:“我读完了大学!”他一甩头,像是甩掉了过去的一切,立即作兴奋状,很快从皮夹里掏出钱,递给丁丁,“去买书,记住,从三年级到六年级!”
丁丁接过钱,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河岸的尽头。
一个月后,窝棚外。
冬天到了。河水已枯,只剩下一条窄窄的流水,人都可以踩着石头过到对岸了。
河滩光秃秃的,枯枝、败草,满目荒凉。
这是一个太阳天。阳光虽然灿烂,北风却是刺骨。
宋明已成了地地道道的乞丐,头发结成一缕一缕,垂到肩上额前,络腮胡像张飞那样张扬地伸向四面八方。他瑟瑟缩缩坐在一块石头上捉虱子。看太阳已经正顶,觉得该升火做点吃的了,便站起身。他的腿伤没好,走路依然十分艰难。他从窝棚捡起早堆在那儿的柴火,放在一个用石头搭成的“炉子”旁,又把一个缺了口的铁锅放到“炉子”上,提起一个压扁的铁桶,把水倒进锅里。之后,坐回石头上。许是穿得太单薄,他冷得一激灵。眼巴巴望着远远通向河岸的小路。
一条细细的小路伸向远处。突然,路上现出一个黑点。黑点急速变大,像是个蜗牛背着重重的壳,越变越大,渐渐清晰:那是丁丁,他背上扛了一个大包袱。
宋明站起身,高兴地向丁丁挥挥手。
丁丁的急走变成了跑步。不过这跑步一跛一跛,像是伤了腿。跑到宋明跟前,已经汗涔涔的了。
宋明先用一块黑黢黢的毛巾塞在丁丁的背上:“别感冒了。丁丁,我看你的腿有点跛,是摔的吗?”
“是摔的。”丁丁很肯定的回答,并从背回来的塑编织料袋里拿出东西,“不小心摔了一跤……”
宋明替丁丁擦脸上的汗,有些心疼地:“你头上的包,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也是摔的吗?”
“是!”
“是?”宋明扳起丁丁的头,“你那么会摔?脸也摔了?”
丁丁笑而不答,举起袋子里拿出来的衣服:“过冬的棉衣、棉裤,我们两人都有了。”突然,他蹲下去,用手卡宋明的脚,“多大号的?”
宋明即使铁石心肠也熔化了!内心的震撼无可言喻,那被毛发淹没的脸抽搐着,片刻,爆发地吼道:“我不配!我不配你这么待我!”之后,一把抱住丁丁,贼亮的眼睛涌出两行热泪。
见宋明掉泪,丁丁呆了!他在宋明的怀里小猫似的一动不动,茫然地望着宋明。少顷,他发现宋明的鬓角有一根长长的白发,便轻轻地、悄悄伸起右手,捻着那根白发,拔了!顽皮地举起,对着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