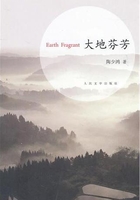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九月寒霜降,”自然是依月亮历的九月。不过这一年的九月,还相当暖,并无寒霜征象,就在中旬前几天,月亮已经很好时候,跑夜警报的,仍只是多穿一件单衣罢了。
成都已好久没有过夜袭了,大家脑里差不多已没有此种影响,黄昏生活还是那样的安定而热闹。
中旬之初的月亮,刚届黄昏,便已挂在天边,阳光越黯,月色越明。倘在去年和前年,日本攻势还正旺盛时,中国天空还只靠少数飞虎队像游魂样偶尔闪过一些影子时,每逢月夜,大家总有所准备,即如唐淑贞,也不会这样心里安闲的打扮着,准备带领儿子去看《泰山凯旋记》了。
因为高继祖不断地催促,唐老太婆只管一面骂她的外孙,却也一面帮着向嫂,比平日提前半点钟就将夜饭端上桌子。唐淑贞对于夜饭,和对于早饭一样,只算是到时候的一种点缀,不吃也可以。她顶要紧的一顿,只有午饭,不过在夜里十点后的那顿点心,是不能少的。
唐老寡妇本和成都一般人家样,是只吃两餐的,即是说上午八点前后一餐,下午三点前后一餐,天明即起,打二更就睡,不吃午点,也不吃消夜的。自从女儿大归,说是要将就高继祖读书之便,建议改为吃三顿时,她是不大悦意的,而首先附和着愿意照办的是向嫂。柴米油盐加三分之一的耗费,不说了,而且还打破了每月只依阴历的初二十六打两次牙祭的老规矩,差不多每天有点小荤,再不行,每顿总有一样猪油弄的菜;而隔不上三天,就有一顿大荤,不是清炖,便是红烧。唐淑贞说:“不常常吃点大油荤,心里不好过。妈是过了六十的人,也应该吃好点,兵荒马乱的年成,过一天,就该穿好吃好,舒舒服服快活一天,喊声日本鬼子杀来,啥都没有,还照以前那样省俭做啥子!娃儿哩,也应该吃好点,他爹说过,小娃儿的营养顶要紧,若是吃坏了,一定有碍发育,并且还多病多痛的,与其病了求医吃药,不如平日吃好些!”主人常常见荤,做饭洗衣的向嫂又哪能专吃清油小菜?何况只一个女工,多一铲少一铲也不在乎,因此,首先附和着愿意照办的也是向嫂。
这还不算,尤其使唐老寡妇起初不得不猛烈反抗,而后来才委屈答应的,就是吃牛肉一件事。据唐老寡妇说,唐家是三代人不吃牛肉的了。头一代是祖爷爷,当李短褡褡、蓝大顺造反时,由隆昌逃难上省,曾在乱兵前头,爬在一条水牛背上抢渡过河,算是水牛救了他的命,便赌咒不再吃牛肉。第二代是老公公,当外科医生时,不知要升一种什么丹药,一连三次都没升好,他若有所悟,连忙跪在药王菩萨跟前,许了愿心,不吃牛肉,那丹药才升好了。南门外二十几亩田地,就是老人家一手积起来的。第三代就是她的丈夫,本是兄弟两人,大哥不成行,十八岁上读书不成,便改而习武,弯弓射箭,练南阳刀,端大磉磴,好一把气力,入了武学的。却因操袍哥,滚到黑棚里去了,在双流地界上犯了案,从此漂流浪荡,不知生死,若果还在,差不多快八十了。因为哥哥不成行,这个小十岁的弟弟便被父母管束紧了,一直到二十岁,父母双亡,业已娶了妻后,还没有职业,还在江南馆徐老夫子那里念八股文章。民国初年,才钻进军政府,弄了个小事,后来跟着尹都督的队伍进川边去当书记官,到出来时,却弄了一身病,又染了一副大鸦片烟瘾。却是倒存了一些钱,目前这房子,就是民国五年修的,同时,唐二老爷也入了佛门,勒令一家人都不准吃牛肉,那时,唐淑贞才三四岁。
“三代人都戒过牛肉。我虽没有皈依,但我却朝过山,进过香,至今还在吃花斋。牛肉哩,二十几年没进过灶房门的,你难道记不得了?为啥要叫我犯戒?”
“你晓得啥!牛肉是顶养人的,价钱又比猪肉相因,为啥不吃?你没在牛华溪看过,那些瘟的老的水牛,还要杀来吃哩,成都这们好的黄牛肉,却不吃!前三代人不吃,是前三代人的事,怎吗管到我们第四代第五代来了!你又没进过佛门,更没道理不吃!你说老太爷皈依了,不准全家人吃,你就至今不吃,那吗,老太爷死了二十年,你为啥还活起在呢?又说,老太爷又皈依了,又不吃牛肉,该是善人啦,善人就该得善报,为啥那年又着冷炮子把脑壳打破死了呢?又说,三代人戒吃牛肉,就应该人财两发呀,为啥到现在,你只生了我这一个居孀的女?财哩,可怜啰,一年到头,都在呻呻唤唤的过日子!你说,你说,不吃牛肉,还有哪些好处?吃了,还有哪些歹处?你说,说不出,就得吃,从今天起,硬要把牛肉拿进灶房门去!”
“姑奶奶,你做啥子这们横豪!”老太婆在别的人跟前从没有这样和蔼过,依然满脸笑容说:“我告诉你,牛是多们可怜的畜生,替你们耕田种地,多苦啦!自家只是吃一把草。我们靠牛为生,还忍心去吃它的肉吗?所以佛爷说,吃牛肉的人要打入阿鼻地狱一译无间地狱,意为人在其中,没有间隙。阿鼻,梵语。——原编者注的。”
后来两句话,她自己也知道是杜撰的,哄不着人,说得并不起劲,也像念灶王经样,不大懂的句子,就囫囵过去了。这连十一岁的高继祖也呵呵地笑了。
唐淑贞的理由更正大了,攻势也更猛烈了:“你这更不对!我们吃的是黄牛肉,黄牛只是喂来吃的,就像喂猪似的,它并不耕田种地呀!耕田种地的是水牛,水牛肉并不好吃,我在牛华溪吃伤了的。”
至于打入阿鼻地狱,以及今生吃了牛肉来生准定变牛一层,已不再置议,因为对方也已没有坚强信念;而自打国战以来,人间惨事多有比吃牛肉更甚的,譬如把壮丁拉去,一群一群的饿死,一批一批的拿扁担打死来示众的事,即会有地狱和轮回,恐已难于轮到吃牛肉人的头上来。于是,二十八年来不拿牛肉进灶房的戒条,公然打破。只是老太婆起初还自己坚持着不肯吃,其后,偶尔喝几口汤,既不反胃,也没有做噩梦,久而久之,也便糊里糊涂地吃起来。
这一天的夜饭菜,恰是清炖牛肉,还是唐淑贞在安乐寺下了早市后,特为从叠湾巷转到皇城坝,在一家相熟的回民牛肉店买的。并听从白知时的说法,放了二两干枸杞下去,说比白炖的还补人。火候到了家,吃起来果然肉嫩汤浓,味道颇鲜。唐淑贞居然破例吃了两个半碗汤泡饭。老太婆和着另一碗素菜,吃得也多,临了时,还讨好似的说:“砂罐里还多,留着明早,够白先生和继祖再吃一顿了!”
刚吃完饭,高继祖就催着要走。他外婆说:“忙啥?还没有吃茶哩。”他妈说:“忙啥?我还没穿衣裳鞋子哩。”向嫂在收碗时也说:“早晨上学时,为啥不这样忙?看戏就忙啦!”向嫂和他外婆相守有十多年,也是快六十的人,所以敢于训他。
他只好到庭前去看天色。黄昏余景犹明,月亮有大半边圆。他叫说:“快黑了!蓉光六点半开,晏了,买不到票的!妈,看看你的手表!”
“才五点三刻,忙啥子?坐车子去,不过几分钟,去早了,难得等!”
“那吗,你快点穿鞋子,我去把车子喊在门口等你。”
不到三分钟,他飞跑了进来。才进大门,便一路喊道:“预行警报出来了,妈呀!妈,预行了!妈呀!”
这像满池塘蛙群里忽然投下了一块石头。两厢房十多家人全沸腾起来。好几个人一面向门外跑,一面问:“真的吗?日本鬼子当真敢来夜袭吗?”
出去的人立刻就回来证明道:“黄旗旗拿出来了,街上已有出城的人。赶快收拾!月亮好得很,敌机一定要来!城外冷,露水还一定重哩,得多穿两件衣裳。顶好把铺盖带去,晓得他妈的敌机啥时候来!”
准备跑的一派,都吵着闹着,尽量在收拾自己得起,背得起,提得起的东西。不跑的一派,还有照例要发挥一番他们相信的真理:“跑啥子哟!白天还不怕他龟子敌机,夜里更不在老子们的意下了。他妈的,前几年好凶啊!‘六一一’、‘七·二七’,百打百架敌机,也没绊着老子们的边边,现在,哼!老子们还是不跑!好!保险给你们看房子!负责没有贼娃子敢来!”
向嫂是从来就没有跑过一步。她的真理是死生有命:“若是命中注定该死,就跑出城去,还是会挨炸的。头一次猛追湾,第二次罗家碾,那些挨炸的,不都是特特从城內跑去凑数的吗?”
唐老太婆顶害怕跑警报了:岁数大,发了福,一双裹死了放不大的小脚。但是胆子又小,不能像向嫂和佃客中那些各有真理相信的人。每一次跑警报总是她顶慌张,收拾一个大包袱,得坐三回马桶。
唐淑贞,每回都是她镇定些。她并非不跑,但总要等到放了空袭警报以后,有时还必等放了紧急警报时,才跑。跑也不远,只是一短段路程,从瘟祖庙的城墙缺口一出去,一过疏散桥,就呆下了。十有九次,当解除警报的哨子一响,她头一个就回了家。或是日本飞机当真飞来上空时,要只是侦察机或战斗机,她根本不理会,不等飞机走远,她已进了城。要是轰炸机哩,她倒也同一般人样,很紧张的,甚至觉得呼吸都快停止了;但是,只须听到炸弹一爆发,她凭经验,知道日本飞机每次远袭四川,无论在何处投弹,总只是每回只投一次,从没有盘旋一周,再投二次的,投几次的也有,那一定是分几批来;她又凭经验,知道来袭成都的路程,比去炸万县、炸梁山、炸重庆的,都远得多,来一回很不容易,所以每来,总只一批,少到九架,多到一百零八架,却从没听说像重庆被炸最利害有严重、剧烈、凶猛、高强等义,同“厉害”义,但仍作“利害”。——编者注时,一天多到五批、七批的;因此,她也就放心大胆的,头一个就赶回来。回来做什么呢?十有九次,也为的过鸦片烟瘾。她感觉到一件稀奇事,就是每遇警报,她的鸦片烟总得加倍的抽,不是事前顶不住瘾,就是事后瘾发得太快。
这时,她已穿上了高跟鞋的,便连忙脱了,换上一双青咔叽生胶底操鞋,是专为跑警报穿的。并连忙将那特制的夹层毛蓝布大幅窗帷扯严,遮得一丝光一缕气都不容易漏出去。然后又连忙从那张旧式架子床的踏脚板凳抽屉中,将一副小巧玲珑的鸦片烟行头取出,连忙点烟灯,连忙烧烟膏,及至她妈和向嫂把一些要紧东西收拾成两个相当大的包袱提到她房间来时,她已抽了小指头大两颗烟泡。她儿子也自己收拾了个小包袱:两件童军服,几本教科书,还有几本《西游记》连环图,是向同学借的。都知道她的脾气,不敢催她,只静静坐着,等放空袭警报。
两厢佃客走的已差不多走完了,负责防守贼娃子的,则一群男女大小都挤在大门口,取笑打从街上走过的男女大小,院子内倒非常清静起来。
“妈,人家都走了。”高继祖怯生生的忽然说一句。
已经是第六口烟过去,唐淑贞精神渐渐勃发,脾气也好了些;仍然技巧的搓着第七个烟泡道:“莫慌!预行出来了这们久,还没放空袭,多半又不会来的了。我在安乐寺认识一个居太太,湖北人,人多好的,有说有笑,她有个娃儿在航委会做事。照她说起来,日本的空军简直不行了,不说在南洋着美国的空军打得落花流水,就在中国地方,也着打得七零八落。它现在就只陆军还行,中国还不是它敌手哩。这话一定确实,是航委会传出来的。那吗,它还有啥力量再敢到我们大后方来轰炸?所以说,大家都别着急,说不定又因了啥子误会,把美国去轰炸了前线回来的飞机,当成了日本的,乱放起警报来,像头一回样。唉!可惜白哥子没在家,要是能赶回来,倒打听得出一点真消息!”
就这时节,八达号里一般茶舞的人,也同样的很镇静,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男女舞客过分胆小,在几个美国空军接到命令,驾起吉普车赶出南门去后,便也各自溜走了。
罗罗,也就是刘易之的太太,穿着一件大红闪花缎旗袍,在百枝烛光的电灯照耀之下,比在黄昏的微弱光线里,尤为鲜艳夺目;胸襟上一大簇茉莉花球,和细长而白净的脖子上的一串假珍珠链的白光,也够调和得颇不俗气。和女主人丁丁比起来,就是那几个来自万里,很少与中国女性接触的美国大兵,也很容易的在几眼之下,便分出了前一个是社交老手,而后一个只是才学摩登的少妇。
她此时正凝精聚神的坐在靠壁一张皮沙发上,同着嵇科长的太太在密谈什么。当马为富走去把电灯一扭开时,两位太太都不觉一震,各自拿手背把眼睛一遮,同声说:“光线太强了!”
陈莉华正站在角落上一只放收音机的条桌旁,虽在收听本市广播电台那位相熟的女广播员以流利的北平腔,报告着今天各报已经登过的中央社的刻板新闻:“高田圩敌昨向桃子隘进扑,被我军击退,敌人损失甚众,有回窜势态。”同时,也听见了两位太太的话,便向正抽着纸烟在与龙子才站着说话的陈登云招了招手。
陈登云笔挺的穿了件“斯摩金”,打的也是黑领结,下面配了条细条纹薄呢裤,算是今天茶舞会里很得体的一身装束。但嵇科长却向费副官私下挖苦他不懂时尚,不应该在不拘礼节,活泼天真的美国朋友跟前,摆出十九世纪的英国绅士派来。
费副官老是那身黄呢中山服,笑说:“我们老粗,又没留过洋,连上海都没去过的,倒不懂这些。我只晓得穿上西装就摩登了!哈哈!”
“你不懂,我懂。你光看今天那几位外宾,是不是都穿的夏威夷衬衫来的,拿老规矩来说,是不该的;比如别人请你参与啥子大宴会,你连长衫都不穿,只穿了一件汗衣去。但是美国人就是这点可爱,以前的啥子老规矩一概打倒,在交际上一味的率真,从没见过面的人,一谈上路,立刻就像弟兄样亲热,并不讲那虚伪的礼貌。你只看报上载的海尔赛海军大将第二次回到他旗舰上来,头一个命令,就是取消领带。穿西装不拴领带,你想这是如何的豪放,英国人办不到,所以在这次大战里,英国的海军就真蹩脚!”
陈登云看见三小姐在招手,立刻就走了过去:“有啥事吗?”
“一定又是丁丁的主意了。小马咋个连这件事也不经心,他也曾交际过的呀!”
“到底为的啥?我不懂你的意思。”
她不由抿着嘴皮一笑:“你也同小马一样了,还要我说吗?”
她又拿眼朝电灯一看,光线果然太强,射得两眼生花。
她今天穿的一件元青花缎旗袍,只在前裾的右角和后裾的左角,绽了两朵朱红花和两片翠绿叶,都是刮绒的,素净而俏丽,和罗罗的打扮恰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并且把那丰腴的身体和颈项,陪衬得更其肉感起来。今天在八九个女客中间,只她与罗罗最为外宾注意,每逢扩音器把音乐片子一送出后,总有两三个高大强壮的美国人一同来要求她们两个跳舞,好几次没有停歇过。她的舞步也还稳当,不过赶不上罗罗来得轻盈,这是常不常跳的关系,倒没有什么,而使她略不高兴,认为不如人的,就是罗罗能够说英国话,唱英文歌,而她却是哑巴。好在今天由费副官邀来昨下午茶舞的几个空军,都能强勉说几句中国话,差能略略达意,不过有一个学了些下流话,在相搂而舞时,贴着耳朵说了句:“你是乖乖!”她真没办法去回答他,只好拿眼睛白了他一眼,又摇一摇头,同时找一句简单的中国话回答他:“说得不好!这是顶不好的话!”他好像懂了,也摇摇头,又笑一笑。但是那只搂着腰肢的有毛的粗膀膊更其紧了紧,而贴着耳朵仍是那句:“乖乖!你是乖乖!”就这时候,得了消息说,日本飞机有到四川的模样。一般正搂着舞伴的美国兵遂都立刻聚在一处,说了两句话,便匆匆的给每一人握一握手,喊着“古拜”走了。
因了她的眼风,陈登云才懂了她的意思,连忙点点头道:“好亮的灯!哦!是的,应该换成绿色的电泡。我已跟小马说过,并且我亲眼看见他预备了的,何以又不改换?”
“我想,一定是丁丁的主意!”
“不见得罢?”
“你怎么知道不见得?想到有这们多客,又有洋人,若果不把电灯弄得雪亮,不怕人家说她点惯了清油灯吗?”
陈登云一笑走开,跟着便是老杨来把灯泡换了。立刻这个舞厅里——此刻可以说是客厅里的光线,就柔和了,恰与庭中的月色花荫配合成一片优美的境地。
嵇太太忽然诧异道:“谁叫人把电灯泡换了的?真聪明!”
嵇太太是三十年纪,一个正在发福的少妇。从面孔到一双脚,从头发的电烫样式到鞋子后跟,无一处不显得四平八稳,没一点指得出瑕疵,但也没一点引人兴趣的特征。态度也大方平淡,好像熟透的一颗水蜜桃,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她是出身大家,而又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交际场中,是那样的蕴藉文雅,却与任何人都无过分亲热之表示。也因此之故,她虽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过于文爱娜,比起罗罗的那种洋泾浜英语来,更不知高明到哪里,可是一般美国空军人员,总把她当成有学问的老阿姐,也一样同她跳舞,也一样同她谈天,甚至有时也一样的邀她坐吉普车兜风,或到几处空军营去出席什么联欢会,而到底是不敢越份,而到底只算是忘形的朋友。她就是这点强,就是这点才把一个自命风流浪漫的嵇科长抓住了,使他只敢偷偷摸摸,而不敢光明正大的胡搞,并且还不惜把一面惧内的挡箭牌挂在口上,一点不怕人笑。
罗罗望着她一笑道:“我晓得这个人,但是我不说。”
“唔!不劳烦你说!”嵇太太也聪明地一笑:“厅子里只这几个人:先生们都是心粗气浮的,想不到;女主人家进去了,没出来;居太太哩,是新认识的客,不会管到这上头;那吗,还有什么人呢?自然用不着你说了!”
“噫!你果真是条理分明,无怪嵇科长和纳尔逊中校那们佩服你!”罗罗顿了顿,又道:“若果你当真去做起官来,恐怕许多男子们都要吓死了!”
“岂但我?就是你,就是陈三小姐,就是坐在那边的居太太,哪个不会把些笨男人吓死呢?如其都做了官,其实,告诉你,做官是顶容易的事,比我们剪裁一件衣料,烧一样寻常菜,还容易得多!你莫把做官看得太神秘;我告诉你一桩故事,你就明白啦!”
丁素英又匀了一次粉,又换了一件新衣服,嘻哈打笑的挽着她的马经理,走到舞厅中间,像宣布开会样,把两只短而胖的手,拙笨的几拍,等到众人都注意的看着她时,她却红起脸,推着她的马经理:“你说!你说!”
“好的,我说!哥子们,嫂嫂们,拙荆旧时对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叫拙荆,出自《列女传》,说梁鸿的妻子孟光“常荆钗布裙”。——原编者注的意思: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开办的舞会,请帖上虽写的茶点招待,其实是预备了一点酒菜。原先因为有外宾在场,安排是中餐西吃。而今外宾既不在场,到底我们还是西吃的好呢?还是”
几个清刚而低沉的男高音、男中音:“西吃!我主张西式!还是西吃的好!”
只有陪着居太太在密谈的那个正走红运的龙子才队长没有提出主张,而四个女客,也只是笑,不表示意见。
“不行呀!”马为富屈着指头算算道:“男女来宾九人,主张西吃的只有四人,都是男宾,这咋行呢?”
陈莉华笑道:“又不是啥子军国会议,说不上表决,更说不上多数少数。我看,客随主便罢!”
嵇太太跟着说:“对的!我赞成陈三姐的说法!”
嵇科长向罗罗挤了个眼睛道:“两位女宾的作风真够圆滑,可以当得外交部长了。”
“我才在说嵇大嫂若做了官,头一个就会把你吓死!”
丁素英遂向她的马经理道:“那吗,我们还是西吃罢。”
杨世兴慌忙走来,向众人说:“先生伙!警报扯响了!你们的车夫问啷格办?”
居太太首先站了起来:“多谢你家!我要回去了!”
“莫要走!”龙子才也站起来,无意的伸着两手一拦:“你那条街正是军事机关!”
费副官挺着胸膛,很像一个负有全责的大军人,挥着两手叫道:“请雅静!等我们听一听!”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是空袭警报,没关系!等我打电话问问看。”
陈莉华已把收音机扭开。
“注意!注意!敌机三批,由鄂西基地西飞!敌机三批,由鄂西基地西飞!已过万县!已过万县!仍向前进!五分钟后再报告!”
陈登云立刻走过去说:“我们回‘归兮山庄’去罢!”
刘易之毕竟年轻,比他太太还沉不住气,向陈登云说:“我们也到你那儿去!”
汪会计领着男女老小一大群,从舞厅门外走过,叽里呱啦的,很像才散了戏的模样。
嵇科长也有点慌了,对他太太说:“我们也到陈三姐那里去,好不好?”
他太太还是稳坐不动地说:“刚才你没听见毛立克上尉说吗?他们决不容许日本飞机进入市空的,现在不比从前,你还怕吗?”
罗罗也才恍然若悟,连连点着她那美丽的头道:“我可证明,密斯特毛立克确是这们说过!那,我们还怕什么!我们有盟军保护!莫走莫走,大家都别走,陈五哥、陈三姐、嵇大嫂、嵇科长,都别走!啊!还有居太太、龙队长,都别走!当真,密斯特毛立克说过,唔!华生中尉也像说过的,不过我没听清楚,总之,有盟军保护!日本飞机”
“注意!注意!敌机三批由鄂西基地西飞!已过梁山!已过梁山!敌机三批继续西进!敌机三批继续西进!成都平原月色甚好!月色甚好!市民们赶快向四郊疏散!市民们赶快向四郊疏散!”
罗罗刚走去把收音机关了后,费副官也打了电话回来。
“真该枪毙,那伙接线生!偏是紧急时候,偏跟你顽皮,喊了老半天,才打通!”
小马问:“咋个的?说是三批敌机已过梁山,到底一批好多架嘛?”
“没关系,没关系,我刚才问了防空部,说是一批只有三架,还是两个马达的轻轰炸机,看光景是扰乱性质,发生不出大作用的。并且我们盟军的截击飞机,已向遂宁那带飞去了,大约不会让它窜入市空。不过,马经理,灯火却要灭尽,那倒开不得玩笑!”
小马登时就把舞厅的电灯关了,并亲自到前前后后去检查电灯关完了不曾。
丁素英大声说道:“恁早就把电灯关完了!我们咋个消夜呢?”
几个清脆的女高音:“我们都还不饿,等解除了再吃罢!”
嵇科长走到外边阶沿上说:“这们好的月亮!大家不如到外面来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