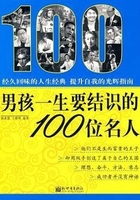为此,在“四书”结业后,讲授《诗经》、《左传》、《庄子》、《纲鉴易知录》之前,首先讲授了《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写诗。他很重视对句,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反复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讲授李氏的《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诵读声。
他还给我们讲,对句讲究虚字、实字。按传统说法,名词算实字,一部分动词、形容词也可以算是实字,其余的就算虚字。这种界限往往不是很分明的。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先生还常常从古诗中找出一个成句,让我们给配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对出上联。我面对窗前场景,想了一句“衰桐摇败叶”,先生看了说,也还可以,顺手翻开《杜诗镜余》,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秋柄,一个响晴天,先生领我们到草场野游,回来后,让以《巧云》为题,写一篇五百字的短文。我把卷子交上去,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正值旧历八月初一,民间有“抢秋膘”的习俗,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饭。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原来,塾师批改作文,都用墨笔勾勒,一般句子每句一圈,较好的每句双圈,更好的全句连圈,特好的圈上套圈。对欠妥的句子,勾掉或者改写,凡文理不通、文不对题的都用墨笔抹去。所以,卷子发还,只要看圈圈多少和有无涂抹,就知道作文成绩如何了。
先生年轻时就吸鸦片烟久吸成瘾,每到烟瘾上来之后,荼饭无心,精神颓靡,甚至涕泗交流,只好躺下来点上烟灯,赶紧吸上几口,才能振作起精神来。后来,鸦片烟也觉得不够劲了,便换上由鸦片里提炼出来的吗啡;吸了两年,又觉得不过瘾了,只好注射吗啡的醋酸基衍生物一海洛因(俗称“白面”),每天一次。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行草,凡是前来求他写字的,都带上几支“白面”作为赆礼。只要扎上一针,立刻神采飞扬,连着写上十张八张,也没有问题而且笔酣墨饱,力透纸背。
由于资金有限,他每次只能买回四支、五支。这样,隔上几天就得去一次高升镇。“阎王不在,小鬼翻天。”他一出门,我们就可以放胆地闹学了,这真是快活无比的日子。这天,我眼见着先生夹个包揪走出去了,便急急忙忙把我和嘎子哥的书桌摞在一起,然后爬到上面去,算是登上了皇位,让嘎子哥给我叩头请安,三呼万岁。他便跪拜如仪,喊着“谢主隆恩”。我也洋洋自得地一挥手,刚说出“爱卿平身”,就见老先生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原来,他忘记了带钱,走出二里地才忽然想起。往屋一进,正赶上我“大闹天宫”,据说,当时他也只是说了一句:“嚯!小日子又起来了。”可是,却吓得我冷汗淋淋,后来,足足病倒了三个多月。
病好了以后,略通医道的魔怔叔说我脸色苍白,还没有恢复元气。嘎子哥听了,便悄悄地带我去“滋补”,要烧小鸡给我吃。他家后院有块韭菜地,几只小鸡正低着头在里面找虫子吃。他从后面走过去,冷不防腾起一脚,小鸡就糊里糊涂地命归了西天。弄到几只以后,拿到一个壕沟里,逐个糊上黄泥,再捡一些干树枝来烧烤。熟了之后摔掉泥巴,外焦里嫩的小烧鸡就成了我们丰盛的美餐。
这类事干了几次,终于被看青的“大个子”叔叔(实际是个矬子)发觉了,告诉了魔怔叔,为此嘎子哥遭到了一通毒打。这样一来,我们便和“大个子”结下了怨仇,决心实行严厉的报复。那天,我们趁老先生上街,两人跑到村外一个烂泥塘边,脱光了衣裳,滚进泥坑里,把脸上、身上连同带去的棍棒通通涂满了黑泥,然后,一头钻进青纱帐,拣“大个子”必经的毛毛道,两个黑孩拄着黝黑的棍棒分左右两边站定。只见他漫不经心地低头走了过来,嘴里还哼着小曲。我们突然大吼一声站住!拿出买路钱!”竟把他吓得打了个大趔趄。
与这类带有报复性质的恶作剧不同,有时候儿童淘气,纯粹出于顽皮的天性,可以说,没有任何前因后果。住在我家西邻的伯母,平时待我们很好,桃子熟了,常常往我们小手里塞上一两个。我们对她的唯一不满,就是她一天不住嘴,老是“嘞嘞嘞”,一件事叨咕起来没完,怪烦人的。
这天,我发现她家的南瓜蔓爬到了我们这面墙上,上面结了一个小盆大的南瓜,便和嘎子哥一起给它动了“手术”:先在上面切一个四四方方的开口,然后用匙子把里面的瓜瓤掏出来,填充进去一些大粪,再用那个四方块把窟窿堵上。经过我们观察,认为“刀口”已经长好了,便把它翻墙送过伯母那面去。隔上一些天我们就要找个事由过去望一望,发现它已经长到脸盆一般大了,颜色也由青翠转作深黑,知道过不了多久,伯母就会用它烛鱼吃了。
一天,见到伯母拎了几条河鱼进了院子,随后,又把南瓜摘了下来,搬回屋里。估摸着将要动刀切了,我和嘎子哥立刻赶到现场去看“好戏”。结果,一刀下去,粪汤“哗哗”地流满了灶台,还散发着臭味。伯母一赌气,就把整个南瓜扔到了猪圈里。院里院外骂个不停,从正午一直骂到日头栽西。我们却早已蹦着跳着,“得胜还朝”了。
在外面跑饿了,我和嘎子哥就回到他家菜园子里啃茄子吃。我们不是站在地上,把茄子摘下来一个一个吃掉,而是平身仰卧在垄沟里,一点点地往前移动,用嘴从茄秧下面去咬那最甜最嫩的小茄苞儿。面对着茄秧上那些半截的小茄子,魔怔叔和园工竟猜不出这是受了什么灾害。直到半个月以后,我们在那里故伎重演,当场被园工抓住,才揭开了谜底。告到魔怔叔那里,罚我们把半截茄子全部摘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吃掉,直弄得我们肠胃胀痛,下巴酸疼,暗中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类“蚀本生意”了。
但是,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顽童是没有记忆的。没过多久,我们又“作祸”了,而且,情节更为恶劣。那天,我的书包里装了一把炒熟的黄豆,放学后忘记带回家去,第二天发现书包被老鼠咬个大窟窿。这是妈妈花了两天工夫精心缝制的,我心疼得流出了眼泪。嘎子哥说,别哭别哭,看我怎样收拾它们。
他的本事也真大,不知道怎么弄来的,一只大老鼠已经被关进小箱子里。晚上自习结束,他引我到马棚里,就着风灯的亮光,用一块麻布罩住老鼠的脑袋,让我用手掐住,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半把生黄豆一粒粒塞进老鼠的肛门里,再用针线缝死,然后放出门外。当夜院子里发生了一场群鼠大战。原来,那个老鼠因腹中黄豆膨胀而感到干渴,就拼命喝水,水喝得越多就越是膨胀,憋得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发疯似地追咬它的同类,结果,当场就有三只老鼠送了命。
私塾不放寒假,理由是“心似平原野马,易放难收”。但进了腊月门之后,课业安排相对地宽松一些。因为这段时间没有背诵,晚自习也取消了,我便天天晚上去逛灯会,看高跷。但有时,先生还要拉我们命题作诗,或者临机对句,也是很难应付的。
古制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日止。”意思是,官府衙门到了腊月(嘉平月)二十前后便要封存印信,停止办公,临时设置灯官,由民众中产生,俗称“灯笼太守”,管理民事。到了正月下旬,官府衙门印信启封,灯官即自行解职。乡村结合本地的实际,对这种习俗作了变通处理。灯官的差使尽管能够增加一些收入,但旧时有个说法当了灯官的要倒霉三年”,因此,一般的都不愿意干。村上只好说服动员那种平时懒惰、生活无着的“二混子”来担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计中的困难。
到了旧历除夕,在秧歌队的簇拥下,灯官身着知府戏装,头戴乌纱亮翅,端坐于八抬大轿之中,前有健夫摇旗喝道,两旁有青红皂隶护卫,闹闹嚷嚷地到全村各地巡察。遇有哪家灯笼不明,道路不平或者随地倒置垃圾,“大老爷”便走出官轿,当众训斥、罚款;街头实在找不着岔子,就要走进院子,故意在冰雪上滑溜一下,然后,就以“闪了老爷的腰”为名罚一笔款。
这笔钱,一般用来支付春节期间各项活动开支,同时给予灯官这类特困户以适当的补助。被罚的对象多为殷实富户,农村所谓“土财主”者,往往都是事先物色好了对象,到时候找个名堂,走走过场。这样,既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又带有鲜明的娱乐性质,颇受民众欢迎。
每当灯官出巡,人们都前呼后拥,几乎是全村出动。这天晚上刘先生也拄着拐杖出来,随着队伍观看。第二天,就叫我们以此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和一首即事诗。嘎子哥写了什么,忘记了;我写的散文,名曰《“灯笼太守”记》(全文附后),诗是一首七绝: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先生看过文章,在题目旁边写了“清顺可读”四个字;对这首七绝,好像也说了点什么,记不清楚了。散学时,先生把这两篇文字交还给我,让带回家去,给父亲看。
记得还有一次,那天是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外面锣鼓声越来越近,知道是高跷队(俗称“高脚子”)过来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共枕一条三尺长的枕头,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吸着鸦片烟。由于零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荼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了一句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歌鼓喧阒,窗外脚高高脚脚;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我正愁着找不出恰当的对句,憋得额头渗出了汗津,忽然见到魔怔叔把脑袋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便灵机一动,对出了下句:
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
魔怔叔与塾师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临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后来从事诗词创作获益颇深。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溶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而两位老师帮我造就的好学不倦与迷恋自然的情结,则久而益坚,弥足珍视。
“少年子弟江湖老”。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轻脆的风铃声,仿怫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边。马缨一风铃,风铃一马缨,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