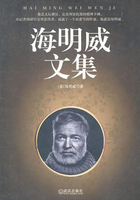当天晚上,乐人丰就去了孙跃文家里。
老市长在春城宾馆设宴招待外宾,还没有回家。孙跃文妈妈昨天去了广州,为市府机关管理局购买进口汽车。家中只有孙跃文同老阿姨,正是谈话的好机会。如果老市长或是他的老伴有一个人在家,定会向乐人丰提出一连串的质问,叫他难于回答。听说两位老人都不在家,乐人丰的身心一下子放松了。
今天的孙跃文同那天去公安局的孙跃文简直判若两人。
他好像把那件不愉快的事忘掉了,对乐人丰同过去一样的热情洋溢,亲昵而真诚,仿佛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龃龉,更看不出由于龃龉而造成思想和感情上的裂痕。
“喝点什么饮料?对雀巢有兴趣吗?”进了会客室,孙跃文问乐人丰。
“行嘛,放浓点。”乐人丰说着,朝三人沙发坐下去,斜倚在搁手上。
“你不怕失眠?”孙跃文说。
“时间总是不够用,要是失眠那才好呢。糟糕的是我从不失眠。”乐人丰揶揄地说。
孙跃文替乐人丰冲了咖啡,他自己喝百事可乐,那“喷”
的一声,把乐人丰吓了一跳。
“那天我的火气太大了,不该弄得你下不了台。”孙跃文喝了口饮料,颇为遗憾地说。
“我个人下不了台倒无所谓,只是被你那么一闹,把我们的工作弄得够被动的了。”乐人丰也直率地说。
“更确切地说,把你们弄得够被动的并不是我,而是别人。”孙跃文言简意赅地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
“你呀,又在硬装榫头了。”乐人丰温和地嗔怪道,仿佛拿他奈何不得似地摇摇头。
“我那天的火气不是毫无由来的。”孙跃文温文尔雅地说,“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造成我与美术界的某些人结下了不解之冤,一遇到政治气候变化,他们就想图谋我。现在市府大院发现了一具女尸,你又生出花样要为死者画像,这一下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于是,他们就借用你的箭,来射我这个靶子。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样的事落在你身上,你能不生气吗?”
“你同谁结下了不解之冤?”乐人丰见他讲得振振有词,不禁脱口而出。
“多着呢。罗琴君便是其中一个。我同她曾经恋爱过的事,你不会不知道吧?”孙跃文说得极随便,极自然,决不会让你留下别出深意的印象。
乐人丰暗暗地吃了一惊。心想,死者的肖像画出于罗琴君之手的事,他至今守口如瓶,连刑侦处也没人知道,而孙跃文的话里有着明显的暗示,说明他已经知道了死者的肖像画的来龙去脉了,岂不咄咄怪事?为了不让对方看出他内心的吃惊,他随即回答道:
“曾经听说过,但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谈崩了。是她把你蹬掉了吗?”
“要是她把我蹬了,就不会记恨于我了。”
“是你把她蹬了?”
“是的。不过,更确切地说,是我父母坚决反对的结果。”
乐人丰本想问他在这个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但他连忙把冲到唇边的话用舌头尖裹回肚里去了。这是万万问不得的。他同罗琴君由于幼稚无知所犯下的过失,又出于幼稚无知将此事告诉了孙跃文,随着时间的消逝,孙跃文也许淡忘了,如果他一再追问,岂不把这条已经模糊了的线条反而描绘得清晰而突出了吗?必须更换话题了。
“跃文,那幅画像,完全是我根据死者的牙齿想象出来的,不料正好与你的女朋友面容接近,这是一种巧合,希望你不要乱犯猜疑。”乐人丰一方面作着解释,一方面趁机把谈话引入正题。
“但愿如此。”孙跃文大度地说。
“跃文,请你能够满足我一个要求。”乐人丰字斟句酌地说。“由于这件事弄得家喻户晓,我们必须见到你的女朋友,才好向群众宣布这纯粹是巧合。”
“说来说去你们还是怀疑死者是我的女朋友了?”孙跃文没有动气,声音也很平和。
“不是怀疑,而是为了澄清。”乐人丰说。
“倘若我不说呢?”
“我相信你会说的。你总不愿意让真正的杀人犯逍遥法外吧?”
这对童年时代的好朋友虽然此时此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语意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但他们谈话的方式始终是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着,宛若这会儿吹来的一阵春风,蓝色的绸窗帷轻轻地摆动着,给人一种极其柔和恬适的感觉。
“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将我女朋友告诉你们,但你必须也要告诉我,死者的肖像画出自谁人之手?”孙跃文说。
“请你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乐人丰心里不高兴,觉得他不该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为了顺利地达到此来的目的,他没有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因为我们有一条规定,对于请来为我们工作的画家,绝不许可让办案者以外的任何人知道。这是纪律啊!”
“既然这样,那我也只好无可奉告了。”孙跃文仍然微笑着说,仿佛是在开玩笑,只有从他眼睛里闪动的执拗的光芒,才可以看出他说得很认真,谁也休想叫他改变主意。
这天夜里,乐人丰失眠了。当然不是浓咖啡的作用。而是今晚同孙跃文的交谈之后使他禁不住思潮汹涌,联想翩翩。
乐人丰对待朋友是质朴的、宽厚的,从不以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而高人一等。对待生活中的弱者,他的襟怀里渗透了一种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而另一方面,他对某些特别能够生存、咄咄逼人而又满不在乎的“强者”,却无法掩饰他的内在反感。虽然,他并不为这种情感上的抵触所拘囿,在理智上他始终是十分清醒的——比如今天晚上的谈话中,孙跃文一再暗示他已知道死者的肖像画出自何人的手笔,却故意引而不发,不予说穿,在“诬陷”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便不得不引起乐人丰怀疑,孙跃文明显是在恫吓,向他施加压力,企图把他吓退。如果孙跃文心中没有鬼,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乐人丰心里这样想。于是,他对孙跃文的怀疑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
然而,想到这里,他的思绪猛然来了个急转弯:他的性格,孙跃文应当很了解,如果孙跃文当真是杀人犯,他决不会徇私情,也决不会由于顾忌自己与罗琴君的关系被披露而背叛自己的信念。倘若孙跃文企图用这件事要挟他桐吓他,那只能是欲盖弥彰。孙跃文是聪明人,不会这么蠢。是不是自己神经过敏?
但是半个月以后,案情出乎乐人丰意料地发展,他的犹疑和善良的愿望却被一扫而空。
一天,乐人丰被叫到局长室。刑侦处一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已在那里,乐人丰到达时,应克强正拎着暖瓶往余福庆茶杯里倒水,说明他们在这里坐了好久了。柴副局长手指间夹着一支牡丹烟,在屋里低头踱步,眉宇间闪露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神情,像兴奋,又像焦虑,一时间,使他成了矛盾的混合体。
“碰到什么棘手的问题了?”乐人丰不敢惊扰柴副局长的沉思,悄悄地在沙发上坐下,压低声音问身边的余福庆和应克强。
乐人丰的声音像隔墙传来似的胆还是让柴之坚听到了。
他从沉思中抬起头来,敛去眉宇间的焦虑神情,在乐人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去,说:“你判断错了。不是碰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而是案子有了转机,案情进一步明朗化了。”他把话顿住,吸了口烟,转向余福庆说:“向人丰说说吧。”
“我同克强去过处长室,你不在,我们便直接来向柴局长汇报了。”余福庆说话做事唯恐有失,生怕别人误解他不把新处长放在眼内,没有忘了在汇报之前先作这番解释。“情况是这样的:春城市和清风口之间,有个石门水库,水库又大又深,终年不干。水库上面有一片果园,看守果园的是一位姓柳的中年农民,我们访问了他。他向我们反映了如下的情况:三年前盛夏的一天傍晚,他看到一辆黑色小汽车停在水库的堤坝上,有个男人在黑乎乎的物体上抽动绳索,他以为是城里人趁天黑来这儿偷偷地捞虾捕鱼,便冲着汽车方向吆喊着奔了过去。他的喊声惊动了对方,那男人慌忙将那黑呼呼的东西抱上了车。这时候,他方才看清楚对方搬动的根本不是鱼网而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当他赶到水库堤坝时,汽车已经开走了,只留下一条粗麻绳和几块大石头。他突然起了疑心,那男的莫不是要将女的坠到水库里去呀?!他越想越怀疑,立即向镇派出所作了报告。这是派出所当时做的记录。”
余福庆刹住话头,从公文包里抽出两张纸头递给了乐人丰。
乐人丰看完从派出所抄回的报案记录,问余福庆:“能够肯定是孙跃文吗?”
柴之坚拿起茶几上一支钢笔,摇摇:“这是孙跃文留在水库上的证物。”
乐人丰接过钢笔一看,笔杆上果然刻有“跃文”二字。
立时,他眸子里闪烁着明暗交替的光亮,接着眉根拧成了一个结,不知是兴奋还是惊疑,眼瞳里盛满了特异的感情。
余福庆朝愣着神的乐人丰笑道:“按你过去所说,市府大院是第三现场,那么,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都找到了,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应克强开腔了,他本想说,现在就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话到唇边变成了这样:“人丰,现在就看你的了。如果你对画像很自信很有把握,我就起草报告,要求批准拘留孙跃文了。”
乐人丰当然看出应克强是在将他的军,但他一向性情温柔脾气极好,绝不流露这种洞察,平和地说:“画像只能作为侦察工作的参考,并不能作为破案的依据。”还有一句留在心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应克强说:“你这样模棱两可,事情就难办了。”
柴之坚从沙发上坐直身体,将半截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眼光流星般地在三位部下脸上一掠而过,一字一顿地说道:
“请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孙跃文不是市长的儿子,不是你们其中某人的朋友,而是一般平民百姓,案情发展到这一步,你们当提出怎样的意见?”
在坐的三个人心里都明白,与其说柴副局长在问他们,还不如说他是在问自己更为确切;与其说他的话里包含着嗔责之意,毋宁说他的话里更多的却是鼓励的成分,既鼓励部下,也鼓励他自己。只是三个人都不愿流露这种洞察而已。
乐人丰还是那么冷静,那么稳重地说道:“根据死者牙齿画像,我曾经做过试验但在案件中实际运用这还是头一次。说实在话,像画出后,被孙跃文那么一闹,我的自信心一度发生了动摇,甚至曾经产生了偃旗息鼓的念头。后来通过清风口的调查,以及那天晚上同孙跃文单独谈话后,我的自信心又猛然从心底崛起,并且十分执着。现在又加上石门水库的情况,我虽不敢完全肯定,但敢于这样说,市府大院的那具女尸,十有八九正是孙跃文的那个女朋友。”
余福庆听后,频频点头。
应克强未动声色,仍持保留态度。
柴之坚起身,开始在屋里踱步,神色十分严肃。他一向恼火别人打断他的思索。他也从不打断部下的思索。因而谁也不敢说话。
屋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这沉默自然要柴之坚自己来打破。他仿佛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没有让沉默持续多久,便踱到应克强和余福庆面前,决然地说道:
“你们马上回去写一份案情综合报告,明确地提出对孙跃文拘留审查,明天一上班交给我,我去向老市长当面汇报!”
千锤敲鼓,一锤定音。应克强虽然仍有疑议,见局长决心已下,不便再说什么了。
乐人丰同应克强他们一起离开了局长室。回到处长室时,他心里滋生了一种莫名的烦躁,同时又有一种潜意识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