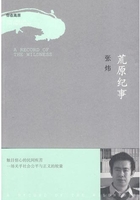甜吃就比较适合新鲜热馒头,一面看网络下载的电影,一面下意识地揪下一小块馒头,不是直接送到嘴里,而是蘸一蘸炼奶再吃。我看完一部电影,基本可以蘸完小半碗炼奶,吃完一个到一个半大馒头,吃到几乎不便动弹的程度。有时候,在炼奶短缺的时候,我以蜜糖替代,还要甜到骨髓里。
馒头这种元凶就算了,难不成还捉人家归案?
至于肥胖,我想起有人说过,我胖起来只是想在你的心里多占一点地方,我重起来只是想在你的心里多占一点分量。这话像是爱情通知,更像是肥胖借口。
我,两样都占了。
肉里风月
本来把题目取做《肉里虫二》,但虫二显然不如风月更直抵人心。
就好像前凸后翘的比基尼女郎,当然比粗服乱头的灶下厨娘要更吸引眼球。而一盘红亮冒油的回锅肉,当然也远比那碟姿色平庸的白水煮肉更撩人口水。
风月是个暧昧的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青山白马逐风月,一骑红尘走天涯。古人把风月婉称为虫二,他们吃饱等饿,闲来无事,就把 “風”(风)字和“月”字去掉边框,风月就成了虫二,取其风月无边之意。既然处处有风月,无事不风月,那么肉里风月也就说得过去了。
最有风月的人,是女人。
最爱风月的人,是文人。
最有风月的肉,当属回锅肉。
20世纪初,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曾经出现过一个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流派,专写风月言情。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先生就特别喜欢吃回锅肉,每当写小说写累了,他就踱步到院子里,伸伸懒腰,打打哈欠,手搭凉棚,看看天色,摘下青蒜,猪肉过水,上油锅、加辣酱、放青蒜,美美吃上一顿,再打着饱嗝回到书房继续写他的风月,写他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
后来,香港的李碧华笑他的回锅肉是鸳鸯蝴蝶回锅肉。
也许就因为这回锅肉,张恨水先生的风月小说,总比别人多了一点肉香辣香和蒜香,人人爱看,个个爱吃。
人世间的风月之花,常常盛开在这样一盘世俗的回锅肉里。
回锅肉里肥瘦相依,爱恨交集,软硬夹杂,有瘦肉结结实实、正正经经的劲道,也有肥肉颤颤巍巍、油油滑滑的性感,是菜中最为世俗香艳的肉,也是最有致命诱惑的肉。
二手男女也是回锅肉,这些经历了上次婚姻和感情的滚水焯、油锅炼,去了油,爆了香,卷成吱吱冒油的灯盏窝,变得老辣微甜,从容不迫,会哄你也会驾驭你,仰天长笑对众生,逢一个俘虏一个,见一双灭两个,无敌于情色江湖。
世人都爱回锅肉,殊不知回锅肉里有美味的危险,你以为不肥不瘦,不咸不淡,于是吃得口滑,不知不觉吃下半碟,把裤头撑得滚圆。就像一些老练的二手男女,一颦一笑里全是历练过的风月。
人肉里的风月,远远要比猪肉里的风月还要叫人屈膝的。
把舌头当拖把
吻的方式深浅不一,花样百出。
害羞的男女互吻,顶多像羽毛一样轻轻掠过对方的唇。拘谨的男人轻吻疼爱的女人,像是在对方的额头上盖一个热乎乎软绵绵的印章。顽皮的女人挑逗爱人,只肯像啄木鸟一样轻啄他一口。而热恋中的男女,则会舌吻。
所谓舌吻,就是把自己的舌头当作拖把,把对方的牙齿牙床拖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同样,吃玉米也有很多种花样,蒸煮焖炸,层出不穷。
最家常的就是炒玉米。起油锅,炝葱花,下玉米粒爆炒,这叫做“黄金万两”。假如再洒下一抓金黄的松仁,洒下一把碧绿的青豆,松仁粒粒松脆芳香,玉米颗颗饱满脆甜,这道菜就叫做“黄金翡翠尽妖娆”,趁热舀一勺,嚼得满口喷香。好的菜名像狡猾的厨师一样,也会刺激我们的唾液,撩拨我们的舌尖,给我们带来欲望的挑逗。
最无趣的是玉米糊糊,霍霍霍喝下一口,嚼也不是,喝也不是,嚼没有嚼头,直接喝下又恐发生堰塞,玉米糊糊像稀稠不定的泥石流一样,总是在你舌尖犹豫不决的时候,不由分说地,前呼后拥地灌进你的肚子。
最有趣的是爆米花。这也是很多人挥散不去的童年记忆,一条老街,一群小孩,一只火炉,一鼎黑锅,一个风箱,一把玉米,火起锅转,“嘭”一声巨响后,满街飘香。有一个网络笑话:两颗相爱的玉米粒决定结婚,新郎在婚礼开始就找不到新娘了,只好问一直跟在身边的一颗蓬松的爆米花,爆米花害羞地说:“讨厌喔,人家穿了婚纱你就不认得了?” 这蓬松的爆米花,就跟一些空虚蓬松的爱情一样,看着满满一捧,其实就一小把,吃下肚去并不顶饿。当然,有的恋爱并不是为了不饿,只是为了不寂寞。
小时候看见玉米上的玉米须,总把它扯下来,挂在颌下假装京剧老生的胡须,咿咿呀呀地假唱几句。蔡澜嗜好吃玉米须,他在专栏里眉飞色舞地说,把玉米须下油锅,炸得香脆,略加点糖吊味,新鲜可口,最为精彩。玉米须真的比玉米本身更美味吗?这有点像我第一次听到人家用紫茄子把蒂来炒五花肉时,倍感好奇,顿时来了食欲。当我们和食物相看两厌烦的时候,当男女相处日久平淡的时候,不妨借鉴一下蔡澜,把玉米须加点肉末,用猪油煸一煸。
再,把我们平时从不说的情话,说一说。
烤玉米是我的最爱,刷了烧烤汁,洒了孜然粉,淋了黄油或者色拉油,丢进微波炉烤得焦黄,一面慢舔细啃,一面努力体味一个女作家说的:“啃烤玉米,就像跟自家奶奶舌吻……”
3个烤玉米啃完,我愣没体会出这个舌吻,这个女作家难道真的是把舌头当拖把,在吃玉米之前用舌头把玉米棒子拖扫了一遍?
软软硬硬的调情
调情的方式,有硬,也有软。
花生的吃法很多,也是有软有硬。
有人喜欢把新收的花生水煮,咬起来清甜软熟,坐在那里吃了剥,剥了吃,剥剥吃吃,吃吃剥剥,直吃到饱死为止。有人喜欢把花生和猪脚炖得烂熟,盛起一碗,汤汤水水,淅沥嗦啰。还有人喜欢把水煮花生风干晾硬,嚼得滋味深远,嚼到脑门头筋胀痛也在所不惜。
我牙口不好,跟《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喜欢甜软的东西,最近几年更是嗜吃花生酱。李碧华说花生酱又湿又黏,好似烂泥巴,她看见花生酱就胃门落闸放狗。我是开门五里,倒屐相迎,舀一勺,厚厚地抹在热馒头或者面包上,又香又甜,食量立马超出一倍,当然腰围也因此而激增无赦。
张爱玲也应该是嗜吃花生的,在《红玫瑰白玫瑰》里,就借了花生酱来安排男女调情——
娇蕊取出一罐子花生酱笑道,“我是个粗人,喜欢吃粗东西。”振保也笑:“哎呀,这东西最富于滋养了,还会使人发胖。”娇蕊开了盖子道:“我顶喜欢犯法,你不赞成犯法么?”振保心领神会,把手按住玻璃罐说:“不。”娇蕊踌躇半日,就支使振保给她面包抹酱。振保真给抹了。娇蕊从茶杯口上凝视着他,抿嘴笑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支使你?要是我自己,也许一下子意志坚强起来,塌得极薄极薄,可是你,我知道你不好意思给我塌太少了的!”这段读来,我看得到娇蕊的媚眼如丝,看得到振保嘴角的坏笑,也闻得到花生酱的甜腻香气。
张爱玲的小说里还有个漂亮的使女叫做睇睇,长脸儿,水蛇腰,因为和女主人争宠,惨被赶出公馆。临出门前,睇睇虽然两眼哭得红肿,脸庞却寂静得泥制的面具,有人远远偷看她,看久了才发现她脸上有一条筋在那里缓缓地波动,从腮部牵到太阳心,而红而脆的花生米衣子,时时在嘴角掀腾着——霍,原来这妞子竟然还在吃花生!我当年看到这里,心里像打翻了一罐过期花生酱,抹得心里乱七八糟的,明白这睇睇肯定不会去上吊了,因为她还吃得下花生。
一颗花生就能缓解睇睇的悲哀。
我的堂姐夫是酒鬼,逢饭必酒,逢酒必花生米,我见过他炒炸花生米——先是冷锅放湿花生米,再冷油漫花生米,小火徐徐加热,期间不断翻炒,油一开,花生米先是噼啪爆响,继则咝咝小响,等到终尔吡啵有声时,就出锅了,洒上细盐,任其自然凉透。上桌时一看,每一颗花生米都沾着盐粒,带着油花,每一颗饱满油亮,志得意满。这多是酒鬼下酒的心头之爱,一碟花生米、半瓶三花酒、一个人,硬是可以从黄昏吃喝到半夜。
至于“温一壶月光下酒”,根本就是臭屁文人的瞎掰呻吟,只要有一碟酥脆花生米,立马原形毕露,酥脆略咸的花生米一颗紧接一颗吃得像鸡啄米,根本无暇与月色调情,皎皎明月只好去照沟渠了。
对于花生,大多数男人女人都不关门坚拒,各喜欢吃软的硬的,或者不软不硬的。
对于男女间的调情,大多数人却各有各的坚持,有人喜欢硬的,有人喜欢软的,还有人喜欢不软不硬的。
比较少见的是有一种人执拗,不仅软硬不吃,还放了狗在门口龇牙咧嘴。
拥有江湖气质的肉
爱吃牛肉的人,无论男女,多少有点江湖气。
跟味道中正平和的猪肉相比,牛肉味道浓厚,纹理粗粝,更像须发戟张、性情热烈的男人,更有拥有江湖气质。
《水浒传》里江湖好汉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的就是上好的卤牛肉。武松喝了十八碗“透瓶香”村酒,吃了四斤牛肉,直吃得口滑,这才提着哨棒,摇摇晃晃上景阳冈打虎去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贬到草料场,店家也是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他吃。林冲又自买了些,临走还打包两块牛肉,揣在怀内带走。除了义气,牛肉就是这些江湖男人们的最爱。
《诗刊》杂志曾经发表了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里面也提到牛肉,“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末句有伟人一贯的气冲霄汉,在瞬间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句。
以致我每次吃到土豆加牛肉,就心生豪气,豪气之后就静等着有没有屁。
古龙的江湖是食色江湖,他那么江湖的人,自然爱吃牛肉,他小说里的武侠人物总是爱吃切得薄薄的牛肉片子,炖得烂烂的红烧牛腩,炒得嫩嫩的蚝油牛肉,细软而不烂的烩牛肚丝……牛肉汤总是由那种胸脯很高,腰肢很细,年纪却很小的女孩子做好端出来的,有人说古龙的牛肉汤更像一个载体,承载着一个好女人应有的内涵。她必须热气氤氲,必须玲珑有致,必须浓而不腻,还必须清而不浮。
古龙真挑剔,这样的女人还真难找。
我嗜吃牛肉,每到饭馆,坐下便点一客水煮牛肉。这道菜的牛肉须得有江湖气的人来切,太薄显得小气局促,太厚又显得心思太重,须胆大心细,要切得半个巴掌大小,从滚烫鲜辣的牛肉汤里,夹起大片鲜辣牛肉,嫩而多汁,实在过瘾。有一次,在同一家饭馆里吃水煮牛肉,一看那汤,浑浊有余油亮不足,一夹那牛肉,比平时的缩水一半,随口问服务生:“你们换大厨了?”服务生答:“没呢,大厨请假回四川,下礼拜回。”同桌的人,见我竟然分得出大厨二厨的水平,大感惊诧。
张爱玲当年吃得出鸡味里有“二天油”的药膏味道,为此“把脸埋在饭碗里扒饭,得意得飘飘欲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我那天也是,假装低头喝了半盅茶,左右顾盼了好一会,这才把得意掩饰过去。
前不久,回家看望生病的老爸,进得门去,即闻到牛肉汤的香气,问老妈,是我们家的汤?
老妈抬起满是皱纹的老脸,说,我每天给你爸炖牛蹄牛筋汤,削皮剔骨撇浮沫,每天要炖8小时。
娶女人,一定要娶这种能为你炖8小时汤的女人。
这种女人,有真爱,比许多须发戟张的男人更有江湖气。
一斤红薯三斤屎
《一只红薯三个屁》这题目我一直觊觎。
不想几年前,竟被铁鹤舞写红薯时抢先用了,搞得我悻悻。那感觉如同你在街头那个烤红薯炉前,看中一只烤得糖油外溢的烤红薯,眼睛一亮,正待伸手,却被眼疾手快的旁人抢了去,叫人怎能不扯颈?
如今,我也写红薯,怎么也要用《一斤红薯三斤屎》,虽然在闻得到、看不到、抓不着的神秘感上略逊,但在分量和重量上,哈,哈,哈,至少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这话说完要打几个激灵的。
小时候,我们常常把红薯当水果吃,洗一洗,擦一擦,蹭一蹭,再削一削皮,或者用门牙刨一刨皮,就咬了生吃,咔哧咔哧,又甜又脆。记忆中,生红薯有甜浆汁,滴在衣服上眨眼就变成褐色,永永远远洗不掉,好似什么前科印迹一般,生生世世无计可消除。除了生吃,就是把红薯丢进炭火里烤,这叫煨红薯,等闻到红薯的焦香味道,要赶紧扒开炭灰,把红薯抢救出来,扒出来的红薯灰头土脸,皮绽肉裂,焦香烫手,得“呼呼呼”用嘴吹,得“咝咝咝”倒吸气,还得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来回急速倒腾,以免被烫着。因此古人比喻拍马屁之徒就如同吃煨红薯——又吹,又拍,又捧;到了今天,我想这比喻该换成求婚前的男人,他们对婚前的女孩就是又吹,又拍,又捧的。
吃过红薯的人都知道,吃红薯有两多——屁多,屎多。
煨红薯大半熟得不均匀,生红薯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吃下去,就要静等屁来,有时是响屁,“吥~~~~”,声调悠扬悦耳,有时是闷屁,“嗤~~~~”,好似单车轮胎漏小气,还有时是连珠屁,“咕噜咕噜~~~~~”令人起疑, 而且这种屁不来则已,一来必是屁意绵绵,放之不绝,一只红薯,远远不止三个屁!倘若在电梯这种封闭空间里放屁,每一个人掩鼻之余都会鼻知心明——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红薯屁了。
我不爱吃烤红薯,这跟三个屁和三斤屎无关,跟交通疏导有关。
我每逢吃烤红薯,喉咙就要被堵塞,好似下班高峰期塞车一样,水泄不通。
每逢这时我就要屏住气,腾出一只手来捶自己的胸口,咚咚两下,不行就再咚咚捶两下。一口水喝下去,感觉得到少许水小心翼翼地沿着喉咙管壁挤过去。然后后面的水才猛地一下发力,似乎喊了声口号,那些水团结起来,齐心一推,喉咙管子中间的障碍物即红薯才被冲下去了。这一口红薯,往往喝得眼泪都迸出一两滴。不是每一滴眼泪都跟激动啊爱恋啊有关,就好像打哈欠,经常也会迸出一两滴没什么感情色彩的眼泪。
虽然用了《一斤红薯三斤屎》这么够分量的题目,我还是喜欢那个《一斤红薯三个屁》。
越得不到的,越觉得特别好。
烤红薯亦然,婚姻和爱情也亦然。
年轻的月饼
年年有中秋,年年看月亮,年年吃月饼。
我们都老了,月亮还没有皱纹。
而月饼最过分,不仅不老,还似乎越来越年轻了。
中秋的夜晚,举头看明月,低头吃月饼。我们引颈望月,天空通常是深蓝色的,挂着一轮金黄的月亮。假如你像鲁迅笔下的后羿对着它:“呔!”大喝一声,月亮也不会理你,抖也不抖一下。倘若你前进三步,月亮便会退三步;你退三步,月亮也会如数前进。
月亮这么多年来,似乎一直不肯老。
“年轻人想看三十年前的月亮,说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杂云轩信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而且圆。”这话是张爱玲说的。而三十年前,我们吃的月饼是用纸包的,月饼渗出的油渍浸沁在纸上,湮开一个月饼大的红黄湿晕,散发着香甜温暖的气息,即使月饼吃完了,那张油纸仍可以放在枕边诱你入梦,直到月饼油渍日渐陈旧而迷糊……因着这份有滋有味的儿时回忆,似乎我也有理由说,三十年前的月饼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饼要销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