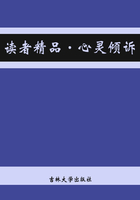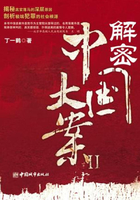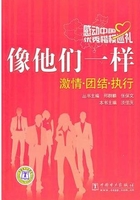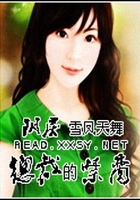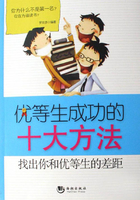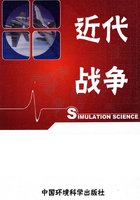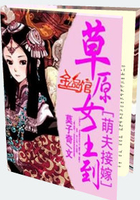挚虞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诗体演变的脉络。中国诗的源头是《诗三百》,而《诗三百》中诗的体裁句式绝大多数是四言。从语言的角度看,四言诗具有整齐稳重的特点,在变化上也显得相对简单,这种简单性正与人类早期语言表达的简单朴素相一致。从音乐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早期人类的乐感,无论是旋律还是节奏,都呈现出简单和整齐。鲁迅在探讨文学起源时,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他在《门外文谈》中说,劳动时的众人协同用力催生了劳动号子。所以他说自己是“杭哟、杭哟”派。《诗三百》中的四言诗正具有这种“一句两个节拍”的简单稳定的节奏特点。
学界论《诗经》之体,又常有“雅”、“颂”、“风”、“南”四体之说。雅即小雅、大雅,颂即商、周、鲁三颂,风即十三国风,南即周南、召南(顾炎武《日知录》、梁启超《释四诗名义》)。颂是原始的舞曲祭歌,雅是西周土乐,风是黄河流域各地的土乐,南是长江流域的土乐。雅、颂起源较早,至迟在西周前期和中期即已存在。风诗是晚出的新声,大约在西周末期兴起,有《桧风》可证。南诗的出现大约在平王东迁之后,因为长江流域的渐渐开发是公元前8世纪之后的事。二南之中,也明显可见没有西周诗歌。孔子在《论语》中再三称道二南,如: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女为周南召南已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可见后来者居上,“南诗”是“四体”中最进步的。但此种论体,着眼于音乐种类的划分,与我们论及的体式之变已无关涉。
《诗经》之后,诗歌逐步发展,诗体也逐渐变化。挚虞论体,论及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经》四言之后,即论三言。但《诗经》之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辞(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屈原及其作品均提出疑问,但仅属“大胆假设”,尚未做到“小心求证”)。为何挚虞不论楚辞体而直接讨论汉代乐府中的三言体呢?推想其原因,或许挚虞认为“辞”不能称作“诗”。后世学者也多有此意,如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就将屈原作品列为“辞赋”而与“诗歌”区别。楚辞句式变化大,六言、七言、八言交错,甚至还有九字句,例如《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历吉日乎吾将行。
可见屈原作品属于长句长篇一类的作品,句式变化大,但我认为仍应归入“诗”。这是一种体式特殊的诗。楚人敬重鬼神,祭祀活动繁多,活动中歌唱不已,故而形成了“楚辞”这种特殊形态的诗——长句长篇的作品。这与黄河流域的诗歌形态有较大区别。应该说,楚文化表现在诗歌上,它朝前迈出的步子很大,从内容和形式上看都是一种更先进的诗歌。但是,当时文化的主流是黄河文化,诗歌形态从四言径直跳到六言、七言或八言、九言,难以被主流文化所认同和接受。这也揭示出诗体发展不能是“突进”式的,而只能是“渐进”式的。在中国诗史上,诗体由四言循序渐进而至五言,再进至七言,最后以五言、七言定格为诗歌的基本体式。这也体现了诗体发展的规律。
楚辞作为诗歌,犹如炫目一现的昙花。
然而正因为楚辞体诗歌具有超前性,它在后来诗的发展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如汉初项羽之七言四句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又如刘邦之七言三句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过了七十年,到了汉武帝时,又出现了武帝的《秋风辞》、李陵的《别苏武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和刘细君的《乌孙公主歌》。如《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楚辞体诗歌的长句形式已经逐渐趋向于七言,而它的长篇形式则朝着短小方向发展。楚辞体诗歌正是后世七言诗的滥觞。
《诗经》之后,诗体发展的正格是五言诗。三言体和杂言体则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变格。
三言诗以三字一句作为意义表达单位,显得过于短小,难以成立,正如二言一句的诗也无法成立一样。早期曾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样的诗句(《吴越春秋》),后来也两两归并而成四字句:“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三言句在《诗经》中数量很少,可见它在传情达意上无法与四言句抗衡。楚辞中的六字句多由两个三字句归并而成,七字句也是“三兮三”这样的特点,即两个三字句中间联结一个“兮”字。汉代郊祀祝颂之辞用了不少三言。由于其节奏短促有力,便于记颂,于是训诫之辞和民间谣谚也常用三言,但它用于艺术表达的回旋余地小,不易抒情,于是魏晋之时便已式微。也有极少量的三言诗写得十分成功,如魏末晋初诗人傅玄的《杂言诗》:
雷隐隐,
感妾心,
倾耳听,
非车音。
全诗仅寥寥十二个字,把思妇在等待时的那种专注和痴迷之情描写得惟妙惟肖,真让人读后顿生“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慨叹了。这样的佳作,是三言诗中的凤毛麟角。
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中间还经历了杂言体的过渡阶段。杂言体的诗包含了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甚至还有二字一句和一字一句的。汉乐府诗有很多杂言诗作品,如《有所思》:
有所思,
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
双珠玳瑁簪。
闻君有他心,
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
当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
勿复相思。
相思与君绝。
鸡鸣狗吠,
只嫂当知之。
妃呼唏!
秋风肃肃晨风飔,
东方须臾高知之。
又如《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些诗中,各体杂陈,长短随意,整散不拘,二、三、四、五、六、七言的诗句都有,是典型的杂言体。汉乐府多用杂言是由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决定的。乐府诗宣泄的是直露而激烈的思想感情,在中国诗史上是一次情感表露的大解放——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这些都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这样的思想内容当然只能用“杂言体”来表达。像《上邪》诗中那种犹如山洪暴发般的感情,怎能采用固定的章法和句式呢?一个爱情遭受挫折之后更加渴求爱情的女子,她呼天抢地般的呐喊,当然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四言诗之后出现的杂言体是一种新体诗,集中体现在汉乐府的《铙歌十八拍》中,包括《有所思》《上邪》在内的这十八首诗全是杂言,可谓自成一格。杂言相对于整齐的诗歌句式,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如果说汉乐府诗的作者完全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写杂言体的诗,并非有意识地创造新诗体的话,那么到了南朝刘宋时的鲍照和盛唐时的李白那里,他们则是自觉追求一种特殊的文学效果,在“歌行体”的诗中,把杂言的妙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是在杂言诗这一过渡期之中,孕育出了新型的诗体——五言诗。
前文所引挚虞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五言诗的最早形态是以一句两句杂在四言诗之中出现的。所指就是《诗经·召南·行露》,该诗如下:
厌浥行露。
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
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
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
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
亦不女从。
这首诗共三章,首章三句,全是四言,二、三章每章六句,都是前四句五言,后两句四言。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诗经·小雅·北山》之中。但是,整部《诗经》中没有一首通篇五言的作品。这说明迄于春秋时期,只有零星的五言诗句,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篇。
晚于挚虞的南朝著名学者刘勰,同样高度关注五言诗起源,他指出:“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刘勰也是先考察《诗经》,找到的五言诗句的例子正与挚虞相同。但他接下来却以《沧浪》作为“全曲”,将其视作完整的五言诗篇。《沧浪》一诗见于两书,一为《楚辞·渔父》,一为《孟子·离娄》,《渔父》的真伪,后世争论很大,可不论。以《孟子》所引为据,则《沧浪》当产生于战国时代。其辞如下: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我足。
诗的一、三句都是六言,对此,刘勰认为其中的兮字“乃语助余声”,“无益文义”,故欲删去,从而视作五言。我们认为,汉字一字一音,字字独立,不能视“语助”为无物。《诗经》中有许多“语助”一类的虚字,如“薄言采之”的“薄言”,怎能删去?况且“兮”字在楚声诗歌中关系到体格特征,不可忽视,更不能删削。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即《汉书》中的《郊祀歌·天门》,其诗曰:
蟠比翄回集,
贰双飞常羊。
月穆穆以金波,
日华燿以宣明。
假清风轧忽,
激长至重觞。
读后茫然,不知所云。再检王先谦《汉书补注》,发现原诗应是:
蟠比翄兮回集,
贰双飞兮常羊。
月穆穆以金波,
日华燿以宣明。
假清风兮轧忽,
激长至兮重觞。
可见删削兮字以成五言,将乖违辞意,全不可通。
到了秦代,也没有出现完整的五言诗篇。秦代甚至没有任何诗歌作品流传下来。秦朝存世极为短暂,仅十四年,犹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苍穹。但是,秦王朝连年征伐,徭役繁苛,人民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形下,人民自会唱出心声,然而想必数量不会太少的民间歌谣却一首也没有流传下来,这是秦始皇和李斯实行“燔灭文章”的文化灭绝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到了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时,引用了三国末期吴人杨泉《物理论》中的一首民谣,其辞曰:
生男慎勿举,
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
尸骸相撑拄。
这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它写的是秦朝征发大批民工修筑长城,百姓死亡无数的事。但它不是秦朝的作品,郦道元只是引用,并没有也不可能说明杨泉《物理论》中这首《长城谣》五言诗的来历和出处。比杨泉早数十年的建安诗人陈琳,有一首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的句子,这应该是《长城谣》五言诗的来源。杨泉诗正是删改陈琳诗而成。
汉初七十余年间,有戚夫人《舂歌》、李延年《北方有佳人》等作品,其中五言诗句明显增多,但仍不是全篇五言。直到汉武帝末期,才出现了民歌五言诗。《汉书·贡禹传》中记载:
何以孝悌为?
多财而光荣。
何以礼义为?
史书而仕宦。
何以谨慎为?
勇猛而临官。
到了汉成帝时,五言民歌渐渐多了起来:
安所求子死?
桓东少年场。
生时谅不谨,
枯骨后何葬。
——《汉书·尹赏传》
邪径败良田,
谗口乱善人。
桂树花不实,
黄雀巢其颠。
昔为人所羡,
今为人所怜。
——《汉书·五行志》
民间文学总是新的文学,也是文学中新体式的源泉。它们犹如深山清泉,石涧春水,潺潺流来,静静地、无穷无已地赋予各个时代文学以新的生命。
在民间五言诗的滋养之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产生。东汉班固《咏史诗》楬橥之后,经张衡、蔡邕、秦嘉的不断发展而到《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式才完全成熟和定型——一个“五言腾踊”的诗歌时代来临了。
诗体变化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七言诗的出现与定型。
五言诗之后,诗体发展的正格是七言诗,六言诗则是这一发展进程中的变格。由此可见诗歌体式之变也与其他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充满了复杂性。
六言诗句在《诗经》《楚辞》中已出现,而尤以《楚辞》中为多。这一现象正如刘勰所言:“六言七言,杂出诗骚。”(《文心雕龙·明诗》)《离骚》中的多数诗句是六言、七言。汉代五言诗出现之后,至汉末开始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篇,如孔融的三首《六言诗》:
郭李纷争为非,
迁都长安思归。
瞻望关东可哀,
梦想曹公归来。
——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