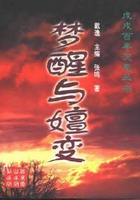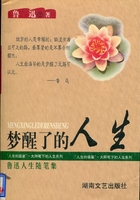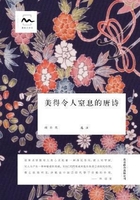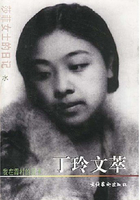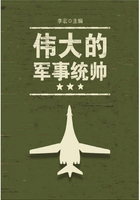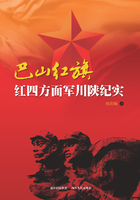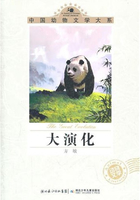吴歌西曲经由倡优艺妓、豪商富贾之口,传衍至社会各阶层,就有贵族采集和模拟这些艳歌。《南史·王俭传》云:“褚彦回弹琵琴,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梁书·羊侃传》云:“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最早大量地学习吴歌西曲,因而也最受正统贵族奚落的,却是下层文人鲍照和汤惠休。颜延之称汤惠休的诗是“委巷中歌谣耳”。起先是鲍照这样不避俚俗的下层文士,进而是在浮华空气中出生的“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终于,拟作“里巷歌谣”成了盛极一时的风气。及至梁武帝,将这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翻了个,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提倡。《唐书·乐志》载梁武帝曾令沈约拟《白纻舞歌诗》的歌辞而改题为《四时白纻歌》。而《白纻舞歌诗》的大意如《乐府解题》所说,是“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为乐”。这个时候,宫廷文学中已经透露出了浓厚的宫体的气息。宫体诗风在简文帝时出现,实际上是水到渠成。
市井流行歌曲的浮华风气同宫廷奢侈享乐汇合,首先,产生了音乐方面的变化。江南流行清商曲,清商曲以丝竹乐器为主,音声动人,被认为是“郑卫之音”,因此深得贵族的喜爱。梁裴子野的《宋略·乐志叙》描述宋以来的音乐歌舞云:“优杂子女,荡目淫心。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慢为环玮,会同飨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在上班(疑脱一字)赐宠臣,群下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梁武帝宫中也有专门演唱吴歌西曲的女伎。《南史·徐勉传》载,梁普通年间,梁武帝挑选“后宫吴歌、西曲女妓各一部”赐予徐勉。歌曲有曲有辞,配合着“郑卫之音”的就是艳诗。对宫廷文艺说来,辞和曲的影响是同时发生的。因而梁代萧子显评价当时的艳诗体云:“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宫体诗多作于歌舞宴集之上,诗成之后交付歌伎演唱,其中有的是依声作辞,有的是由乐工乐伎配上曲谱,但都不出当时流行的清商曲。
其次,对吴歌西曲等市民文学的接受,使宫廷贵族逐渐偏离正统文学观念。当时有一些正统贵族如萧子显和裴子野维持着贵族的体面,对流行的艳歌持轻蔑的态度,但萧子显又不能不承认艳歌盛极一时的现状,只好说“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裴子野的《雕虫论》也说自宋以来,“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但简文帝萧纲站在贵游年少一边,倡导离经叛道的主情说,反对文学以经典为范本,他在《与湘东王书》中云:“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吟咏性情是有明显倾向的,《答新渝侯和诗书》云:“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情性”狭窄到了“艳情”,而“吟咏情性”本也不想“止乎礼义”,而是与“摈落六艺”互为因果的。这清楚说明宫廷贵族内部的分化和正统诗教在贵族中的衰落。
宫体诗的出现也有诗体自身发展的因素。六朝诗体,由玄言而山水而咏物。简文帝之前,诗歌描写对象大抵有天文、气象、动物、植物、器物等,至简文时代,王室士族奢侈淫逸,蓄妓养妾风气甚盛,女色声伎的享受成为门第世家的生活重心。于是,诗人文士咏物的兴趣与注意力,也转向集中于宫廷女子身上,由直接写酥软和横陈的女人进而写闺思和娈童,再写女人所用的物品来代替人,诸如接近肉体的绣袜、枕席卧具,以及其他器物。再由于女性复杂多样的容止情态,具有特殊美感与吸引力,诗人得以客观写实的态度,并以形似、细密、雕琢的手法,全力描绘女性内在与外在的各种怜爱情态,于是侧艳的宫体诗诞生了。
宫体诗是在永明体基础上出现的“新变”诗体,由永明体写自然山水转为写艳情,更注重形式的华美精巧。宫体诗作家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宫体诗人中坚徐陵也刻意求新,《南史》说“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传写成诵”。萧纲、萧绎也明确地反对“宗经”,反对以政治与伦理的标准约束文学,他们看重文学的美感与抒情。萧纲更主张全面新变,提倡“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萧绎也要求文学“绮彀纷披”、“情灵摇荡”。宫体诗的“新变”不仅指题材,也有辞藻、声律等内容。
宫体诗“新变”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摆脱了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离经叛道,多以女性为描写对象。宫体诗人认为写女性具有美感,是有新变意味的好题材,因而大胆描绘女性容颜、体态、服饰及男女艳情,而提供了新的审美类型,拓展了诗歌题材。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继二谢以山水为主题的诗歌一变为描绘人物为主的“宫体”,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和革新精神。当然,宫体诗中女性是被观看与被描写的对象,依然表露出传统“男尊女卑”、“夫主妇从”的性别政治,在这种“宰制—统治—从属”的文化政治关系凝视下,宫体诗中“妇女”具有固定的形象特征:温柔、怯弱、谦卑、顺从等等。
宫体诗“新变”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声律方面向前跨了一大步,因而在汉语诗体流变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我们先看宫体诗的体式流变。宫体诗的主要体裁是五言和七言,五言占绝对优势,七言尽管也是主要体裁,但它仅有五言诗的四分之一,其他句式在宫体诗中微乎其微。宫体诗之前,元嘉体以长篇为多,半数在十八句以上;永明体诗歌中,八到十六句的诗歌过半,短篇制作是大多数。但这种变短的趋势只是刚刚开始,长短篇之间的差距并不大,短篇的数量只比长篇略高一点,而二十句式的数量仍然很多,也是沈、谢的主要体裁。宫体诗中,十二句以内的作品占了压倒性优势,短篇制作中数量最多的是四句式和八句式。综合来看,五、七言中,使用频率由高到低的排序是四句式、八句式、六句式和十句式。参阅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9-184页。这样一来,宫体诗在诗体发展过程中所占的位置一目了然。诗歌趋短有各种因素,既是对晋宋诗歌繁复铺张倾向的反拨,也是受到民歌影响的结果。吴歌西曲中五言四句较多,这对宫体诗人的创作有直接影响。
其次,对偶的大量使用也是宫体诗体式流变的重要方面。有学者通过数量统计发现,宫体诗中绝大部分作品是对偶诗,宫体诗人对对偶技巧是相当重视的。宫体诗人使用对偶相当频繁,对偶句在宫体诗中占很大比例。对宫体诗中对偶的数量分析,参看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6-187页。词性相对是对偶能否成立的最基本条件,也就是做到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等等。进一步提升难度的话,就是在同一词性内部进一步分出若干小类,要求以小类相对,如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这就是工对。还可以要求对句做到结构相对,如动宾对动宾、主谓对主谓,修饰对修饰,等等。检查宫体诗中的对偶句,以词性相对(宽对)和结构相对而言,宫体诗的偶句大体上都做到了。
按照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的归类,工对可以具体分为十一类和若干门,只有同类同门的词相对才算工对。王力先生的分类主要以唐诗为依据,以此衡量宫体诗,也同样实用。现略举一些例证:
一、天文对。“何当照梁日,还作入山云。”(萧纲《采桑》)“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庾信《夜听捣衣诗》)
二、花鸟对。“细萍重叠长,新花历乱开。”(萧纲《采桑》)“竹叶裁衣带,梅花奠酒盘。”(徐陵《春情》)
三、器物对。“月辉横射枕,灯光半隐床。”(萧纲《夜夜曲》)“奇香分细雾,石炭捣轻纨。”(徐陵《春情》)
四、衣饰对。“下床著珠珮,捉镜安花镊。”(萧纲《采桑》)“风住疑衫密,船小畏裾长。”(陈叔宝《采莲曲》)
五、形体对。“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庾信《王昭君》)“落花同泪脸,初月似愁眉。”(陈叔宝《有所思》)
六、宫室对。“一去葡萄观,长别披香宫。”(萧纲《明君辞》)“合殿生光彩,离宫起烟雾。”(庾肩吾《赋得横吹曲长安道》)
七、颜色对。“白石春泉满,黄金新埒开。”(庾信《咏画屏》)“杨柳条青楼上轻,梅花色白雪中明。”(江总《梅花落》)
八、人名对。“自作明君辞,还教绿珠舞。”(庾肩吾《石崇金谷妓》)“歌撩李都尉,果掷潘河阳。”(庾信《结客少年场行》)
九、地名对。“偃师虽北连,辕已南背。”(萧纲《伤离新体诗》)“龙城远,雁门寒。”(徐陵《长相思》二首之一)
十、数字对。“欲传千里意,不照十年悲。”(萧纲《华月》)“荡子十年别,罗衣双带长。”(刘孝绰《古意送沈宏》)
十一、方位对。“东西争赠玉,纵横来问家。”(萧纲《茱萸女》)“杏梁始东照,柘火未西驰。”(萧绎《树名诗》)
十二、重叠字对。“尘镜朝朝掩,寒衾夜夜空。”(萧绎《闺怨》)“袅袅河堤树,依依魏主营。”(徐陵《折杨柳》)